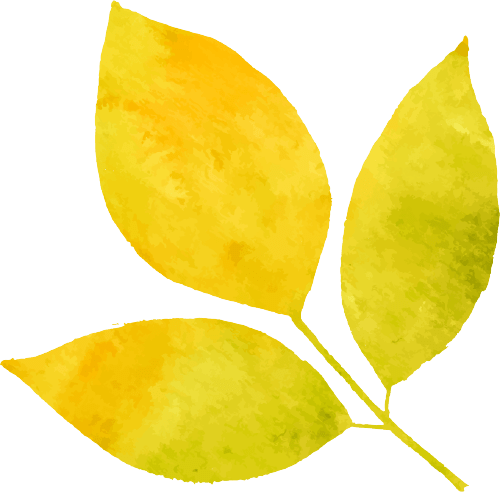| 新书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苗族的传统信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上 › 新书 |
新书
|
仪式—心理学派:代表人物是缪勒、泰勒、弗洛伊德,研究的起点为关注宗教或仪式的起源,主要观点是仪式起源于“自然崇拜”“蒙昧人—哲学家”“俄狄浦斯情结”。 社会结构—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是涂尔干、麦克斯·格拉克曼、范根纳普、维克多·特纳,研究的起点为关注仪式功能,主要观点是社会纽带、个体的社会化、舒缓和解决社会争端、整合社会、身份转换,认为仪式是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神圣或世俗的关系和行为被看作二元对立的基本社会分类。 宗教现象学派:代表人物是米恰尔·伊利亚德,研究的起点为关注意义的来源,主要观点是神话与仪式是人们获得经验与人生意义的方式,仪式是对神话或象征的展演。 象征文化学派:代表人物是格尔兹、特纳,研究的起点为强调仪式附带的意义、价值与情感,主要观点是强调仪式所表达和传递的观念、价值和情感、态度。 实践、表演学派:代表人物是布尔迪厄、马歇尔·萨林斯,研究的起点为仪式的核心是变化、权力与关系是分析的起点、看重文化的普遍实践。主要观点是仪式参与者通过对象征的理解、阐释、修订,形成神话与仪式双向互动;历史和结构不存在,仅以文化价值的形式被纳入人的再生产和实践中,人的行为是形塑文化和历史的关键。 尽管六大学派对人类仪式研究的关注点各有侧重,但研究的路径基本沿着两个主要方向进行:一是对仪式与古典神话之间关系的阐释和理解,以泰勒、斯宾塞、J.G.弗雷泽为主要的代表,其中J.G.弗雷泽的《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堪称典范之作;二是对仪式的宗教行为和社会实践理论的探讨,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可算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六大学派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社会结构—功能学派和象征文化学派以及实践、表演学派。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学者深受这些学派的影响。比如,彭兆荣认为:“它(仪式)可以是一个普通的概念,一个学科领域的所指,一个涂染了艺术色彩的实践,一个特定的宗教程序,一个被规定了的意识形态,一种心理上的诉求形式,一类生活经验的记事习惯,一种具有制度性功能的行为,一种政治场域内的策谋,一个族群的族性认同,一系列节日庆典的展示,一个人生礼仪的通过程序,一个社会公共空间表演……”学界一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切入去认识和理解仪式,这种定义的方式具有较大幅度的开放性和空间。在世俗社会,人们同样依据自己的认识、经验和理解去解释仪式,譬如,认为仪式是一种程式化的宗教程序,是一种艺术性的实践行为、一种地方性的记事模式、一种被约定的意识形态、一种族性认同活动,或者是一种娱情表演、一种人生过程的记忆……一言以蔽之,对“仪式”一词的理解和定义,从来就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 随着仪式研究视野和边界的不断拓展,现代仪式研究更多地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民俗与礼仪,学者对仪式行为包含的技术性、符号性、物质性、资料性研究兴趣日益高涨。人们逐渐认识到,仪式还可以是一种文化诗性行为,更是一种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现象,这种诗性特质来源于仪式行为主体的心理情感活动以及表演性行为过程。 学界从未停止过关于仪式与文学产生的关系,特别是神话、仪式、巫术与诗歌的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在整个仪式活动中,文学作为仪式的口头活动部分,起到贯穿、承接、指示和强化仪式的诸多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仪式与文学的产生关系密切。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最为擅长和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恰好是其“诗学化”的研究传统,即对口传神话的记录、文本的重新诠释,对历史文献的破解、文字训诂,大量地针对未开化民族(野蛮人)口传神话、古歌、巫术、方技的搜集和整理等。这种“诗学化”的研究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文学写作与批评的风尚。泰勒就曾深入研究神话中仪式(物态神话)与语言(语言神话)之间的关系,他把神话类分为“物态神话”和“语态神话”,认为物态神话处于基础地位,而语态神话处于从属地位。后来的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埃利希·诺伊曼、帕里、洛德等人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讨论过诗歌与巫术仪式之间的关系。博厄斯认为早期民族的诗歌具有礼仪的性质,认为神话与仪式是一种协约关系,一个仪式与一则神话相对应,仪式是神话的展演,神话是仪式的原始刺激物;利奇则认为言语,诸如圣歌、咒语、祷词、歌谣之类,如同手势和器物一样具有仪式的价值;兰德尔·柯林斯认为“在微观社会现象中,仪式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也是一切社会学研究的基点”。 仪式在程式展演的过程中表达意义以及意义的重要性。仪式中的人、服饰、道具、动作、声音共同完成一套固定的仪式行为,其间,那些连续的、片段式、纵横交织的象征性行为或情节实现意义的呈现和诠释,因而仪式具有文学的特质,表现出文学所特有的自我说明能力和结构特征。仪式作为文学表达形式的载体,将人们对宇宙、时空、鬼神、生命、死亡、情爱、伦理等的观念通过一系列象征、模拟的行为和程式进行表达和演绎。通过仪式,我们可以洞察不同时代的文化面貌、文化事项和社会风尚。中国古代诗歌中常常会提到或描述各种仪式,因此许多学者往往从诗歌的角度切入,研究诗歌与仪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诗歌与民俗、祭祀、巫术之间的关系。显然,诸如此类的研究已涉及文学与仪式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学界对先秦时期诗歌与当时盛行的巫术仪式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已触及仪式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微妙联系,但遗憾的是并未深入展开对仪式与文学之间更为广泛的研究。在笔者看来,仪式不仅是文学产生的语境,更是文学阐释的重要形式,还建构了文学的表现形式,成为文学表达的重要审美特征。文学借助仪式展示意蕴、思想和情怀,从而表达人的存在、心灵和理想。综上,笔者在总结和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仪式的理解:所谓仪式,就是将个体经验通过一定的人为形式变为集体经验的人类活动和典型范式。 苗族古歌始终与广泛存在于民间的神圣或世俗的仪式如影随形,通过与仪式的交融以及各种文化符号构筑起自身在本民族文化中的定位。从文学的角度看,苗族古歌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口头歌谣。从仪式研究的角度看,经历了仪式化洗礼的苗族古歌,已然成为一种融入苗族族群精神与现实的仪式,每一次吟唱,都是一场郑重的仪式展演过程。可以说,苗族古歌是苗族心理的表现,内容与仪式的结合成就了苗族的精神家园。这或许可以给苗族古歌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仪式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吟唱来呈现。人类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仪式一直是表达人精神和意志最惯常的社会行为和活动,当人们被恐惧、压抑、欣喜、期待、迷惘、悲哀等情绪左右时,总会寻找某种方式去祈求逃避和化解,以求得心理上的抚慰和宁静。在苗寨里,无论是在场面宏大的宗族祭祀庆典活动中,还是在个人的各种人生礼仪中,仪式与苗族古歌总是相伴而生,相映成趣,传承千年。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从这些神圣的吟唱与感性的仪式中获得某种力量,与祖灵的精神合二为一,从而感到快乐、慰藉与释然。无论是族群的理想还是个人的情怀,无论是宗教活动还是私密往来,都能借助苗族古歌和仪式沟通情感、表情达意。 如果说苗族古歌本身只是一种文学样式,那么苗族古歌的吟唱或展演,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仪式所具备的诗性特质以及典型范式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通过苗族古歌仪式化的吟唱过程,实现个人情感转化为集体经验的标记、强化和身份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吟唱苗族古歌是一种特殊的仪式。“仪式的古歌”使苗族的审美理想与价值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达。
作为仪式象征符号的歌师 苗族古歌吟唱者的身份是特定的。学界将吟唱苗族古歌的人称为“歌师”,实际上,在不同的苗族方言区或支系中,“歌师”的称谓各有不同。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记住动辄万言、数以千首的苗族古歌,绝非等闲之辈能够做到。作为仪式象征符号的歌师,唯有那些有超过常人智慧、记忆力惊人、富有创造力和恒心的苗族中的佼佼者才能胜任,甚至村寨中还盛行一种说法,即成为歌师需要得到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帮助,这当然缺乏依据,也难以考证。在苗族村寨中,能够得到公认和尊重,能承担起演述古歌这一重大责任的人,无外乎就是村寨中的鼓藏头、理老、活路头、鬼师、巫师等。这些人具备聪明的头脑、嘹亮的歌喉,超强的记忆能力、表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掌握苗族古歌的内容并具备阐释苗族古歌含义的能力,他们除了拥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处理重大事件和矛盾纠纷的能力之外,还必须有教授徒弟学唱苗族古歌的能力。尽管这个衡量和评价标准体系不受性别和年龄的限制,但歌师一般还是以男性居多:《贵州民间艺人小传》一书收录了二十位苗族歌师,其中女性只有两人。麻山地区传唱《亚鲁王》古歌的“东郎”,也大部分是男性。清镇麦格乡四印苗族支系吟唱《簪汪传》的“无绕”也以男性居多,因为在当地各个家族的传承谱系中,苗族古歌的吟唱一般传男不传女。 在黔东南的苗寨中,鼓藏头是苗族中一个宗族(又称“鼓社”“江略”)的宗教领袖,是“鼓藏节”祭祀活动的核心人物和主持人;寨老是一个个高度闭塞、聚族而居的苗族村寨的自然领袖,又是家族的族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知识丰富、行事稳重、通晓本村传统文化的长者担任;理老是本村“习惯法”的司法者,村中一旦出现纠纷、偷盗争斗时,就要依法裁决,因此理老只能由熟知古理古规、明白是非、正直公正、威信高、能说会道的长者担任;巫师是苗族民间巫术仪式的执行者,民间常常认为他们是能沟通天地阴阳的人。苗族巫术抛开其中弥漫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色彩不谈,巫词中往往混杂着民族的历史、哲学以及地方性知识,而展示巫术的仪式则一定伴随着苗族古歌、音乐甚至舞蹈。主导和实施巫术仪式的巫师自然是苗族古歌的歌者与施仪者,他们的吟诵要么神秘庄重,听者不可随意模仿跟唱;要么充满禁忌,内容隐晦,使听者心存敬畏与恐惧,避之不及。在不同的村寨,巫师被称为算命师、通司、鬼师。黔西北苗族地区把丧葬礼上负责祭祀的歌师称为“东郎”。除此之外,村寨中的活路头、芦笙头等,也是苗族古歌的吟唱者和传承者。 尽管苗族歌师的身份是特定的,也非常人能胜任,但他们并非专事苗族古歌演述,更不以此为生。歌师的身份往往是“兼职”的,平日里与族人的生活作息无异,闲时务农生产,过着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只在祭祀、节庆、婚丧、人生礼仪等重大场合,由村寨集体推荐或某户村民“邀请”的方式去不同的场域演述苗族古歌。演述苗族古歌既是职责,也是他们的兴趣和喜好,同时也提高了其威望和知名度。 每逢宗教祭祀、驱灾辟邪、婚礼丧葬、治病除魔、秉公裁断的仪式场合,就会吟诵古歌,歌师就变成具有象征意义的引领者:要么是宗教信仰的领袖,要么是解决纠纷的判官,要么是声情并茂的表演者,要么是治病救人的医者……在整个苗族古歌的吟唱过程中,歌师永远是具有仪式象征意义的符号,他是开始,也是结束;他是圆心,也是圆周。无论是一人、两人还是多人,歌师永远是苗族古歌唱述的灵魂,指引着人们的行动,牵引着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他们既普通,又让人敬畏崇拜,他们仪式性地用苗族古歌在村寨中传播着苗族的宗教信仰、哲学、道德、风俗与社会规范。每当人们虔诚聆听歌师吟诵那些古老的歌谣时,内心便涌出千种情绪……那些名为《开天辟地》《枫木生人》《溯河西迁》《跋山涉水》的苗族古歌,一首首,一句句,永远唱不完,激荡着世世代代的苗族精神,教他们不忘故土、不惧艰难、心怀美好、守望未来、真诚生活,也带给他们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歌师学习苗族古歌完全靠口传心记。贵州雷山县的苗族歌师唐德海曾说,在其一生学习与传授苗族古歌的过程中,不仅完全掌握了苗族古歌复杂的问答叙事,而且在问答叙事的基础上,也融入了自己对苗族古歌的创新,使得他传唱苗族古歌的技艺十分娴熟。在传统语境中,歌师是苗族古歌得以活态流传的保存者、传播者和再创造者,是唤起苗族族群集体记忆和想象的引路人,是苗族精神文化家园的守望者。歌师的出现和存在都只能在苗族文化语境中。正如乌丙安所言:“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民俗知识和参与民俗活动的经验,而且还在社会群体中、在大多数接受习俗化养成的承受者受众中获得信赖荣誉和崇敬。”他们“维护着族群地方文化的血脉”,成长为“民俗文化传人和习俗社会规范的主要支配力量”。 神秘而郑重的苗族古歌传承仪式 在苗族传统社会中,拜师学歌,无论是家族传承、祖先传承,还是师徒传承,都要经过一系列神秘而古老的仪式,才可以真正开始跟着师傅学习古歌。通常歌师不轻易收徒,收徒既要有师徒的机缘,徒弟还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首先,学歌者的天分和勤奋是第一位的,要聪慧敏捷,记忆力超群;其次,学歌者要人品朴实,勤奋好学;再次,学歌者自己要有意愿学歌,要再三诚心求教,表明决心;最后,学歌者的资质、诚心、恒心、人品等要被反复考察,还要经过巫术(占卜)一类的方法测算后,才可能成为歌师的徒弟。歌师通常一次收三五个徒弟,而能真正学到本领、坚持下去的常常只有一两个人。 黔东南苗族地区拜师学歌的仪式郑重神秘,程序烦琐复杂。歌师经过筛选和考察,决定收徒后,通常在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期间择一吉日,学歌者要拎一只鸡、一束摘糯、几条鱼,带着一元两角钱到歌师家,举行祭“歌神”、拜师傅的仪式。这些带去的物品各有寓意,鸡用来占卜传授苗族古歌的吉凶,摘糯能让人在学歌时得到祖灵的启迪,钱用来给歌神买路,使歌神能到人间,鱼用来祭祀曾生活在河边的祖先。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歌师便开始“祭歌神”仪式。完成歌师一连串复杂的唱、颂、祭、演和学歌者的应和仪式之后,收徒仪式结束。歌师便开始正式教徒弟学唱苗族古歌,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苦。学歌者每学完一段古歌就拿起一块竹片放在一旁,“放竹片”的行为一方面充满了仪式感,另一方面又实质性地起到了记录学歌进展的作用。许多苗族村寨规定学歌必须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可以连续学三年,如果学不会,那就不能再学了。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学会数量和篇幅都惊人的苗族古歌,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歌师也好,学歌的徒弟也好,都是村民中智慧与品性出类拔萃之人。学歌的仪式,还透露出一个口传文学的重要信息:没有一首同名的苗族古歌是完全相同的,哪怕是同一人演唱的,因为每一句歌行的识记只能靠耳闻心记,每一次唱述都是歌师凭记忆的重复与发挥。大概苗族古歌的动人之处也在于此:永远是古老和新鲜的混合体,充满了不同历史时期每个歌师对苗族古歌的理解与阐释,以及鲜明的个人特征。除了师傅教授苗族古歌,苗族民间还流传着更具神秘色彩的学歌故事,许多歌师是经历了一场大病后突然开始会唱歌的,据这些歌师自述,他们唱歌的能力是在昏迷和恍惚中由祖先传授的,这充满了神秘色彩,无可考证。 传统苗族社会中,传习苗族古歌是社会生活中的神圣事件,充满神秘色彩,这与其对歌师的严格筛选和郑重其事的拜师仪式密切相关。仪式行为和复杂的程序使拜师学歌强化了族群记忆,成为苗族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升华意义的演述场域与禁忌规则 文化人类学者认为口传文学的演绎需要构筑特定的情境才能实现。他们通常从特定的仪式时空、表演形式、文本系统、叙事对象等维度对这种特定的情境展开分析,并将这种特定的情境称为文化的“演述场域”。巴莫曲布嫫也曾提出了传统在场、表演事件在场、演述人在场、受众在场,以及研究者在场的“五个在场”理论来阐释口传文学的演述场域。 梳理苗族古歌的各种出版文本或记录文本,演述的场域大致可分为三类:信仰祭祀场域、人生礼仪场域、节庆娱乐场域。从“传统在场”的视角看,苗族古歌在演述时对演唱语言和环境都有着严格的规范和要求,一般只在传统的节庆、婚礼、葬礼、农事活动、走亲访友等重大场合中演唱,非重大场合和重大节日是不轻易传唱苗族古歌的。苗族节庆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俗话说:“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各村各寨几乎天天都在过节。节庆文化是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以及各种文化风俗的凝聚形式之一,是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途径。苗族重要的祭祀活动如“祭鼓社”“祭稷柱神”“椎牛祭祖”“接龙”“还傩愿”“架地桥”“祭财门猪”“祭窝堆”等,重要的节日如“苗年”“姊妹节”“跳花坡”“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放社”“踩秧堂”“跳月”“赶秋节”等,都是演述苗族古歌的重要场域。苗族重要的人生仪式——出生礼、婚礼、丧葬礼中也必有古歌的吟诵。苗族是农耕民族,在其“起活路”“撒秧”“吃新”等重要农事活动中,苗族古歌也必然在场。苗族古歌演述形式的规范性、场域的重要性更加显示出苗族古歌演述的神圣和庄重。因此,苗族古歌一旦开唱,听者立刻肃穆,静静聆听,四座寂静无声。 每一次苗族古歌的演述都会有固定的场所和千年传习的禁忌,有着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古歌演述有特定目的,是仪式过程的重要部分。那些涉及信仰与神秘祭祀的苗族古歌,必须在特定的场合、时间由特定的人(歌师)去演唱,并伴随着各种仪式化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苗族古歌的演述场域不仅是一种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文化语境和社会心理诉求的因素也包含其中,营造出与古歌唱述内容相生相融的场域,强化了古歌唱述的效果。正如弗里指出的:“演述场域是指歌手和受众演述和聆听史诗的场所,这个场所通常是一个特定的空间。与其说它是一个地理上的界定,毋宁说它是特定行为反复出现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设定史诗演述的框架。” 苗族古歌唱述的规范其实就是吟唱的禁忌。所谓禁忌,包含了唱述内容的禁忌和唱述活动的禁忌两层含义。比如,《兄妹成婚》涉及苗族祖先亲兄妹成婚的隐私,为后世所忌讳,一般是不会在公共场合演唱的;《焚巾曲》只能在埋葬死者的当天夜里由巫师来唱,唱时焚烧死者生前的头巾、腰带、裹脚巾等;《洪水滔天歌》有缅怀祖先蒙难之意,不能在屋内唱;《亚鲁王》全篇只能在丧葬仪式上由东郎演唱,而且不能有半点错漏;《蝴蝶歌》非祭祖之年不许演唱,更不允许小孩子们唱,否则就是亵渎祖先,可能会因冒犯祖先而遭到惩罚。湘西苗族地区传唱的《火把歌》,吟唱时也要根据场合而定,一般原则是在丑事场合可以唱完七支火把的歌,而在好事场合则只能讲述喜事的内容,不能牵涉到丑事的话题。从江岜沙苗寨有着逝者安葬且众人离去后,由巫师一个人吟诵苗族古歌引导亡灵的习俗,且吟诵时不能被其他任何人听见,否则就会触犯神灵和祖先,给村寨带来灾难。 苗族学者杨元龙还谈到了搜集《祭鼓辞》时的艰难: 为抢救、搜集月亮山地区苗族吃鼓藏的祭鼓辞,我退休后重返月亮山采风,决心把祭鼓辞收集到手,由于工作关系,笔者与许多祭司已经很熟,但当笔者向他们说明来意,并请他们给予提供时,没想到却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说,他们可以给笔者唱古歌、故事,就是不能给祭鼓辞。问其原因,他们说不是他们不肯给,而是因为不是吃鼓藏的时候,念不得。祭鼓辞要在特定的时间(日、时、辰)、特定的地点(房屋中柱、大门内外、牛图、杀牛塘、树脚等)、针对特定的对象(祭品、牯牛、牛圈、大门、枫香树、水井、敲牛叉等)才能念。现在念了,祖先听到后,就认为寨子在吃鼓藏,就会来参加。如果不见有木鼓、看不见牛打架,不听芦笙响,姑娘不跳舞,更不见敬献给他们的鼓藏牛,寨上冷冷清清,一点不热闹那样,他们就会生气,家神野鬼就一起来找大家的麻烦,就会搞得人丁不安、六畜不宁,哪个敢啊。 可见,苗族古歌演述场域与其他口头文学,诸如神话、歌谣、故事的公共娱乐休憩性大相径庭,有着不可替代的仪式性、唯一性、神秘性和神圣性。 仪式化的苗族古歌吟唱过程 通过吟唱不同内容的苗族古歌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是苗族社会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仪式化教育模式。苗族传统村寨是一个个以血缘、地缘、亲缘构成的高度封闭的社会,村寨的集体生活、文化事项与个人生活融合混杂,难以区分。人们在集体共同事务如祭祀、扫寨、祈福、丰庆活动中,在家族的婚嫁丧葬事务中,在个人情感的悲欢离合中参与苗族古歌演绎,或听或唱或应和。吟唱过程既是现时性的集体接受,又是历时性的传统教化。一方面,现时性的接受过程发挥了极具感染力的剧场效果,人们的情感从中得到涤荡和熏陶;另一方面,历时性的传统教化实现了世代相传的宗教传统与文化记忆的灌输。一次次不同场域中苗族古歌演述过程的推进、道具的展示、场景的布置、歌师的歌唱与身体语言的配合、听众的行为,还有讳莫如深的禁忌所营造的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仪式化的苗族古歌吟唱过程,实现了一种“古歌吟唱”的文化内驱力的加速和文化意蕴的升华。 在那些隐藏于横亘高山、河水腹地的苗族村寨中,当一首首苗族古歌袅袅响起的时候,意味着歌者演述形貌与细节生动淋漓地绽放,也意味着吟唱过程中各种道具、唱词和行动的仪式性呈现。在苗族古歌的唱和中,一场场值得人们郑重对待的活动按照古老的约定和经验开始上演,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族群的记忆、历史、训诫,还有那亘古不变的精神气韵和神秘氛围扑面而来,一遍遍地唤醒和告诫着子孙。 《焚巾曲》是中部苗族黔东南地区的丧葬仪礼古歌,流传范围极广。该古歌内容丰富,不仅包括了族群起源、战争、迁徙和逝世者一生的经历,还包括给予逝世者的如何沿着祖先曾经的来路回家的指引。歌中对祖先曾经走过的各个地方的典型地貌进行了详细描述,还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民俗风情,仿佛一幅长卷的、极具感伤格调的风俗风景画,同时,这首古歌吟唱的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仪式展演过程: 《焚巾曲》演唱前,丧家先备好长桌一张(枫木树打的),摆在堂屋中央;桌上摆着熟鸭熟鸡各一整只(头反搁在背上,各插筷子一双于熟鸡鸭背上);桌上还有祭祖酒三杯,木升子一个;桌下置一笆篓,盛有一些稻谷(这是给歌唱者巫师的工钱),笆篓口有新白布两张(也是送给巫师);桌下还有木制脸盆一个,盛有少许清水,盖上新白布巾一张。歌唱结束时,焚此白布巾于木盆里。故亦名“焚巾”。 开始唱歌前,丧家宾主都聚集在堂屋里,围起桌子坐。由家族长老坐在桌边主持歌场。按丧家的老、新亲各门亲戚的顺序,逐门亲戚点名呼唤,请他们唱《焚巾曲》。被点唤到者均客气地推迟说不会唱,但愿出钱来请人唱。于是各各掏钱来放在桌上的木升子里(多少不拘)。然后主持歌场者才正式请巫师来唱。歌唱完后,主持人将笆篓口上的白布系于巫师手臂上,并将笆篓内的谷子给巫师。最后将客人买歌的钱分送给听众。 这段资料描述了吟唱《焚巾曲》的前后仪式过程。包括仪式前各种器物、祭品的摆放,人们的言行以及巫师怎么开始唱,歌唱结束后也有一系列的行为,吟唱苗族古歌的部分是仪式过程最主要的部分。 《扫寨辞》是黔东南扫寨(也叫“推火秧”)活动中唱的歌,或者说是活动仪式的唱词,仪式是这样进行的: 寨上(大家)筹钱买一头猪(无论大小),猪宰杀后砍成十二个“刀头”,加上猪肝、血、肺、心、腰(每样要一小点),十二坨米饭,香纸,十二个蚌壳酒,一杯清茶,猪肉和饭等。唱完一段词后,将其煮熟摆放。一棵五倍子树(削掉皮,露出白生生的树干、树枝),在其高为12米的地方,捆成四个杈杈,支架木皮或板子,上面放酒、刀头等,在寨子头(高的一头)进行扫寨(要单身汉来做,结过婚的不行)。 师傅身上斜挂一条白布,左手拿着锄头,右手拿着杆子。锄头把上捆一小条白布,刀把上捆几根青草,面对大树,面前放一双卦,然后口念(扫寨辞)…… 念完后开始下一段仪式,接着再继续吟诵《扫寨辞》,如此往复推进,直至完成全部仪式,同时该古歌也唱完了。 “仪式”在苗族古歌中的呈现 当一种传统文化逐渐蜕变成文学读本或者记忆时,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坚持对于个体来说只是个自由选项,而不是必选行为。无论沧海桑田、世事变迁,苗族一直保持着旺盛而蓬勃的生命力,这与至今以“活”的形态发展和传承的苗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苗族古歌中的许多篇章包含着大量仪式内容和传统文化,通过吟诵,强调族群传承千年的根谱、血缘、姓氏,缅怀征战与迁徙中祖先的伟绩与艰辛,饱含着对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鸟一兽不可言说的、无法割舍的深情。苗族古歌中大量仪式的内容,是族群关于神灵、祖先、故土与个体的所有亲属关系与族群认同,表现出强烈的、深刻的民族自觉性和民族自豪感。 苗族古歌中有关仪式的内容,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的叙述过程,有的再现话语,有的描写服饰,有的罗列器具,有的表达人对神的敬畏……《开天辟地》中有关于立房仪式的详细描述: 来看妈妈立仓房, 妈妈要立九柱房。 寅时寨里公鸡叫, 卯时天就蒙蒙亮, 妈妈匆忙去寨里, 去喊来个老巫师, 究竟喊的是哪个? 喊个巫师老人家, 纸条剪作鸡毛样, 撑把青布伞遮脸, 雪白公鸡拿手上, 时将白鸡扬一扬, 请嘎西来帮撑房。 嘎西山神下山来, 要立新房逗榫子, 妈的房屋才稳固。 这段歌把苗族建房仪式的规制唱得很分明:建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时辰应该做什么事、请谁来做建房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应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按照歌中的规制建房的好处是什么…… 《洪水滔天》古歌开篇第一节就呈现了开唱苗族古歌前祭祀祖先的仪式: 古歌有十二首, 《洪水滔天》别唱了, 昏天黑地难得走, 任你选唱哪一首; 如果要唱洪水歌啊, 把鸭杀了摆地上, 鸭子杀死再开口。 《金银歌》中有多处对选吉时祭天地、杀牯牛、造鼓祭祖仪式的描述,歌中唱道: 要是祭祖的牯牛啊, 它走了还留下犄角, 留着我们爹娘家里, 挂在中柱上。 挂给祖先看, 可是休纽走了, 犄角留在哪里呢? 挂在寺庙里, 挂在衙门里, 苗人汉人都看哩。 《古枫歌》中也记录了建屋以及新屋建成的仪式: 来庆贺他造新屋, 聪明善良的水龙, 挑根扁担颤悠悠, 这头一篮糯米饭, 那头一壶酒; 二钱银子啊, 揣啊揣腰怀; 咚咚叨叨放爆竹, 震得地动山发抖, 烟尘飞满天。 《蝴蝶歌》中有关于庆贺生子、击鼓祭祖、祭雷神、祭祖消灾、打猎祭祖仪式的描述,比如歌中描述祭祖的过程和穿戴: 拿双鼓去请亲戚, 请来了姐夫姑父, 把黎请来了, 把勇叫到了。 黎来黎带着东西, 勇来勇配着物件。 黎扛着一把大刀, 勇配来一柄长剑。 勇早起支锅, 央早起烧火, 热水来洗脸, 洗好了脸戴项圈, 戴好项圈插雉翎, 要去找鼓得打扮。 苗族古歌中的仪式内容告诉人们所有关于庆典、祭祀、避难、造物以及日常生活中行事的规矩与传统、行为的方式与禁忌,也告诉人们如何对待血缘关系、宗族关系、地缘关系与人情世故。在苗族古歌仪式内容的告知和指引中,人们将总结出的那些与宇宙天地自然相处的经验和基本知识,以及基于这种认知制定的规范和禁忌一代代承继。 综上,从苗族古歌的歌者、传承方式、唱述的内容、过程、场域与禁忌等各个方面来看,苗族古歌都显示出鲜明的仪式特征,呈现出显性的仪式性质或状态。换言之,苗族古歌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古歌唱述就是这种仪式的呈现和展演,可以说苗族社会的信仰体系、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主要通过古歌这一仪式活动的反复展演得以实现和维持。人们正是在苗族古歌千百遍重复的仪式性唱述中找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摘自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略有删减) 新 书 推 介 苗族古歌的审美研究 吴佳妮 著 2023年7月出版/168.00元 978-7-5228-1814-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苗族古歌作为“叙事性文本”,是中国古代“曲合乐曰歌”的一份珍贵而独特的鲜活范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自成一体,是苗族建构自身文化系统、维系族群生存与延续的活的“本文”。 本书选取苗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苗族古歌作为主要对象,并从“审美”和“仪式”两个独特而又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视角切入,从五个方面展开对苗族古歌美学的深入研究:一是在界定苗族古歌内容范畴和分类的基础上分析苗族古歌的仪式性特征;二是解析苗族古歌的审美动机;三是探讨苗族古歌的审美诉求;四是分析苗族古歌的审美想象、审美形态,进而探讨审美意识特殊性形成与表达;五是选取《亚鲁王》和《仰阿莎》两首颇具代表性的苗族古歌为范例,分别进行循序渐进的深度分析,呈现苗族古歌审美特征更为具体生动的样貌。 作者简介 吴佳妮,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贵州民族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研究等。在《中国出版》《贵州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获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持省、厅级社科及教改项目8项,参与完成各类旅游发展规划、地方标准制定等10项。 本书目录 向上滑动阅览 绪论 第一章 苗族古歌仪式 第一节 苗族古歌的分类 第二节 原始思维、神话与苗族古歌 第三节 作为特殊仪式的苗族古歌 第二章 人神沟通:苗族古歌的审美动机 第一节 苗族原始信仰体系 第二节 苗族古歌的审美动机 第三章 讲述与教化:苗族古歌的审美诉求 第一节 苗族古歌讲述的形式 第二节 苗族古歌教化的内容 第四章 混沌与秩序:苗族古歌的审美特征 第一节 苗族古歌的审美想象 第二节 苗族古歌的审美形态 第三节 苗族古歌审美意识的特殊性 第五章 两个案例:《亚鲁王》与《仰阿莎》的审美研究 第一节 神圣仪式中的苗族古歌《亚鲁王》 第二节 世俗生活中的苗族古歌《仰阿莎》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策划:佟 譞 编辑:王宇恒 审校:启 沐 转载自:人文万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