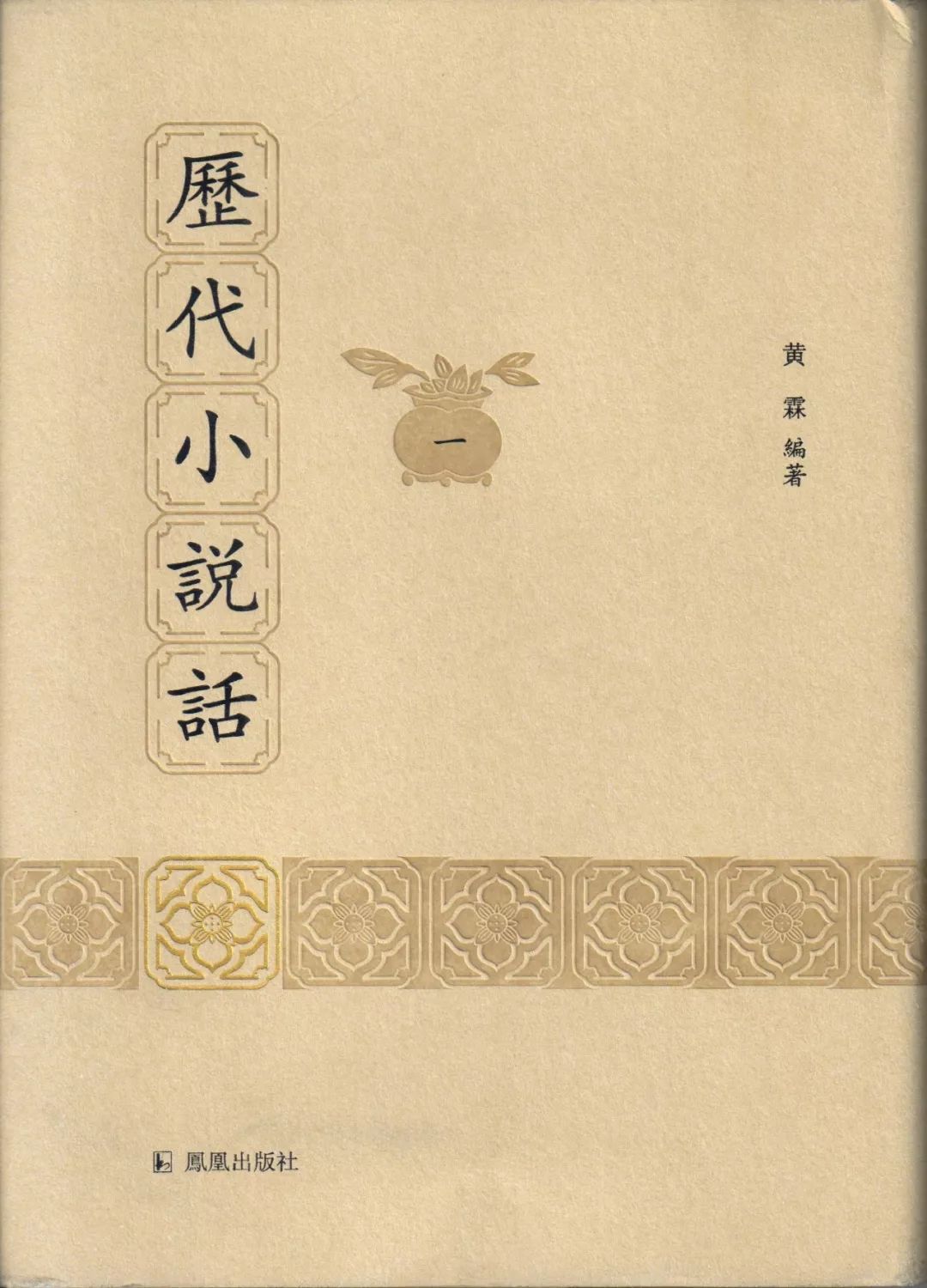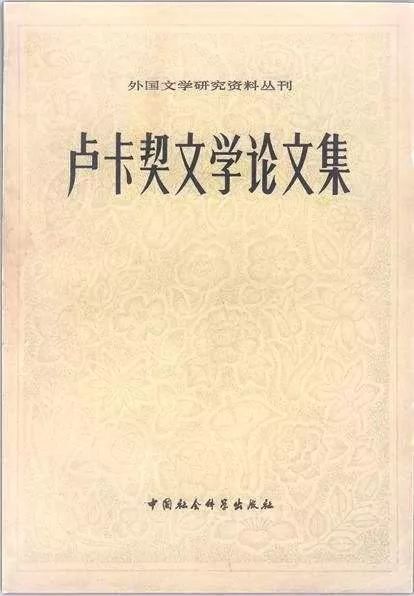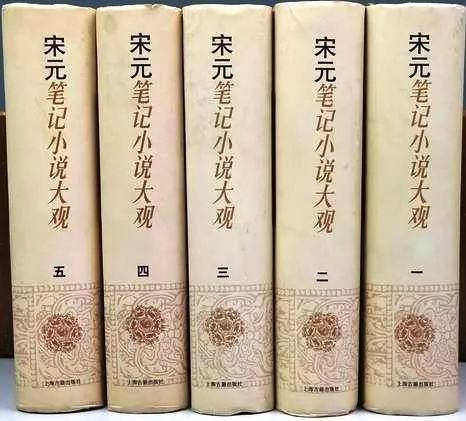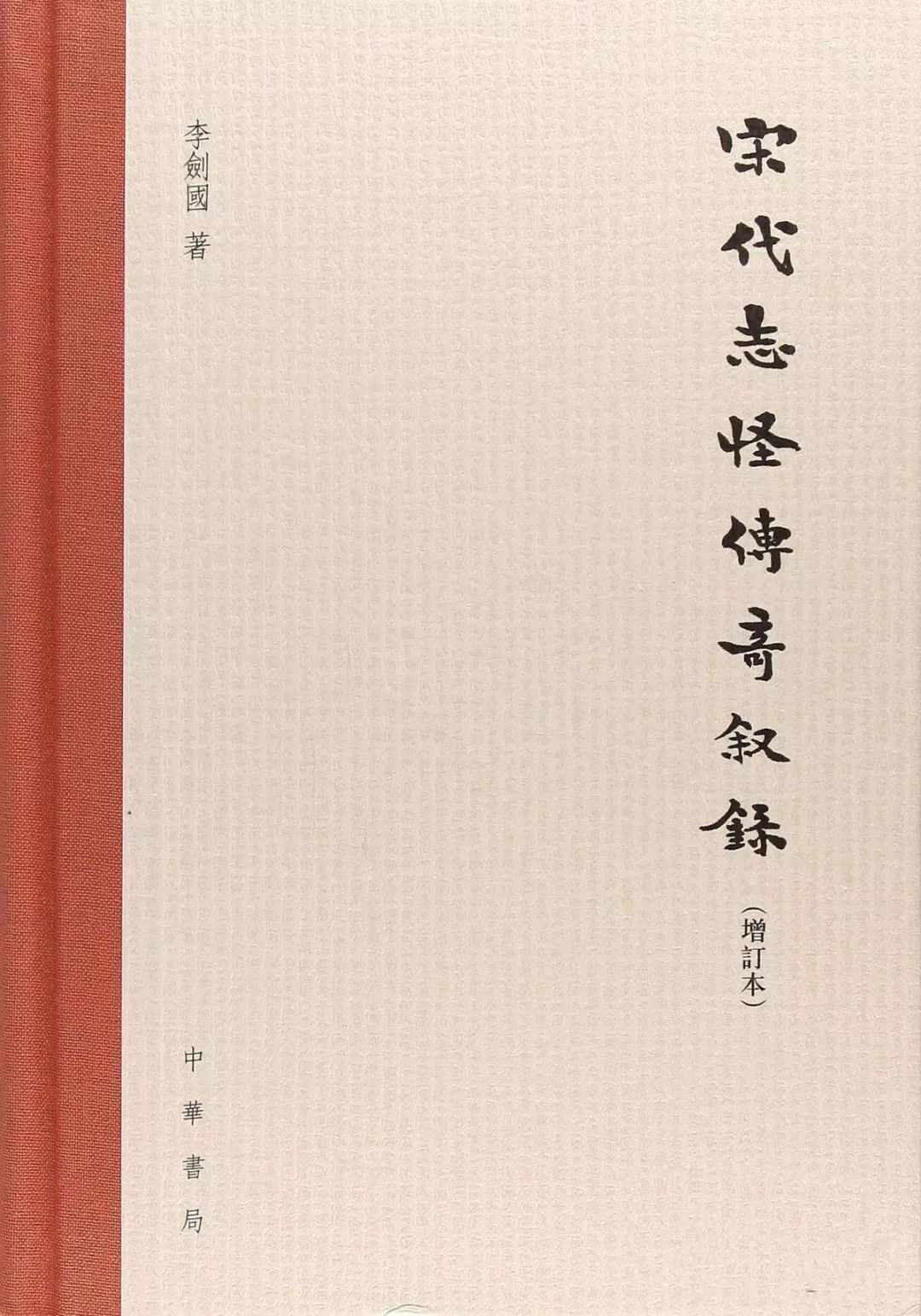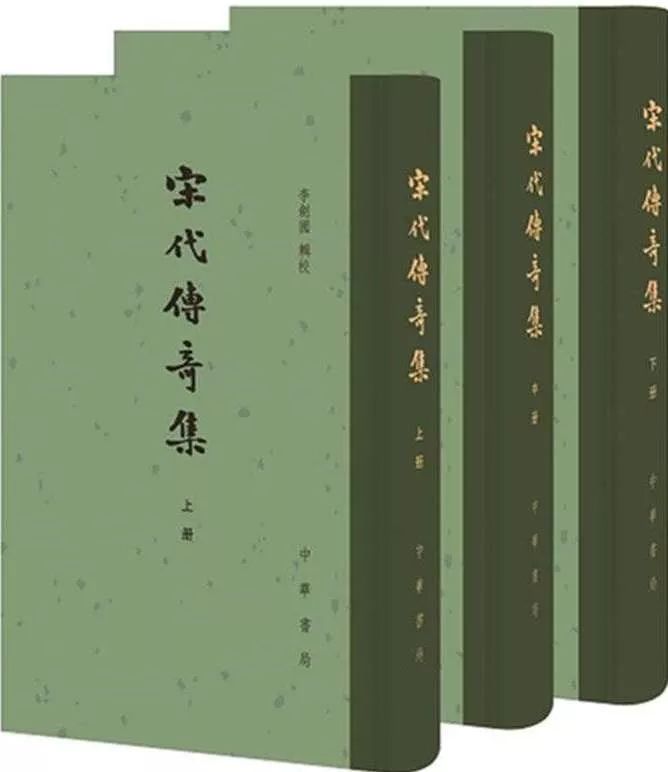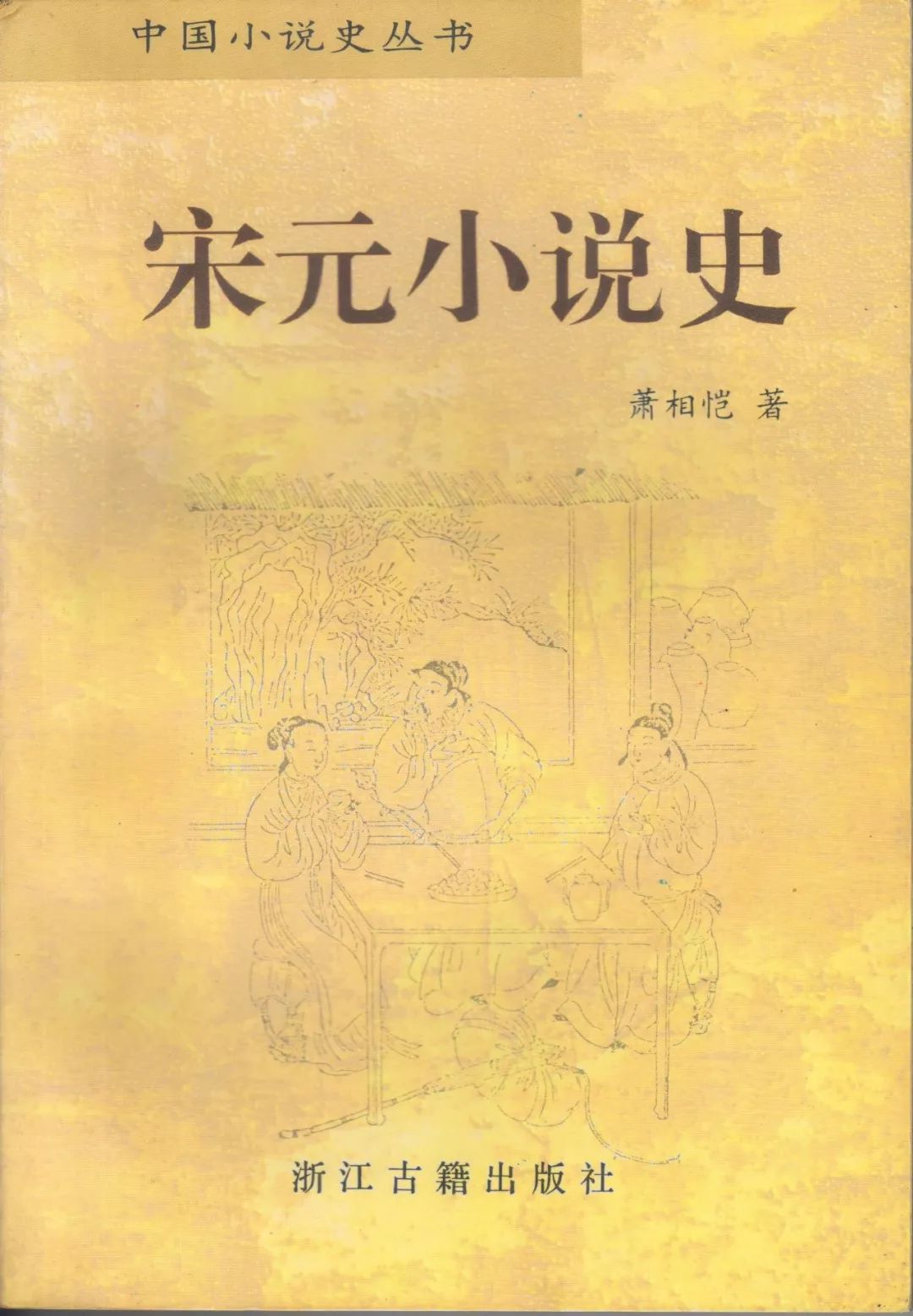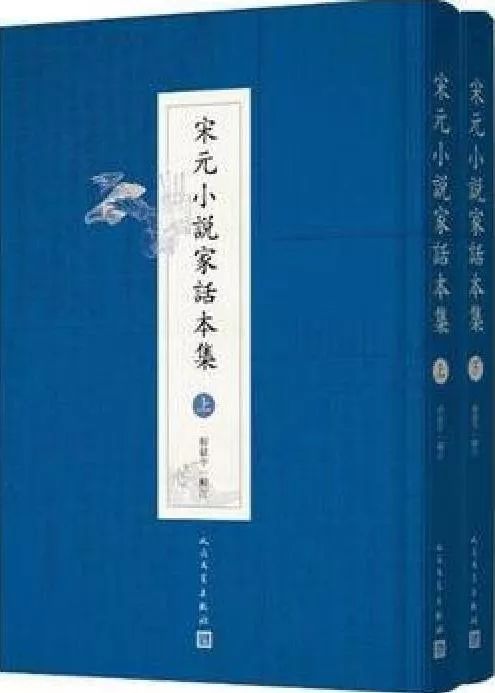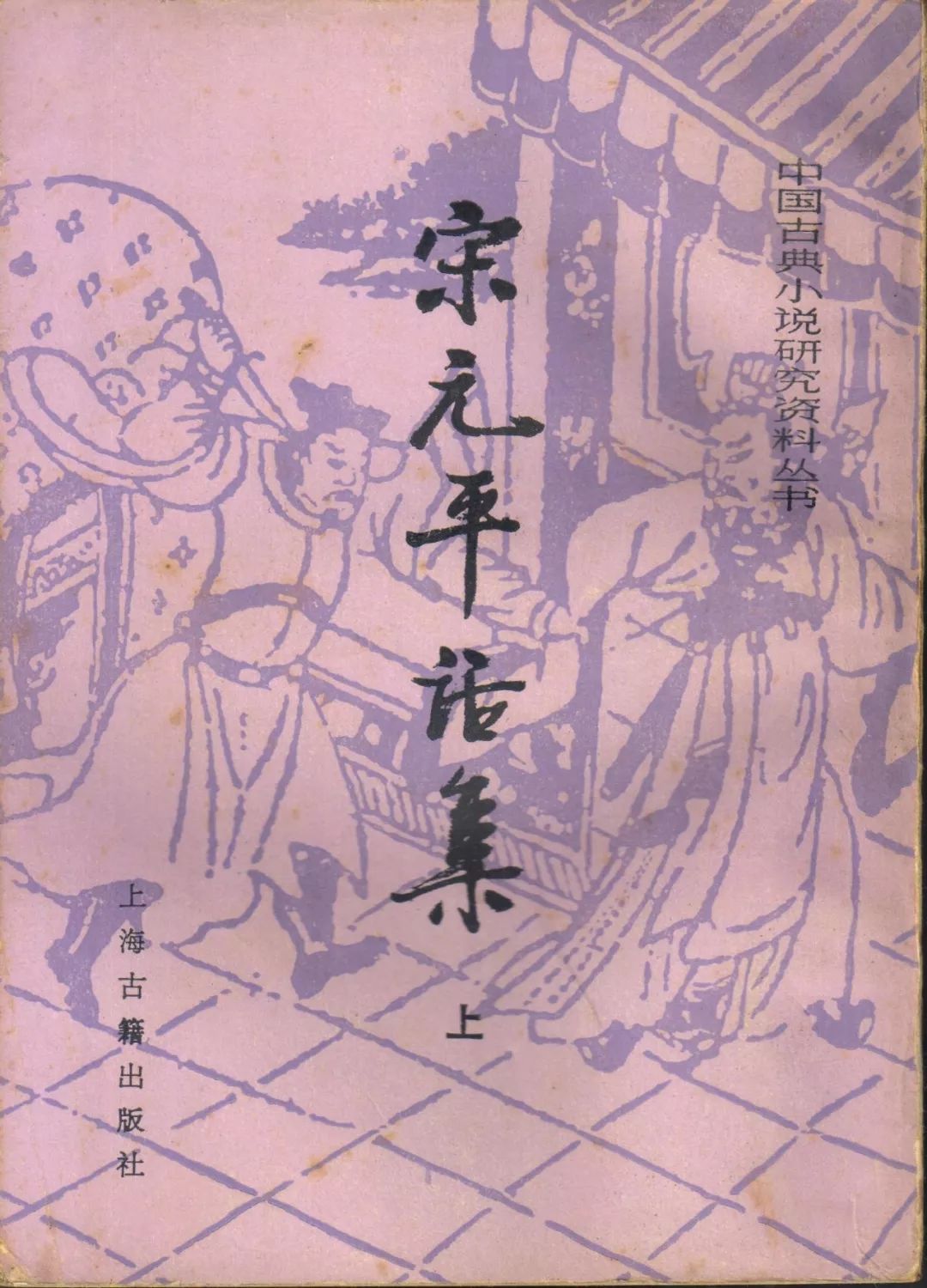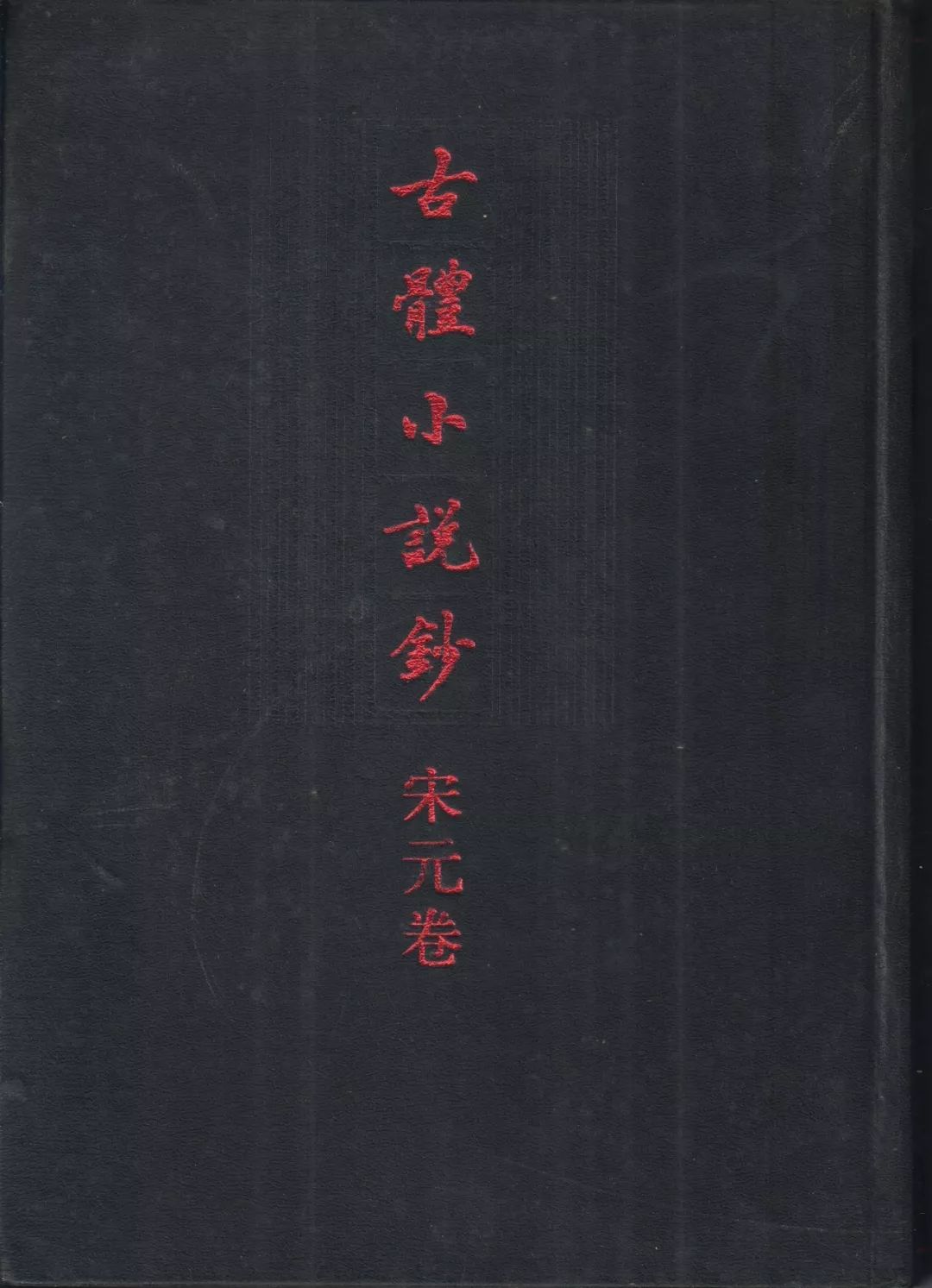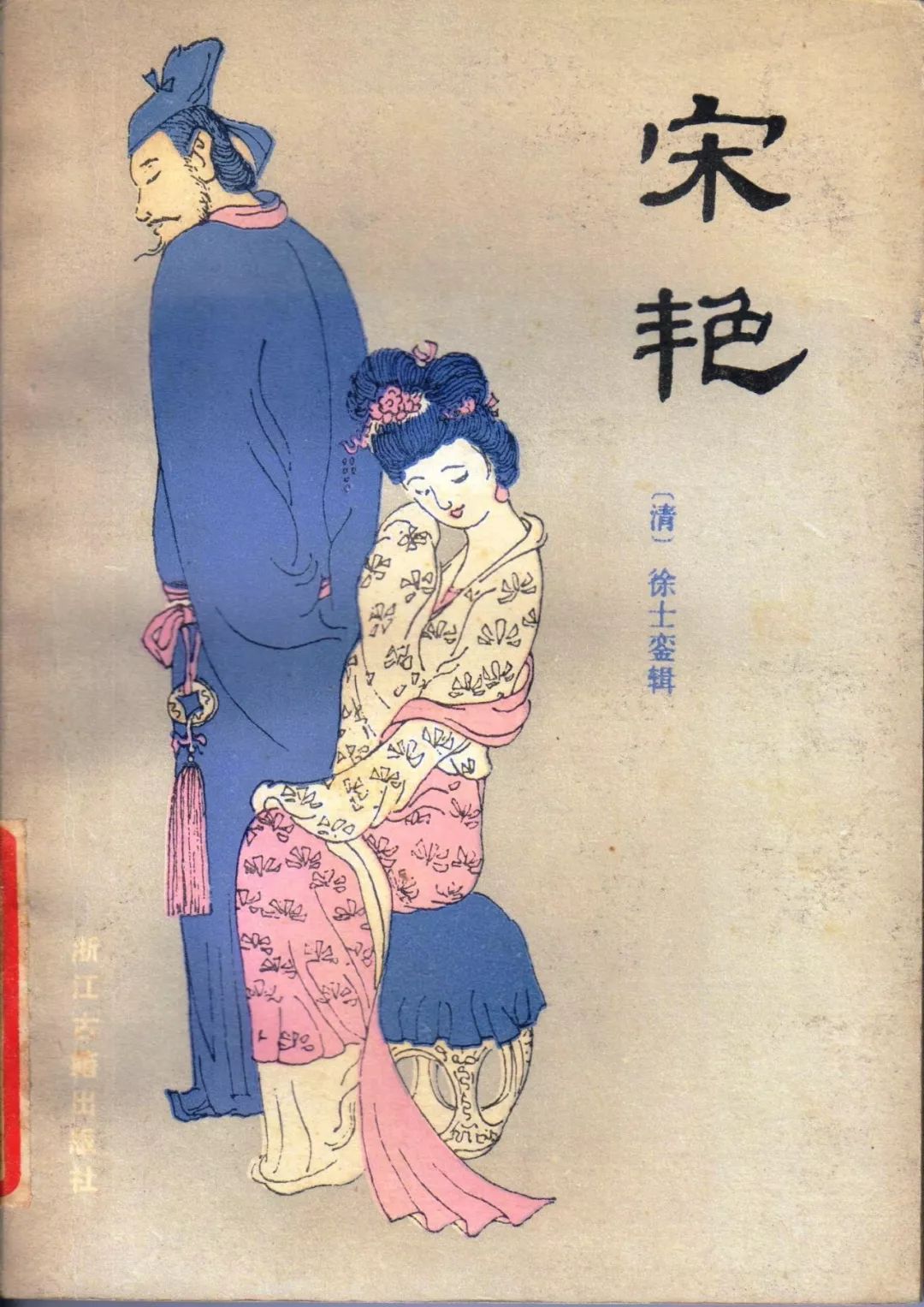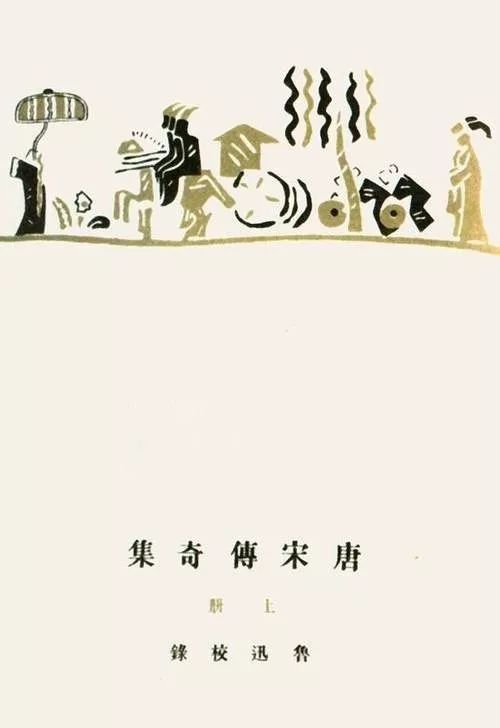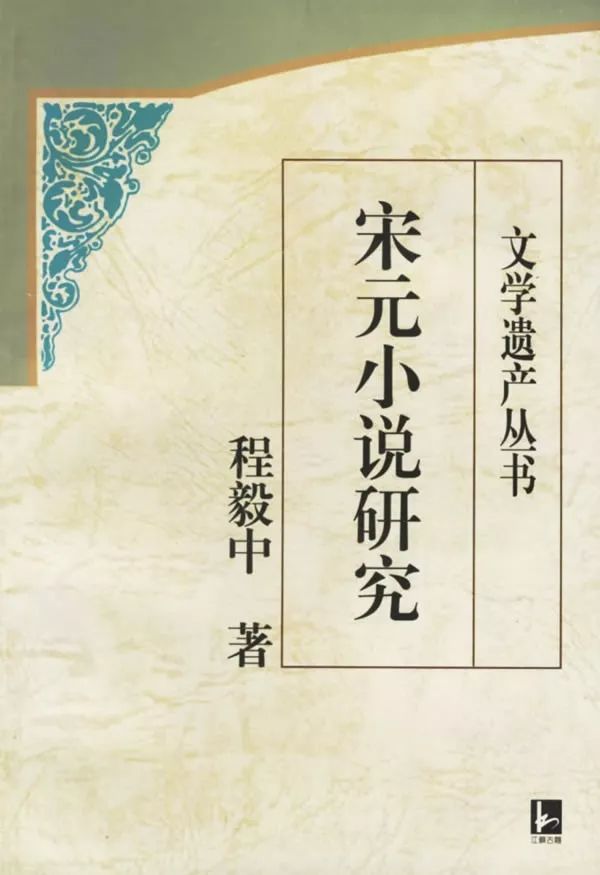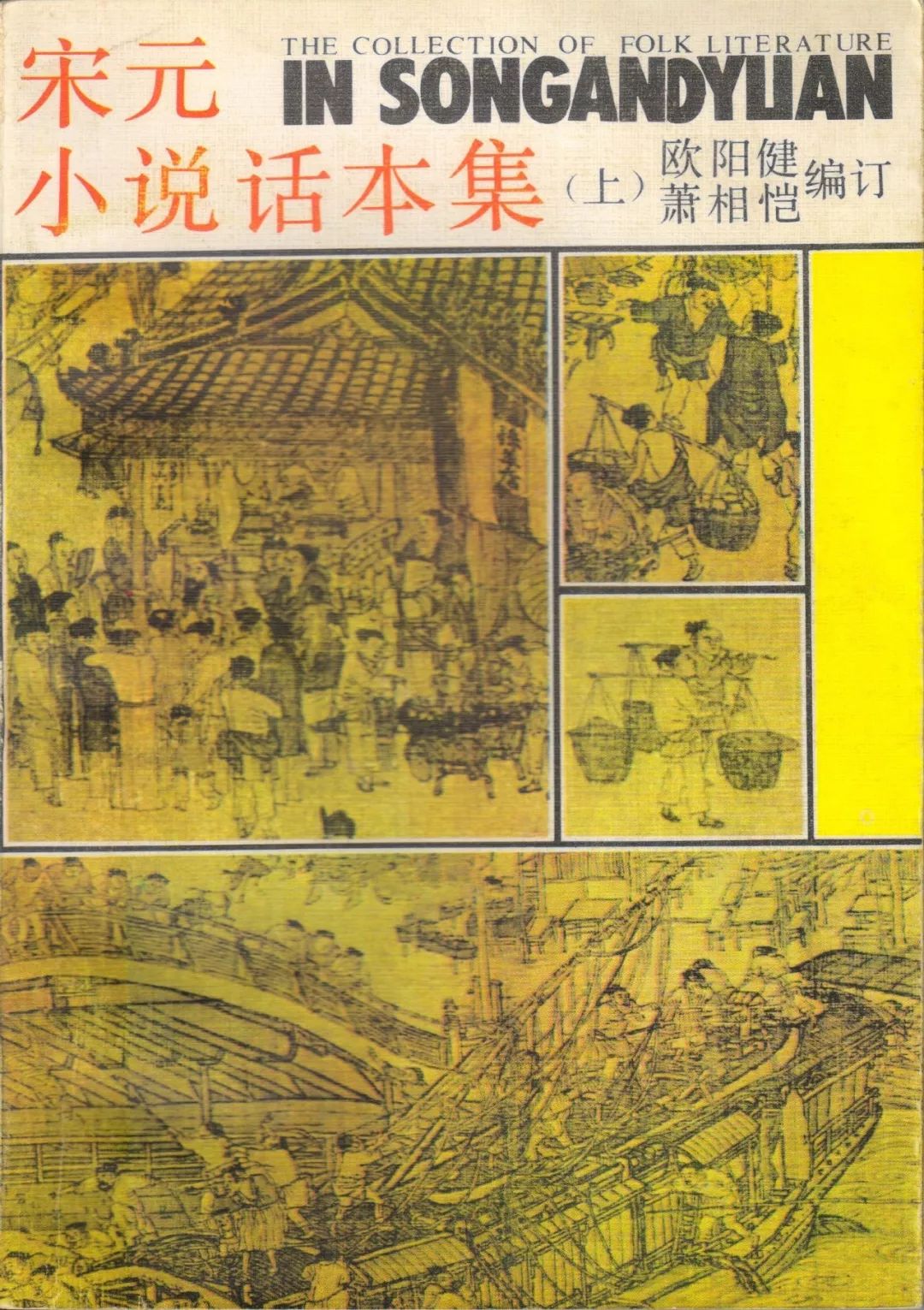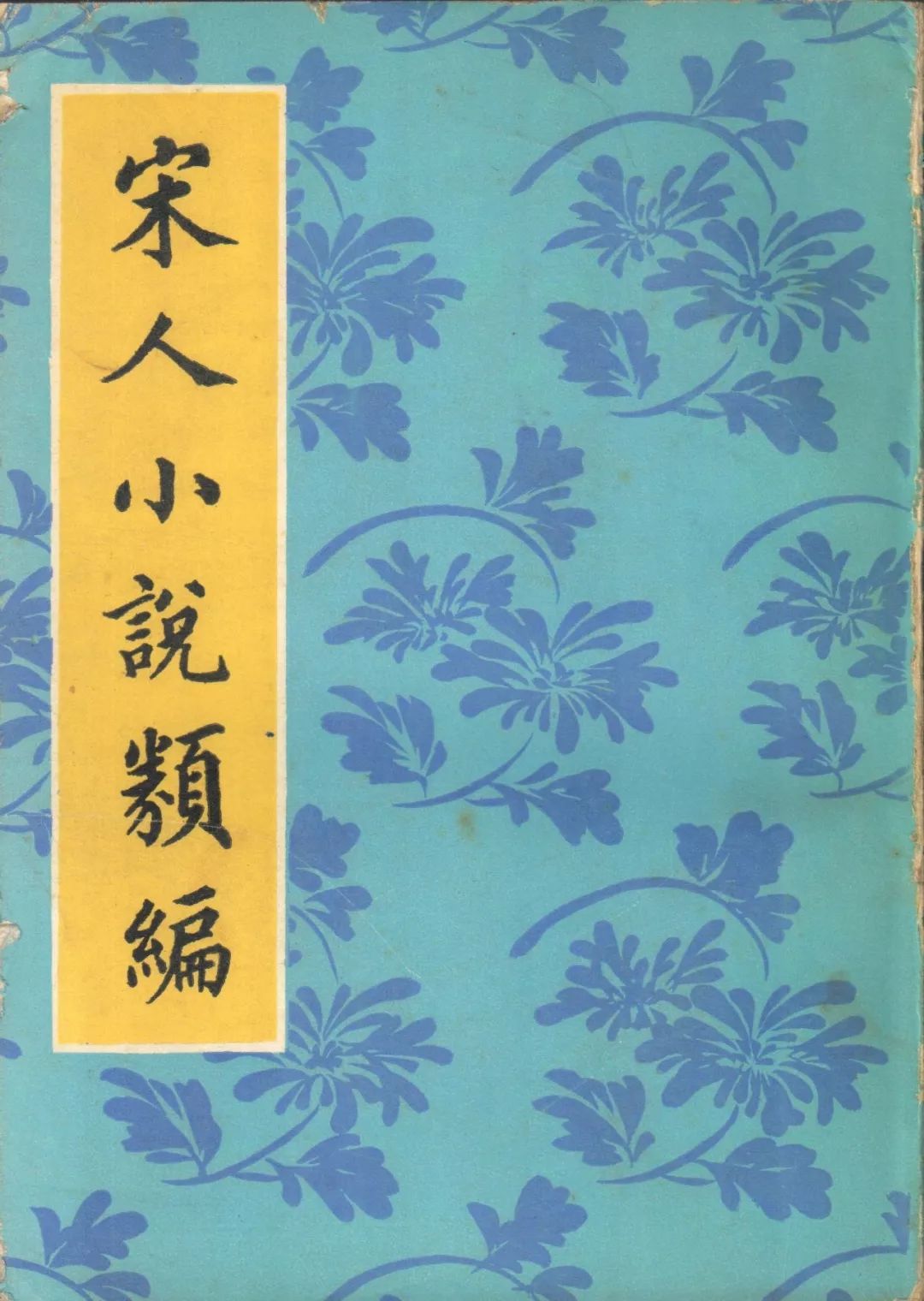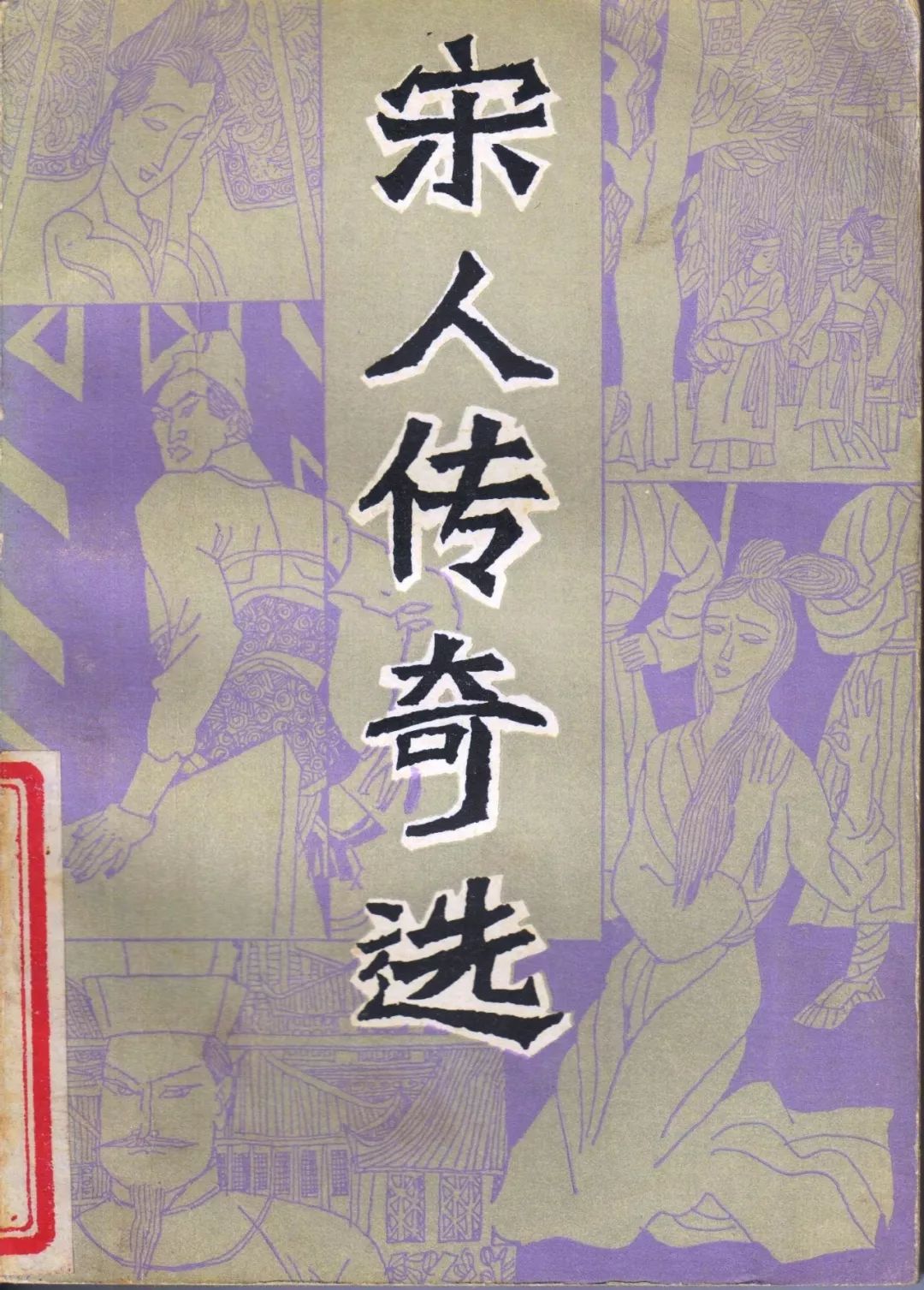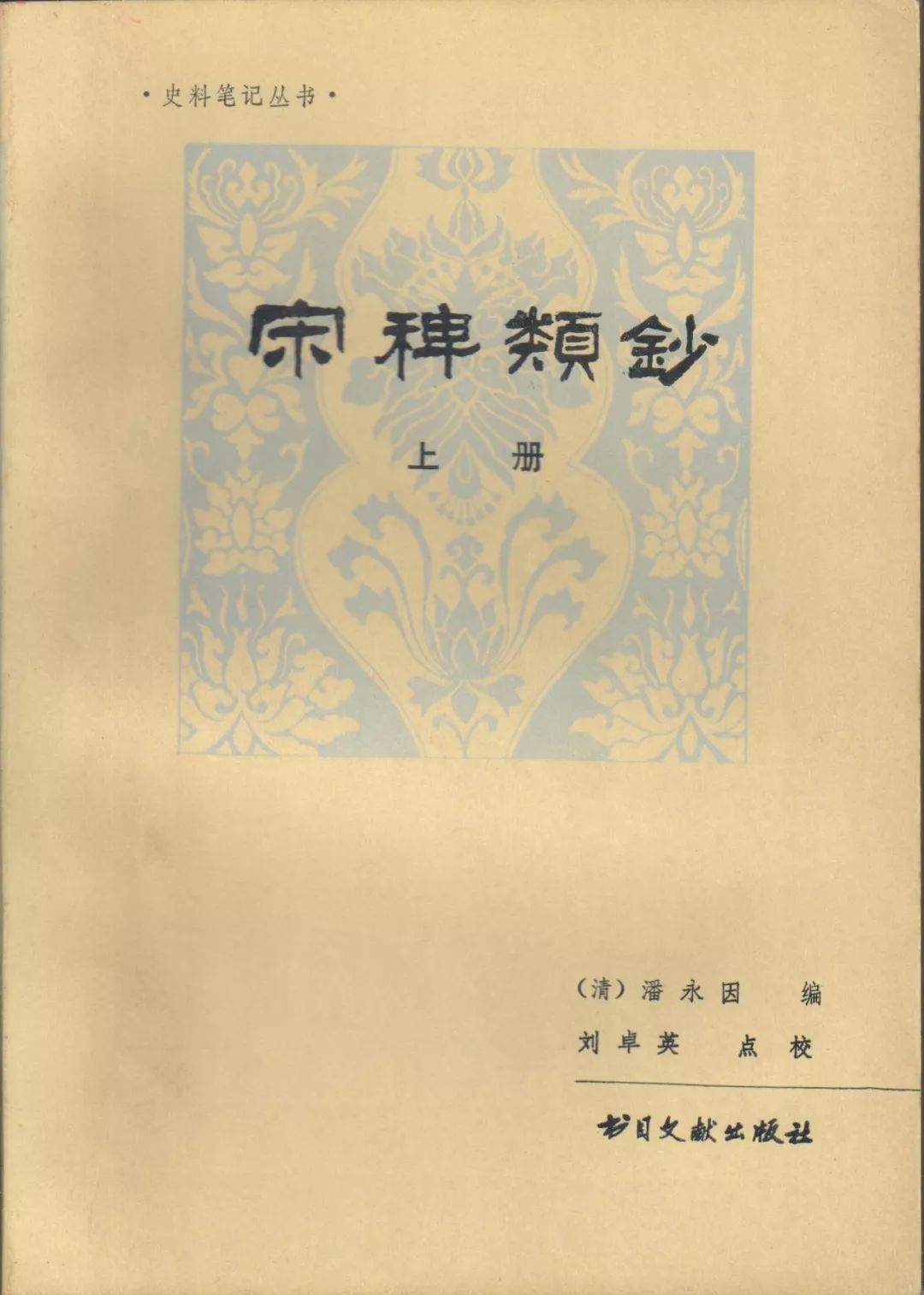| 李建军: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联合国旗帜图案取决于哪个故事里的人物 › 李建军: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
李建军: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
《小说鉴赏》 《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长篇小说是由情节、人物、场景或背景、叙述方法与观点、篇幅、神话/象征主义/意义等六个要素构成,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些法国新小说的创作者故意贬低人物这一因素,主张优先考虑对象和过程。但是真正的长篇小说家依旧是人物的塑造者”。西方无论三要素说还是六要素说,人物都是核心要素。 中国学者一般同意这样的观点:“环境、人物、情节构成小说的三大要素,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可见东西方学者大都意识到人物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 黄霖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点就是‘原人’,不但从‘人’出发和最终服务于‘人’,而且其理论的构建也是与‘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的面貌密切相关的。” 并进一步引申道:“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与小说理论时,是否能走自己的路,探索与总结一种立足在本土的而不是照搬或套用西方的、以论‘人’为核心的而不是以论‘事’为中心的理论呢?”
《历代小说话》,黄霖编著,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诚哉此言,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不能重“事”而轻“人”,仍旧需要“原人”(以人为本原)。 人物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不是仅仅充当行动元、发挥叙事中的结构作用。西方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常将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抽象化、符号化为结构成分,罗兰·巴特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人物的概念是次要的,完全从属于行动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说,可能有无‘性格’的故事,却不可能有无故事的性格。这一观点曾经为古典文学理论家们所重新阐发。人物直至当时只是空具其名,只是一个行为施动者……结构分析从一开始就极其厌恶把人物当作本质来对待,即使是为了分类。” 菲尔拉拉指出:“在虚构作品中,人物是用作结构成分的,即虚构作品的事物和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人物而存在的,而且事实上,正是通过与人物的关系它们才得以具备使自己产生意义并可以理解的连贯性和合理性的。” 但这样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另有学者仍将人物视为人性、个性、心理本质、性格类型等因素的载体,如乔治·卢卡契说:“人物只有在我们共同体验了他们的行动之后,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面貌,获得具有真正人性的轮廓。”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力图将上述两种观点融汇,如里蒙-凯南说:“在本文中,人物是语词结构的交节点,在故事中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前)语言的抽象物或构造。” 詹姆斯·费伦将人物看成叙事的一个因素,但同时具有三个维度——模仿的(作为人的人物)、主题的(作为观念的人物)和综合的(作为艺术建构的人物)。笔者赞同里蒙-凯南、詹姆斯·费伦的观点,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结构要素,也是“具有真正人性轮廓”的价值载体。 小说的人物塑造在展现“真正人性轮廓”之际,必然涉及人之为人的伦理属性。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援引署名阿伦的法国批评家观点,指出小说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表现“纯粹之热情,诸如:梦想、欢乐、悲哀以及一些难以或羞于出口的内省活动”,并认为“历史,由于只注重外在行动的缘故,必然要受命定论所左右。 而小说则不同,一切都体现着人性,认为现存的一切情感都是有意识的,甚至连热情、犯罪和悲痛也没例外”。强调小说“一切都体现着人性”,表现“一些难以或羞于出口的内省活动”,这就必然涉及人物的道德考量和伦理判断。
《荀子笺释》 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更为直接显豁。荀子云:“人之所以为人者,非持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又云:“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有辨”、“有义”等人的伦理属性一直是中国文艺作品表现的重点,宋代陈郁《藏一话腴》指出:“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 从写形、传神、写心三个递进的层面,强调展现人物“君子小人”之分、“贵贱忠恶”之别的伦理面相。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往往都有较为明确的伦理用意。 先看文言小说。洪迈撰《夷坚乙志序》明确提出“不能无寓言于其间”,其写人“丑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见之”、“丑而姓名不可不著者显揭之”,寓意则在“惩凶人而奖吉士,世教不无补焉”。 洪迈“寓言于其间”之论在文言小说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古代文言小说功能在“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其中“助名教”主要就是通过叙述人物的善恶与遭际的吉凶,托寓作者劝善惩恶的伦理用意。
清刊本《夷坚志》 再看白话小说。罗烨《醉翁谈录》作为宋人说话资料汇编,开篇《小说引子》即云:“自古以来,分人数等:贤者清而秀,愚者浊而蒙。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恶。好恶皆由情性,贤愚遂别尊卑。”从伦理道德层面区分人之贤、愚、秀、蒙、好、恶。 接下来《小说开辟》论及小说功效,又云:“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论及说话艺人通过塑造“国贼”、“忠臣”的人物形象,感动观众的同时又寓教化于其中。 说话是中国白话小说的重要源头,说话艺人通过人物塑形而托寓劝惩的叙事技法对白话小说影响深远。 小说在人物塑形中的伦理考量、伦理呈现乃至伦理教诲,是贯穿多数小说叙事伦理的一根红线。 叙事主体(主要指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层面的意图伦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技巧在文本中或隐或显地凸显出来,其中通过命运展示、遭遇讲述、关系设计、人物对比、人物评论等关涉人物塑形的方式呈现出来,无疑更为形象、效果更好。 故事层面的故事伦理,虽然侧重于分析小说题材、内容本身所蕴含的伦理意蕴,但人物塑形往往是故事外壳包裹中的内核,故事的伦理意蕴多数时候关联于人物善恶贤愚之品性及其决定的沉浮穷通之命运。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叙述层面的叙述伦理,关注叙述交流、叙事视角、叙事时空等叙事形式层面的伦理表达,也与人物塑形密不可分,因为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往往是多种叙事形式综合运用的结果,通过还原人物形象的伦理建构过程即可管窥到相应的叙述伦理。 读者层面的阐释伦理,关注读者阅读、接受文本过程中的伦理体验、伦理判断和伦理认同,其中人物性格及遭遇、人物伦理面相及命运,往往是读者进行伦理衡量的核心要素。 总之,从叙事主体、叙事文本到叙事受众整个链条,从意图伦理、故事伦理、叙述伦理到阐释伦理各个环节,人物塑形往往都是叙事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叙事伦理的重要依托和载体。 人物塑形和叙事伦理密切相连,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主体塑造的同一阶层(如士农工商)人物形象可能面貌迥异,叙事伦理也随之判然不同。 此处有必要说明一下,小说的叙事伦理具体到某个文本,也许“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但某个时代的小说文本的整体,还是会在叙事伦理上呈现出带有共性的时代特质,并涉及“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基本道德观念”。
《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从人物塑形的角度观察,某个时代、某类文化主体的小说文本在塑造某个阶层、某类形象时,会在叙事伦理上呈现某些共性。通过人物塑形寻绎出这些共性,可以勾勒出叙事伦理的时代演变轨迹,并从中管窥到“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的迁异曲线。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伦理在唐宋之际有一个转折,通过唐宋小说的人物塑形比对可以寻绎出这种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小说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两类小说的人物塑形、叙事伦理各具面貌但又有时代共性。立足宋代小说的人物塑形探讨叙事伦理,可以管窥中国从中古走向近世过程中的伦理迁异及其文学影响。 宋代文言小说可以分为笔记体和传奇体,其中人物塑形比较鲜明、叙事伦理比较显明者还是传奇体,故而笔者选取宋传奇为考察对象。 李剑国《宋代传奇集》辑录宋代130位作者创作的传奇391篇,囊括宋传奇的精华,本文即以此为据。
《宋代传奇集》 宋代白话小说即话本小说的判定,学界有较大争议,笔者综合胡士莹、程毅中、陈桂声等诸家观点,认为《碾玉观音》等35种小说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等3种讲史话本、另有1种说经话本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共39种话本小说的主体内容完成于宋代,虽后世有增删修润,但仍应判定为宋话本。 笔者下面即以这391种宋传奇、39种宋话本为基本素材,考察宋小说中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0 2 宋代小说的士人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与话本的编创主体、接受主体有士人与市民之别,两类小说分别反映着不同主体的文化精神和伦理意识。有学者已经指出:“文言小说基本属于由正统文人创作的士人文学,突出反映着士人意识和士人生活,与文人诗文具有相同的文学渊源以及相通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 宋传奇的创作和阅读基本上是在士人圈中,属于士人叙事。宋话本的口传环节是典型的市民叙事,编写环节虽然经过书会才人等文人的加工润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文人叙事的情趣和印痕,但主导性的还是市民情趣,因此宋话本的主体还是应归入市民叙事。
《宋元小说史》 1 宋传奇与话本中士人形象之异 宋传奇中的士人形象,从功名事业层面而言是多否少泰,从情爱婚恋层面而言是多离少合;而宋话本中的士人形象,从功名事业层面而言则多发迹变泰,从情爱婚恋层面而言则多如愿以偿。两相对照,可见宋传奇中的士人形象更多悲情色彩,而宋话本中的士人形象则更多喜剧情调。 这种人物塑形的差异可能与士人与市民的审美心理歧异有关。士人可能更多的以悲为美,创作者通过讲述本阶层人士的悲情故事、塑造士人的悲情形象,书写自己对于同类之命运的悲情感喟,并在感喟中获得美感,阅读者也从悲情故事的咀嚼、悲情形象的体认中获得美感;而市民可能更多的以喜为美,创编者和阅读者都乐于在浅俗的喜剧故事中获得虚幻的心理满足,而宋话本中的喜剧故事多以士人为主角,也隐隐透出当时市民阶层对士人的艳羡。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 2 士人形象差异的叙事伦理分析 宋传奇与话本中士人形象塑造的悲情色彩与喜剧情调之别,从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层面分析,会有更深的认识。宋传奇中负心婚变甚而存心骗财骗色的士人不在少数,叙事主体在塑造这类人物时大多会有比较显明的伦理判断,或者借助文本人物之口评价,或者通过篇末议论等方式进行公开的伦理介入。 宋话本中有轻诺寡信、儿戏婚姻的士人,但叙事主体并不进行伦理介入,反倒将其视为文人风流。宋话本中还有讲述名士前世乃是触犯色戒之僧人的“诨话”,叙事主体也不进行明显的伦理介入,而是着眼于此人此事的娱乐性。 宋传奇与话本中士人塑形的悲、喜格调之别,往往蕴含叙事主体的意图伦理考量。宋传奇通过士人的悲剧故事和显明的伦理介入,有强烈的劝善惩恶意图;宋话本偏重叙述士人的喜剧故事、风流故事,虽也有一定的劝惩意识,但伦理介入并不显明,叙事的优先考虑是娱乐性。
《宋元平话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评价《京本通俗小说》“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其中“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云云点出了早期话本乐(“娱心”)重于教(“惩劝”)的文本特征。 《苏长公章台柳传》、《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等宋话本用苏轼等士人的风流故事做猛料,并不是要从伦理上进行劝惩,而是借此娱乐观众,正是乐重于教的典型体现。 0 3 宋代小说的女性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与话本中的女性形象千差万别,同一类型的女性形象也往往面貌殊异,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其中丰富的文化意蕴。我们不妨把宋小说中主要的女性形象分为情女、贞女、仙女、浪女和娼女五种,下面分类考察传奇与话本人物塑形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叙事伦理。 1 情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清尊录·大桶张氏》、《夷坚志·鄂州南市女》、《投辖录·玉条脱》与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下简称《闹樊楼》)皆述“盗冢复生”故事,情节模式雷同,并都刻画了痴情女子形象,且文本间有承传关系,可以进行对比分析。
《古体小说钞》宋元卷 《闹樊楼》在改编文言小说之际,将故事时间设计为有较清晰的起讫时刻,即从春末夏初到次年二月间,总时长缩短为不到一年,而文本共七千字左右,因而文本呈现出缓速叙事的趋势,当然这两点(较清晰的时间设计、缓速叙事)也是大多数话本小说的共性。 《玉条脱》故事时间的长时段设计,最核心的是孙氏复活后“积数年”、“每言张氏,辄恨怒忿恚如欲往扣问者,郑每劝且防闲之甚”,可见孙氏对张生的怨怒“数年”犹存,这里反映出张生负约别娶带来了严重后果,折射出文本对张生儿戏许婚的道德鞭挞。 《闹樊楼》故事时间的缩短,有利于提高文本密度,凸显市井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急切和炽热,而将道德劝惩暂时隐退。 2 贞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和话本中都有不少的贞女(贞妇)形象,既有忍辱负重最终复仇者,也有刚烈不屈守贞完节者。比较而言,传奇中的女性有更强的道德意识,话本中的女性则有更强的生存意识。另外,话本中的女性更有斗争策略,更有市井女性的机警和坚忍。
《宋艳》 3 仙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传奇《花月新闻》与话本《董永遇仙传》都刻画了下嫁人间男子的女仙形象,可以进行对比分析。《剑仙》中的仙妇与《董永遇仙传》中的织女,都是由于某种因缘而下嫁人间男子的女仙,两者皆有美艳之貌,都有相夫之功,反映了男性作家们共同的心理期待。 当然,两者又有细微差异,前者(仙妇)具有贤明孝顺、宽厚慈爱等宗法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道德油彩,后者(织女)则更具市井女性较少道德约束的自在风习。两者的“同”反映出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同为男性性别叙事对女性的情爱期待,两者的“异”则反映出宋代士人与市民在女性伦理上的不同诉求。 4 浪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传奇《鬼董·陈淑》与话本《刎颈鸳鸯会》中的女主角都是水性杨花导致数位男人丧命的的浪女典型,可以对读。两个文本都通过女主角的毁灭表达了惩戒之意。但不同的是,陈淑与刘生的私通可能并非女方主动,而话本中的蒋淑珍,先后主动与三位男性偷情,显得更为放浪。
《唐宋传奇集》 实际上,如蒋淑珍等更为放浪的女性形象,可能才更加符合市井细民的审美情趣。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到,在塑造荡妇形象之际,士人叙事往往是穷原究委、重在惩劝,而市民叙事则是铺陈细节、劝百讽一。 5 娼女形象与叙事伦理 宋代文言小说集《贵耳集》、《浩然斋雅谈》和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以及话本《宣和遗事》,都涉及北宋末年名妓李师师,但形象差异极大,其中的伦理意蕴叵耐咀嚼。 就故事情趣而言,《贵耳集》、《浩然斋雅谈》两种文本,均将争风吃醋的狎妓丑闻美化为诗词风骚的文人雅谈,而《李师师外传》更是避开庸俗的三角情爱,叙述师师初“幸”于徽宗、后自杀保节之事,更显文人情趣和风节,这些文本都透露出士人雅趣,是典型的士人叙事;《宣和遗事》则津津乐道于李师师与宋徽宗、贾奕三角纠缠的低俗情节,充溢着市井俗趣,是典型的市民叙事。
《宋元小说研究》 就人物形象而言,文言小说文本中,《贵耳集》、《浩然斋雅谈》、《李师师外传》三种文本所塑造的李师师形象,或为雅妓,或为义妓,或为风雅义妓,都是文人妙笔将市井娼妓美化、典型化的结晶。 相对于文言小说文本中的雅妓、义妓,话本《宣和遗事》中的师师则是一位矫情卖俏的俗妓、精明狡狯的黠妓、重利轻义的陋妓,这是市民叙事中不是美化、而是俗化的人物原型,也许这才是市井娼妓的本来面貌。 就叙事伦理而言,《贵耳集》、《李师师外传》中叙事主体通过篇末议论进行的伦理介入,大义凛凛,鲜明表达出文本借师师其人其事,讽谏朝政、匡正伦常的政治用意和伦理用心。 而《宣和遗事》相关内容中的叙述者介入,当然也有伦理用意,但主要还是市民阶层的世俗告诫,与《贵耳集》、《李师师外传》伦理介入的高度不可同日而语。
《宋元小说话本集》 上面考察了宋传奇与话本中五类女性形象塑造及其叙事伦理,总起来说,士人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涂抹了更厚的道德油彩,寄寓了更多的伦理诉求,有更显明的意图伦理,折射出士人阶层的审美理想;而市民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少道德羁绊,更为接近人物原貌,折射出市民阶层的情爱期待。 0 4 人物塑形与宋代小说叙事伦理特色 宋代小说人物塑形的叙事伦理特色,通过唐宋对比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小说题材中,婚外恋、青楼恋与世俗伦理冲突最为激烈,其中人物塑形的伦理考量最堪玩味。 1 唐宋婚外恋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唐传奇《非烟传》与宋传奇《双桃记》都是讲述婚外恋的名篇,然两者的伦理意蕴大相径庭。《非烟传》文本自身并未透露出明显的劝诫意味,而是充溢着婚外恋悲剧所带来的审美震撼。 值得注意的是,篇末附有作者议论,曰:“噫,艳冶之貌,则代有之矣;洁朗之操,则人鲜闻乎……非烟之罪虽不可逭,察其心,亦可悲矣。”对赵象和非烟的婚外恋情予以批评,有垂诫之意。
《宋人小说类编》 但篇末议论的主旨判断“非烟之罪虽不可逭,察其心亦可悲矣”,与文本透露出的同情非烟之不幸而并不责之罪之的真实心态,两者是存有张力、油水分离的。 简言之,篇末垂诫只是强加上去的“蛇足”,文本自身并不在伦理化的劝诫,而是诗意化的审美。《双桃记》中,从文本故事到篇末议论都充溢着浓烈的伦理气息,呈现出典型的宋人面目。 同为婚外恋故事,唐传奇《非烟传》篇末议论(垂诫)与文本倾向(同情)的歧异,反映出叙事主体在伦理判断上的彷徨,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伦理评价上的矛盾,削弱了该篇的伦理力度;而宋传奇《双桃记》篇末议论与文本倾向的高度一致,使得该篇惩戒婚外恋的意图伦理非常显明。 2 唐宋青楼恋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 唐传奇《霍小玉传》与宋传奇《谭意哥》都是讲述青楼恋的名篇,但两者的人物塑形和叙事伦理差异甚大。
《宋人传奇选》 就《霍小玉传》而言,从伦理角度着眼,该篇并未赋予小玉形象过多的伦理意蕴,而主要是通过悲剧结局,谴责李生背盟负约的伦理背叛。 《谭意歌》中的青楼女子谭意歌自尊自立,渗透着宋人强烈的伦理意识。如果说唐传奇《霍小玉传》的意图伦理主要是惩男主角之“过”,那么宋传奇《谭意歌记》则主要是扬女主角之“善”。 婚外恋、青楼恋题材的伦理差异基本可以折射出唐宋传奇的伦理选择,概言之,可谓唐人更宽松、宋人更严苛,唐人或不将劝惩作为文本重心,或进行伦理判断时彷徨游移、出现篇末议论与文本倾向的歧异,宋人则通过叙事主体精准的伦理介入,使文本的意图伦理非常显明。
《宋代小说考证》 相较唐传奇,宋传奇人物塑形中有更为显明的意图伦理,叙事主体有更为精准的伦理介入,反映出宋代士人叙事更为强烈的伦理诉求,当然这只是宋代小说叙事伦理的一个侧面。 另一面是宋话本所反映的市民叙事“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人物塑形的道德羁绊较少,伦理诉求逊于娱乐需要。宋代士人叙事的教重于乐与市民叙事的乐先于教,构成宋代小说叙事伦理的丰富面相。 值得注意的是,宋小说还存在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双向互动的情景,传奇借鉴市井文艺而呈俗化之势,话本吸纳士人文学而有雅化之风,但总体趋势则是叙事文学更为世俗化,士人伦理有向市井伦理滑动的趋势,世俗化传奇如《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等作品中士人气质的平民化、士人伦理的市井化堪称典型。
《宋稗类钞》 宋代小说中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的互动,使叙事技巧更为丰富,士人伦理与市民伦理的互渗,使文本伦理更趋世俗,这就从叙事和伦理两个维度推动着叙事伦理的变迁,使得宋代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此文原文刊于《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约20000字。此为精简版,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