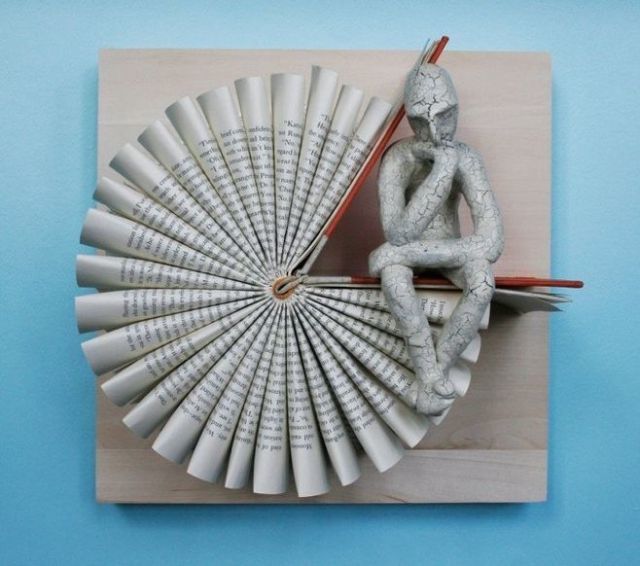| 宗争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符号学理论基础是什么学科 › 宗争 |
宗争
|
符号学与现象学是当代人文社会学科中两种重要的理论。赵毅衡先生明确提出了“符号现象学”,并努力将其拓展为一整套系统的理论表述,以期为符号学研究奠定哲学理论基础。寻找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是符号现象学的基础问题。赵毅衡先生试图从皮尔斯的哲学入手,来构建符号现象学的基本框架,但是他有意避开了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论争。事实上,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开创者,同样表现出对符号问题的极大热情,而他关于符号问题的探索,同样应该成为符号现象学构建的有力支撑。 关键词:现象学、胡塞尔、符号、符号现象学 一、“符号现象学”的提出 2015年,赵毅衡先生明确提出了“符号现象学”的概念,他接连发表了数篇论文论证,符号学与现象学——这两个原先彼此相对独立的学科——具有某种结合的可能性。当然,这一词语此前也被提出并使用过,譬如四川大学哲学系的黄玉顺先生的论文《符号的诞生——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符号现象学问题》等,在标题和正文中都提到了“符号现象学”。但这些文章主要是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论域入手,探究现象学中关于符号的种种设定,与赵毅衡的“符号现象学”大相径庭。这一论域(即符号与现象学、符号学与现象学)亦有前人涉及,如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德里达对“声音与现象”问题的讨论、近人如拉尼根和索乃森等。 赵毅衡主要是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的理论角度来重建“符号现象学”的,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有很大的差别。皮尔斯称:“我将哲学分为三个部分,即范畴学,规范科学(包括美学、伦理学与逻辑学)以及形而上学。”(皮尔斯,2014,pp. 101-102)皮尔斯这一构想,几乎重构了传统哲学的学科框架。其中,范畴学即现象学。而他将符号学基本等同于逻辑学,置于“规范科学”这一门类之下,声称“在一般意义上,逻辑,正如我已表明的那样,只是符号学的(semiotic)的另一名字。”(2006,p. 276)因此,在皮尔斯那里,现象学与包含着符号学的规范科学是两门平行学科。然而,皮尔斯的所谓“现象学”或“显像学”,其实是皮尔斯庞大哲学构想中的一部分,并不是一门纯然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逻辑关系。从这一角度,我认为,赵毅衡的“符号现象学”的理论基础是寻找皮尔斯理论中两个学科的结合部,因为在皮尔斯那里,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出现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赵毅衡称:“符号现象学应当如皮尔斯所考虑的那样,是符号学理论的一部分,是从当今的符号学(而不是现象学)运动的需要出发,重建符号学哲学基础的努力。”
(胡塞尔 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问题在于,鉴于胡塞尔在创立和丰富“现象学”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现象学”一词时所遵循的基本理论语境,我们都很难绕过胡塞尔而只谈皮尔斯的现象学。因此,所谓的“符号现象学”,如果它是一个负责任的理论表述的话,至少应当对于其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进行必要的说明。 而事实上,赵毅衡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意义对象的“非匀质化”》等论文中,其实已经顾及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相关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引述、使用、辨析胡塞尔的理论与术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诸多论述之中,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论争,而恰如赵毅衡自己的解释:“这不是‘符号现象学’有意扭曲‘现象学’。作为意义理论基础的符号现象学,只是回顾并吸收现象学的一些方法,应用于符号学的基础建设。它与现象学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看法可以不同,因为各自的论域很不同。”(2015)如此看来,符号现象学方兴未艾,在理论构建和推演应用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那么,是否“符号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又是否“符号现象学”只能从皮尔斯理论中另起炉灶,而无法与胡塞尔现象学形成有效的融合?又或许我们可以藉对胡塞尔的重新梳理,来找到用以丰富符号现象学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资源。 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概念 我们知道,胡塞尔现象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即是“本质直观”,他强调先验自我对对象的先行把握。简言之,本质即是事物之间的范畴与形式关联,它并不是人们从对事物的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而是意识结构的自明性。事物不能自我显现其意,或用康德的说法,“物自体”是不可认识之物。事物投射到意识屏幕上即为现象,人类的意识只能认识现象,而意识总是关于某物(对象)的意识,那么,意识的本质就是意识与对象之间的这种具有指向性的关系,胡塞尔称之为“意向性”。而现象学的根本可以说就是意识研究,或意识的意向性研究。 胡塞尔的理论视野聚焦在现象学上,他并不是一个符号学家。但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却无法回避语言与符号等问题,事实上,符号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中并不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符号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域。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表达与含义)、第二研究(种类的观念统一与现代抽象理论)、第六研究(现象学的认识启蒙之要素)等部分,都与“符号”、“含义”等问题息息相关。“事实上,通过迎娶现象学哲学的意向分析,符号学思想能得到的嫁妆,远比想象中来得丰赡和具体得多。”(董明来,2012) 国内胡塞尔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倪梁康认为,可以将胡塞尔的意识行为过程区分为四个层次:1、感知;2、奠基于感知之上的想象,感知与想象一同构成直观行为的基础;3、直观行为与奠基于直观行为之上的非直观行为(符号意识、图像意识等)一同构成客体化行为的基础;4、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共同构成主体的意识行为。(2003)而符号行为发生在第三个层次,对于具体符号的应用而理解则显现于第四个层次。
面对事物,感知与想象是第一性的,“现象”即是事物在意识屏幕上的投影。对胡塞尔而言,感知是第一性的行为,它与“想象”构成了“直观”的行为类型。这一观点并不是胡塞尔的首创,它几乎是西方哲学的共识。康德就提到:“有三个本源的来源都包含有一切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并且本身都不能从任何别的内心能力中派生出来,这就是感官、想象力和统觉。”(2004,p. 85)在这上面就建立起了通过感官对杂多的先天概观,通过想象力对这种杂多的综合,通过本源的统觉对这种综合的统一。 仅仅有感知和想象还不足以支撑一个完整的认知行为,我们的意识驱动我们,对直观的体验进行统摄,以及表达。这种“统摄”,康德称为“统觉”,胡塞尔则称之为“立义(Auffassung)”,就是意识活动的一种特殊的功能,“意识活动之所以能够构造出意识对象,是因为意识活动具有赋予一堆杂多的感觉材料(立义内容)以一个意义,从而把它们统摄成为一个意识对象的功能。……杂多的感觉材料通过意义的给予而被统一,从而一个统一的对象得以成立并对我显现出来。”(倪梁康,2007,p. 61)这个词的英文译法apprehension似乎更容易理解,即我们面对感觉材料时,如何进行理解,因为感觉杂多本身不具有意向性,意识就要赋予其一条可以被理解的途径,因此,主体对事物的认识其实是意识建构意识对象的过程。“理解”自然是对意义的理解,中文译为“立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在字面上对“所立之义”、“赋义”有所强调。“对象”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是指“一个东西被意识到并相对意识而立”(倪梁康,2007,p. 179),这个概念基本上可以通约到西方主体哲学的研究中。对象的确立,或者说客体的确立,本身就意味着主体的同时确立,主体性的彰显,而主客体的确立,是主体哲学的研究基础。哲学研究所要面对的并不是“感觉材料”,而是“对象”。 胡塞尔将立义分为两种:“对象性立义”与“理解的立义”。对象性立义也被称为“第一性立义”,“意味着对感觉材料的加工和统摄,并在此基础上使对象在直观中得以产生。”(倪梁康,2007,p. 63)而“理解的立义”是“第二立义”,奠基于“第一立义”,“在这种理解的立义中进行着对一个符号的意指,因为每一个立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理解或意指,这种理解的立义与那些(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客观化的立义是很接近的,在这些客观化立义中,对一个对象的直观表象(感知、虚构、反映)借助于一个被体验到的感觉复合而产生给我们。”(胡塞尔,2006,pp. 84-85)对象性立义,其实就是在直观行为中进行的立义,而理解的立义则利用了符号意指,胡塞尔也因此称前者为本真的,后者是非本真的。 感觉材料被意识所把握、统摄、立义,被构造成为与主体相对的客体,这一过程就是意识对对象的构建过程,胡塞尔称之为“客体化行为”。胡塞尔将意识行为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诸如陈述、判断等具有认知性意识的活动属于客体化行为,这些行为对对象具有构造作用,而诸如意愿、评价等价值性意识活动则属非客体化行为,它们无法构造对象。而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构成了完整的“意识行为”。
(图片来源于网络) 意识行为需要展现自身,需要借助“表达”,只有被表达、被表述,意义才可能得以凸显。在胡塞尔那里,“表达”是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术语,并不仅仅指言说或书写。表达必然对应着被表达的对象,更准确地讲,表达是使对象得以显现。而“表达”的主要功能是“传诉含义”,其过程通常要使用具体的符号。 在《逻辑研究》中,“第一研究”即为“表达与含义”,胡塞尔在“符号这个概念的双重含义”一节中,明确提到了“符号的概念”。他称:“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一个借助于符号而表达出来的意义。”(2006,p. 31)根据“是否具有含义”,胡塞尔将“符号”分为两类:指号和表达。前者没有含义,“在指号意义上的符号不表达任何东西,如果它表达了什么,那么它便在完成指示作用的同时还完成了意指作用。”(2006,p. 31)后者则是“作为有含义的符号”(2006,p. 39)的“表达”。 胡塞尔之所以要将符号进行这样的区分,很可能是基于一种逆向思维:胡塞尔意识到了作为符号的“语言”在表达意义上的重要性,“语言阐释肯定属于为建造纯粹逻辑学而必须做的哲学准备工作之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阐释才能明晰无误地把握住逻辑研究的真正客体以及这些客体的本质种类和区别。”(胡塞尔,2006,p. 40)因此,必须在现象学中处理这一重大课题,但旋即发现语言仅仅是符号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并不能以偏概全地涵盖所有关于符号的分析,因此,它将与语言相似的表意系统统合为“表达”符号,而将“标志”、“标识”等统合为“指号”。 显然,符号问题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那么,在胡塞尔那里,符号究竟是什么呢?胡塞尔所做的,恰恰是对“符号”做现象学的还原。换句话说,他所关注的是在意识行为之中,意识主体为何并如何选择符号进行意义的构建活动。因此,在胡塞尔看来,符号、符号意向、符号意识、符号行为等术语具有理论的一致性,而他几乎也是不加分别地使用它们。 综合胡塞尔关于符号问题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胡塞尔对于符号的界定:首先,胡塞尔基本上是在“符号意识-符号行为”这个维度来谈论符号问题的,因此,他无法也没有必要给出关于具体“符号”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定义。而“符号意识-符号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符号行为是非直观行为,它奠基于感知、想象所构建的直观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称,符号行为其实是对直观行为的代现。 二、符号行为是一种重要的立义方式,具体表现为: (1)符号行为本身没有属于自己的感性材料,它必须借助于直观行为来获取自己的可感表象。称符号“行为”没有感性材料,并非“符号”没有感性材料,例如,言语的声音形象、字符的笔划等都是可感的,它们首先诉诸于直观,但符号行为借助了它们,赋予它们与其感性材料并无直接关联的含义。 (2)符号与含义之间不具有必然性联系,符号与含义之间的关系是意识刻意构建的。“一个符号意向的特殊本质就在于,在它那里,意指行为的显现对象和充实行为的显现对象(例如在两者现实统一之中的名称与被指称之物)相互间‘没有关系’。”(胡塞尔,2006,p. 60)在这里,符号行为其实是作为一种“中介”出现的,一方面是直观可感的感性材料(声音、笔划),而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对另一对象的含义。在这个过程中,符号行为所借助的感性材料并没有意义,它用以代现另一对象的意义。“在质料和被代现者之间的符号代现所建立的是一个偶然的、外部的联系,而直观代现所建立的则是一个本质的、内部的联系。在前一种情况中,偶然性在于,可以想像在同一个符号行为上附加任何随意的内容。符号行为的质料只是需要一个支撑的内容而已,但我们并不能发现在它的种类特殊性和它的本己种类组成之间有必然性的纽带。”(胡塞尔,2006,pp. 96-97)这看起来似乎与索绪尔的经典概念“能指/所指”非常相似,但其实有本质上的区别。索绪尔只是指明了符号的内在结构,而胡塞尔关注的却是搭建这一结构背后的意识行为。 (3)大多数对象的确立,都包含着直观和符号两种立义方式。在具体的对象显现中,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是混合性的被立义的对象。胡塞尔将立义活动又分为立义内容和立义形式。立义内容就是感知所得到的感性材料,立义形式则可分为三种:符号性的、直观性的和混合性的,这关系到“对象是单纯符号性地,还是直观地,还是以混合的方式被表象出来。”(胡塞尔,2006,p. 99)然而,混合性的立义方式占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意识对象大都是混合立义,可以从逻辑上为一个对象剥离出不同的立义方式,但从形态上却无法将其割裂为多个对象。这个问题导致了,在胡塞尔那里,单独的“符号”、“纯符号”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学只能且只愿处理“符号行为”、“符号化过程”等问题。 我们也不难发现,胡塞尔现象学中关于符号的研究其实是意识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尽管他有时也列举一些例子来佐证,但基本上只是对意识逻辑的回溯性研究的补充说明。胡塞尔关于“符号”的种种观点是功能性的,德里达称之为“非实体性”的。他并不是从具体的符号现象出发来思考符形、符义、符用等问题,而是从意识对对象的构建过程中为符号行为给予重新的定位。因此,胡塞尔的符号分析很难转化为一种具有推演和应用功能的系统理论。当然,我们也在德里达、梅洛庞蒂等人那里,看到了不断修正和推进胡塞尔符号问题讨论的努力。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全文文PDF版本,进入公众号点击往期目录获取各期电子期刊 本期编辑:汤文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