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阴的腔调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江阴说的是什么方言 › 江阴的腔调 |
江阴的腔调
|
陶青 一 市政府门前是一片开阔的广场。天气晴好的时候,常见一些洁白的鸽子在广场上散步。鸽子是人工喂养的,不怕人,看到你靠近,它们还会“咕咕”地不停絮叨,听起来很像江阴西乡璜土、利港一带的口音。西乡人于是高兴起来,认为这些鸽子是他们的老乡,连叫声都带着老家的乡音。 鸽子当然不一定都是从西乡飞来的,也肯定不会说西乡话,只是它们在举翮和觅食时发出的“咕咕”声,听着总像是西乡人在用家乡话说“我们”“你们”和“他们”,于是会心一笑,随口编了这么一个笑话。鸽子说的不是西乡话,江阴人说的却是标准的本地土话,江阴人靠它操持庸常的柴米油盐,亲情乡情,当然也表达着酒色财气。有句谚语说“宁卖祖宗田,不忘袓宗言”,说的就是方言与地缘、血缘之间的关系。 江阴地处江南,属于吴方言,是吴语中的太湖片中的毗陵小片和苏沪嘉小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的地方语言。上大学时,现代文学课讲到刘半农,还有他用江阴方言写的 《瓦釜集》;北方同学看不懂,课后我讲给他们听,还没等读完呢,同学的眼睛早已瞪得像牛眼似的,一迭连声问我说的是不是日本话?看着同学惊愕的神情,我心里不免暗暗得意。 其实,那时我对江阴方言也不甚了了。历届同学中都有从江阴考来的,同乡们遇到一块儿,都说江阴话,但用家乡话聊天,于我而言,更多是一种寄托,用以抚慰自己客居异地的漂泊的心。至于什么城里话硬、东乡话拖、西乡话犟、南乡话团……等等,细微之别,是浑然不觉的。工作后,往来江阴各地采访,天天浸染乡音俚语中,自以为深得江阴话三味了,结果一次在西乡作农村婚恋调研时,当地农民随口一个形象化的比喻,竟讓我听得两眼发怔,也没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于是领教了江阴话的神韵,开始细细感受起江阴方言来。 二 说起来,任何一种方言,都是环境封闭的产物,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土著听不明白。拿吴方言来说吧,江阴话、常熟话、昆山话也好,上海话、苏州话、常州话也罢,这个片那个小片的,其实传到外人耳中,一样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就算你的吴侬软语说得再悦耳,出了吴语方言区,一样是恍如天书。难怪当年孟子听了,皱着眉头大呼江南地区为南蛮舌之乡了。 回头还说江阴方言。域外人听来,只要是江阴本土的语言,感觉大抵是相似的,吐字快捷清浅、发音轻巧灵脆、听上去婉转多姿,其实不然,当地人形容江阴方言为“十八蛮”,足见江阴方言的复杂性。 江阴方言的复杂,首先体现在它的丰富性,这是江阴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从高处俯瞰下去,江阴活像一条头东尾西的河豚——北面是长江,东面跟常熟接壤,南面与无锡相连,越过西面的璜土、石庄,就进入了常州的地界。受此地形的影响,江阴东乡人说的话与常熟话十分相似,南乡则有些无锡口音,而到了璜土、利港诸镇,西乡人的嘴巴普遍有些偏大,方言与常州话仿佛说话时要把口腔充分打开,唇齿间溢满豪气。东乡人就不同了,他们说话时嘴巴是敛着的,几乎不用翕动,这使得他们的话风流妩媚,耐人寻味。“文革”时有出样板戏,叫《沙家浜》,里面的唱词唱腔堪称经典,我们这代人差不多都能唱。有次突发奇想,若用常熟话、也就是江阴东乡话来演唱 《沙家浜》,会怎样?故事的原发地本在常熟,让阿庆嫂说一口地道的常熟话,肯定会多出几分妩媚的风姿。实际上,妩媚的上官云珠正是正宗的江阴东乡长泾人。 我老家陶家村是青阳镇最北面的一个自然村,隔开一条河就是月城镇的大、小刘家村了。我与生俱来的母语即属于这片古老的热土,江阴人称之为南乡话。我的南乡话介于青阳、月城之间,严格说来更偏向月城话。好多江阴人不明就里,以为青阳、月城话受无锡方言影响,有些“团”,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真正受到无锡话影响的是更南的文林、马镇一带。我们的青阳、月城话非但没有无锡口音,反而更接近纯粹的吴方言,譬如我们老家一带管“鱼”叫“ng”,就是标准的吴方言发音,必须鼻腔用气才能发出。我小时候最怕说这个“鱼”字,因为我经常感冒,鼻子总是不通气。顺便说一下,“鱼”这个方言读音在普通话中很难找到相关的字来表示,勉强寻了个“嗯”字,还要注意声调,只有表示疑问语气的“嗯”才与我老家的“鱼”的读音一致。 曾问过不少本地朋友,“十八蛮”的江阴话中,到底哪里的话最有特色?有誉东乡话软糯有韵味;有赞西乡话朴质壮阔,像秋天的西风吹过大地;也有主张城里话最有特色,刚直爽烈、硬呛豪迈,像江面上咆哮奔腾的“翻跟斗水”。其实要我说,最有特色的江阴话,恰恰是南乡方言中的月城话。月城话最大的特色体现在语音和语调上,音调基本全是去声,这让月城话又甜又嗲、听起来格外灵动俏皮。我上小学时,村上有个发小,家里生活困难,一次放学回家,照例冲了碗酱油汤,准备吃完冷饭后去割草喂羊。冲汤时,见碗橱角落里有一小碗猪油,便随手掘了一小勺,和进酱油汤里,解了解馋,结果被他母亲发现,一顿揍,边揍边数落:“要翘咧,恁(nen,阳平)个短阳寿啊,一日到夜只晓得啜祭,人家啊拨恁吃穷落咧唩!”——满口的去声音调,听着就像唱歌一样。 月城话除了独特的音调,用词的古奥和文雅,还有其间蕴含的率真情感,是南乡话的又一鲜明特色。譬如,简简单单一个“吃”字,在南乡话里,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境、针对不同的对象,即有着不同的表述:正常情况下,称为“吃”,无褒无贬;指斥好吃懒做甚或只吃不做的人或事呢,就呼作“啜祭”“食丧”——连祭祀与丧礼上的奠品都不放过,可见有多贪吃! 老家有一个词,叫作“kong sao nian wu”,常挂在老辈人的嘴边,用来揭示某人说话不着调、喜欢无中生有编造。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琢磨,这四个字到底该如何写呢?嗯,既然是没有根据的编造,那“kong sao ”应该是“空造”吧?“ nian wu”呢?是“年话”——过年时说的话?可是,江阴人一般是把说话叫作讲“闲话”的啊,那“空造”的就应该是“闲话”、而不是“年话”啊!难道因为过年时正好是农闲时节,乡亲们特别有了说“闲话”的工夫?“年话”,年关“闲话”也。想想也通,于是就把“kong sao nian wu”写成了“空造年话”,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写的。后来教女儿读 《百家姓》,为了增加阅读的兴趣,一次在用普通话诵读之后,接着又教女儿用老家话读了起来。当读到“孔曹严华”时,我脑中突然灵光乍现——“孔曹严华”“空造年话”,它俩的南乡话发音不是一模一样的吗?闹了这么些年,原来,“kong sao nian wu”就是“孔曹严华”啊!用“孔曹严华”来形容说话不靠谱的人,你说,我的母语古奥不古奥、儒雅不儒雅? 不过,话又说回来,跟全国其他地方的土话一样,古奥儒雅不可能是吴方言遣词造句的主要特色,江阴话也不例外。应该说,所有方言都从最底层的市井中来,有些字词难免粗俗、甚至下流,但方言质朴酣畅、气韵生动,犹如田间地头碧绿油亮的新鲜菜蔬,一掐一汪水,充满了泥土的芳香。方言素面朝天,其不事雕饰的犀利质感,远非规范庄重的普通话所能比拟。 在江阴西乡一带,广泛流行着一个词语,“ruan zhi ya wu”。首先要指出的是,“ruan”这个词是江阴话乃至整个吴方言的常用词,我们一般将它写为“卵”。事情办砸了,长叹一声:“奈么卵”“格么张卵”;看不上某人做派、对其为人处事不以为然甚至加以否定,就冲他一撇嘴:“过泡卵怂”“覅去卵着伊”“阿乌卵”。就这样“卵”来“卵”去的,到了西乡,当地人就在这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了一个新词:“ruan zhi ya wu”,通行的写法是“卵子夜壶”。这是西乡话中表现力极强的经典用词,虽显粗俗,但感情色彩饱满浓烈,言辞之间,直抒胸臆,能感觉到他们气冲牛斗的痛快淋漓。 然而我想,“ruan zhi ya wu”大约不可能一上来就写作“卵子夜壶”,很可能最初写的是“耎之呀呜”。《说文解字注》曰:“耎,弱也。”,《汉书·司马迁传》中也云:“仆虽怯耎欲苟活”,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古人惜墨如金,遣词造句往往省俭,能用一个字的,一般不会用两个,但孤零零的一个字不足以抒发千回百转的情感,怎么办呢?于是灵机一动,信口在“耎”字后面缀上几个语气词,“耎之呀呜”就这样横空出世了——这是个古老而儒雅的感叹词。这之后,也许是谐音关系吧,又因为与宜兴挨得近,不知不觉地,“耎之呀呜”摇身一变,成了“卵子夜壶”,并于西乡人的唇齿间安营扎寨,司空见惯、大行其道了! 类似的词语还有“坏伯屁”。其实这词刚诞生时的原貌是“坏伯嚭”,是在一位历史名人的名字前加了个形容词。伯嚭是吴王夫差的宠臣,非常奸诈,他收了越国的金钱和美女,就经常在夫差身边讲伍子胥的坏话,夫差相信了,就赐死了伍子胥。吴地百姓痛恨奸臣伯嚭,便把所有坏人都贬作“伯嚭”,犹嫌不足,最后索性利用方言谐音,换了个字,“伯嚭”于是衍化成了“伯屁”。从那之后,江阴话词典中便多了个情绪饱满的感叹词。但现今后生中知道这个词语的,已然不多了。 三 接下来要说说城里话了。 早年有同学到江阴来,对我说,你们江阴啥都好,就有一样,兵气太重了。说话做事大大咧咧的,像是北方城市。原来同学在江阴的大街小巷转悠时,总听到江阴人一会儿“叨则”“叨样”的,一会儿又是“吃叨啦”“做叨啦”的,恍惚之间像满世界都在卖刀。又见邂逅后的江阴人互打招呼,不管男女老幼,一律以“biao将”相称,言语间满是亲热和欢喜。同学很诧异:济南满城叫老师,因为孔子是山东人;这“biao将”相称,难道江阴人都是将军出身吗? 自然不是,却与将军有关。江阴扼江控海、形势险要,一向为兵家必争。数千年的渔阳鼙鼓,江阴城的空气中也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儿,硝烟味儿飘进口鼻喉腔,江阴城里的方言便变得硬呛起来。江阴城里话与东乡、南乡、西乡话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不同主要体现在音调上。城里话发音多用入声,短短的、急急的,如天空中忽然落下的冰雹,铿铿锵锵、掷地有声,让人油然忆起磅礴的盛唐气象。民间有句俗话说,“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江阴人讲话”,多少可说明一点江阴城里话的特色。江阴城里话透着阳刚、饱含矫健,绝对迥异于传统的吴侬软语。当然,也不似北方话那样粗犷雄健,但却是一律的高亢昂扬。同学是北方人,到了江阴,他说虽然听不懂这种语言,但觉得很亲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同学的直觉是有道理的。说白了,就是因为这种江南土话的面子下,裹着北方话鲜活的里子。理论上讲,江阴城里的方言与本地其他方言一样,都属于吴语的范畴;但事实上,江阴城里是南语北音,一开口,浓郁的北方腔便扑面而来,不但音调、语法等与北方话十分相似,许多词汇更像从北方飞来,经岁月淬炼,最后在江阴城落地生根,开放出绚烂多姿的方言花朵。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我们日日要念叨的人称代词,在江阴城里人说来,既不同于苏州话的“伲、倷、俚”,也有别于上海话的“我、侬、伊”,江阴城里人说“我、你、他”,与北方话并无二致。脚上穿的鞋子,江阴城里话念作“hai”子,北京,念作“bo”京,这些都是江淮官话的发音;还有,把脏乱叫作“邋遢”、称捉迷藏为“躲猫猫”,等等,这些都是东北话的遗音。再者,江阴城里话中竟也有儿化音,比如把吃饭用的筷子呼作“筷儿”等,所有这些,无不印证了江阴城里话中鲜明的北方话的痕迹。 说起江阴城里话“内圣外王”“南语北相”的习性,就不得不提到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铁血特质了。确实,由于滨江锁航的独特地理环境,自诞生之日起,江阴城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古代的吴越争霸、宋金鏖兵,还是近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江阴都是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这种刀光剑影的战争氛围,造就了江阴人豪迈仗义的个性特征、塑造出这座江南小城雄健刚烈的精神气质,也给这里的方言土语带来了深刻影响,这影响尤以乙酉年的抗清为甚——孤城碧血八十一天,全城百姓同心死义。随即,大量北人南迁,在激活这座城市血脉的同时,也给凋敝的江阴城带来了新的言辞和语句。北音北调一经落籍,便与江阴四乡八邻的土著吴语交汇融合,江阴城里的话语因此凤凰涅槃,在血与火的洗禮中呈现出全新的风骨,重获新生。 但这“biao将”可不是赞叹作战英勇的将军,而是“婊子养的”的吞音叫法:“婊将”。“吞音”也是北方话的一大发音特点,如把“特好吃”“不好吃”分别念作“套吃”“抱吃”等等。“婊将”这个词的使用场合非常广,尤其在见面打招呼或在谈论不在场的第三者时,使用频率更高,当然,有时当面指称对方时也用。由此也可看出,江阴城里话中的北方味儿确是全方位的。没人知道“婊将”这词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但我私下猜测,“婊将”这词的产生,可能与乙酉年的抗清有关。想当年,清兵在江阴城遭遇顽强抵抗,损失惨重。清兵恼恨异常,于是屠城,还觉余恨未消,便将恶咒“婊子养的”加诸全体江阴人的身上。谁知江阴人气高性傲、照单全收,并在北音北韵的影响下,将其吞音处理成一个风骨铮铮、意蕴深远的新词:“婊将”——把“婊子养的”吞音读成“婊将”,恰恰体现了江阴人性格中的强悍大气,幽默自信。这词的发音脱胎于北方官话,但声调却与之相异:一读入声、一为阴平,两字并肩,发声时重音在前,呈完全爆破状态,后音随之接上,阴平转为入声;两字连读,似金属相击、短促有力,唇舌翕动之间,雄霸之气,沛然而生。这个初始意思为骂人的恶毒的贬义词,经过江阴人巧妙的改造后,原意尽失,不可思议地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生命力强大的口头禅:小的称“细婊将”、老的称“老婊将”、男的是“婊将”、女的是“婊将”,连称呼对手也是“婊将”。老友故交街头偶遇,一拍肩膀:“婊将,长远朆看见勒么,死哪里扣个拉?”言者满心喜悦、听者浑身舒坦。“婊将”,你道怪也不怪? 忽然想起刘半农来了。刘半农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一个喝“翻跟斗水”长大的江阴城里西横街人,早年以创作“鸳蝴派”小说闻名,在十里洋场扯响了江阴的腔调。1917年,这位敦实的江阴后生勇闯京华,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一起,操着蓝青官话,发檄文、演“双簧”、创立新式标点、发明女性的“她”,以笔为枪,向文学旧营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激昂的江阴腔调响彻古都上空。 还有个李小峰,江阴青阳人。那时李小峰在北大求学,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他组社团、搞出版,风风火火地为新文化运动摇旗擂鼓。遥想那些峥嵘岁月,刘半农、李小峰在北京相遇,我想,他们应该是热络地用家乡话谈天说地的,而且,一时聊得兴起,半农大哥估计就会拍拍小峰老弟的肩膀,欢喜地夸赞一声:“婊将!”北京大学的校园和北新书局的店堂里,不时会响起“落魂”“结棍”“和调”等江阴话的余音。江阴腔调就这样挤挤挨挨、热热闹闹,在那场空前绝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发出了来自千年古邑的声音。 江阴腔调当然不仅仅局限在城里话和南乡话里。 明末的缪昌期、李应升、徐霞客,清代的杨名时、蒋春霖、金武祥、缪荃孙等,他们有的满口东乡音、有的说着西乡腔,虽然他们各自说着自己的母语,发音各异,但是我想,当缪昌期、李应升操着东乡话怒斥阉党余孽,金武祥、缪荃孙说着西乡话校勘孤籍善本,徐霞客以江阴南乡话探幽凌险、杖藜天下时,彼时彼刻,所有的江阴方言不分东西、无论城乡,都汇成了一种独具风采的江阴腔调。这腔调有时像灵动的小溪,有时又像雄浑的大河,有时像夜莺啼唱,有时又像黄钟雷鸣……清越的江阴腔调翻过千山万水、穿透周秦汉唐,似呐喊、如歌唱,久久回荡在万古云水之间,回响在我们每个江阴人的心灵深处,直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哦,我可爱的江阴腔调啊! 责任编辑 吴 倩 猜你喜欢 西乡江阴方言 方严的方言东方少年(2022年28期)2022-11-23魅力江阴小主人报(2022年19期)2022-11-18方言今日农业(2021年15期)2021-11-26《登江阴黄山要塞》中华诗词(2020年1期)2020-09-21江阴特产——马蹄酥小读者(2019年24期)2020-01-19说说方言新世纪智能(高一语文)(2019年11期)2020-01-13留住方言新世纪智能(高一语文)(2019年11期)2020-01-13区12家直属文艺家协会西乡街道分会揭牌成立南风·中旬(2019年5期)2019-09-10《江阴介居书院成立祝词》中华诗词(2019年2期)2019-08-27区12家直属文艺家协会西乡街道分会揭牌成立南风(2019年14期)2019-08-26
|
【本文地址】
| 今日新闻 |
| 推荐新闻 |
| 专题文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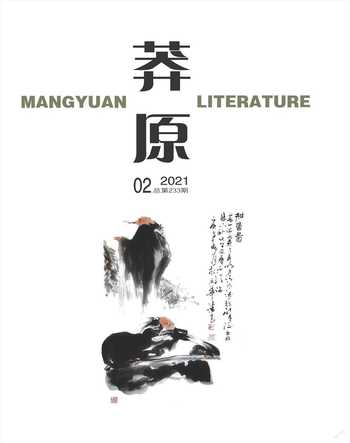 莽原2021年2期
莽原202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