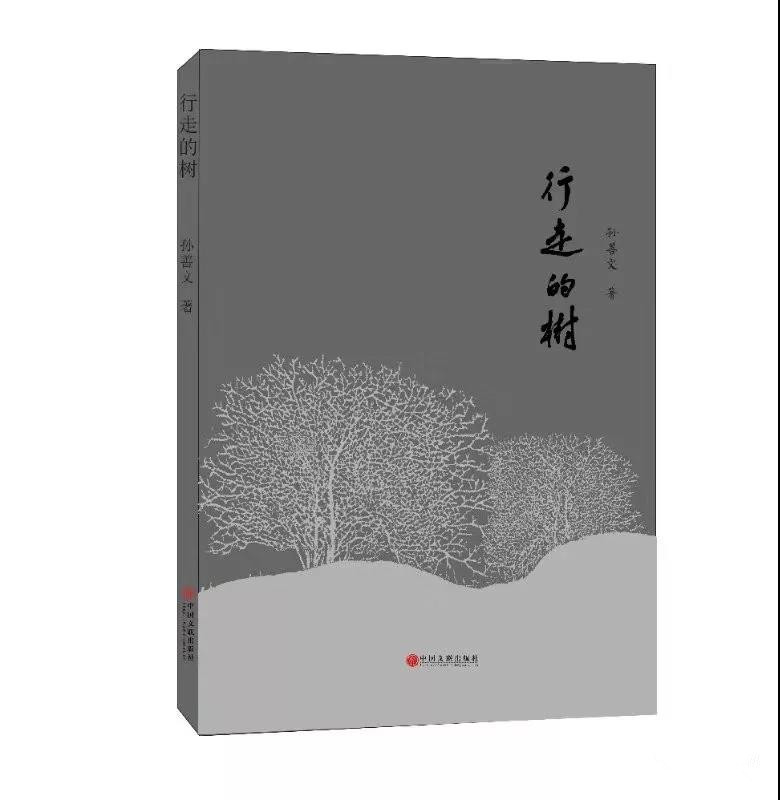| 乡土与都市体验的诗性表达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散文的诗性 › 乡土与都市体验的诗性表达 |
乡土与都市体验的诗性表达
|
孙善文的《行走的树》唤起了我对散文诗这一文体的特别兴趣,甚至让我也产生了捉笔尝试的冲动,这不能不归因于孙善文对散文诗文体长期浸淫后对这一文体审美表达特性的熟稔把握,使得散文诗的自由灵动的审美魅力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关于散文诗的文体定性,至今尚未有定论,部分学者认为散文诗应该归入诗歌的范畴,比如周航、周颖在《当下中国散文诗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一文中提出,“散文诗和新诗一样在‘五四’期间被引进中国,从而替代了格律诗等旧体诗。它从诞生之初就成为了诗体革命的产物。毫无疑问,散文诗是从诗发展来的,散文诗与新诗同源。回顾诗歌从古至今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到中国诗歌经历了漫长岁月,体式结构由严到松,格律由韵到无韵从而走向自由,散文诗也正是适应着这一发展规律而产生的。耿林莽在 2012 年提出了散文诗是新诗的继续发展和延伸,是诗的分支之说,便是由此来论证。皇泯之前也表达过:‘散文诗虽然穿着散文的外衣,蕴藏的却是诗的灵与肉。’由此可见,散文诗蕴含着诗的灵魂,走向更自由的体式,打破了上千年来诗歌镣铐而舞出了行云流水的姿态,用诗意的表达构建了心灵的交流。为能更适合地表现当今生活的复杂性,为使诗的韵律和语言更适合于现代人的表达习惯, 散文诗便成为首选。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散文诗是诗的一种延伸,是诗的分支,而并不是诗与散文简单的叠加。”与之相反,笔者认为散文诗从大的范畴而言应该归入散文的范畴而不是诗歌的范畴;散文诗具备诗歌的某些特性,但从形式规范上看,它属于散文而不是诗歌,可以定性为“诗性散文”。我们不能因为一篇小说虽然具有小说的外壳,但因为有着诗性的灵魂,就把这篇作品定义为诗歌,从形式规范上而言,它依然是一篇小说,或者说诗性小说,而不是一首诗。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散文诗虽然披着散文的外壳,蕴藏的是诗歌的灵和肉,就因此把散文诗定义为诗,从形式规范上看,它依然是散文,或者说是诗性散文。作为散文而言,它的最大美德是真诚,是作者人格、思想、情感、体验、心性的真诚表达,由此引发读者的共鸣。正如梁实秋所言,“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生活中的孙善文是真诚的,重情重义的,这些性情特点都在他的散文诗作品里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他着力书写亲情、书写故乡、书写童年、书写都市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的美好,笔墨中饱蘸了深情与真诚,最大限度地敞开自己的人生体验与内心世界,不能不令人感动。同时,他的目光又是富于诗意的,不管是记忆中的乡村生活,还是都市的车水马龙,总能引发他美好的遐想,诱发他饱满的诗情,“我的生命在于飞翔。每个空间,每个音阶,每道光线,我都深深爱着。”(孙善文《天空那只鹰》)可以说,有的人是天生适合写散文的,适合写诗的,因为他的心性开阔、敞亮,他对人间生活怀着浓厚的兴趣与热情,他念旧,他珍惜着每一个寻常的日子,他也对未知的一切抱着幻想和美好的希冀。孙善文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是适合写散文的,适合写诗的,当然也适合写散文诗。
二 与很多70后作家一样,孙善文的人生路线是从乡村到城市的。70后大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读大学的,对于彼时的农家子弟而言,上大学依然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捷径。笔者也是70后,在一个乡镇生活、学习了十几年,而后通过考大学到了省城,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因此我很能理解从广东雷州的一个乡镇走入深圳这个高速发展的都市后的孙善文对故乡的眷念。《行走的树》的第一部分“故乡,一条涨潮的河流”就集中表达了作者对故乡人事的追忆与怀念,其中渗透了浓浓的“原乡情结”。“原乡作为一种文学话语,它是作家经过内心的浸润、记忆的积累而形成的。同时它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可以是作家曾经生活且念念不忘的具体的地理意义上故乡,也可以是抽象的文化故乡,还可以是作家通过想象构建出来的精神家园。而无论一个作家的原乡是什么,这里面一定存在着某种认同,或是对一个地方,或是对一种文化,又或者是对一些人,不同的作家原乡各不相同。原乡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中的《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一文。”(邹绿《流散视域下的原乡情结》)因此,对于孙善文而言,故乡既是那个具体的雷州的五谷丰登、亲情洋溢的乡村,也是他抽象的精神家园,是他可以不断从中汲取人格、思想、精神营养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就是这部作品为什么以“行走的树”为题的真正原因。树是乡土最常见的事物,也是作者自身的象征。扎根于乡土的树茁壮、朴实,即使“行走”到异地,到城市,“树”依然保持了乡土赋予它的秉性,怀抱“原乡情结”的它也依然能够在对乡土的回想中汲取力量,保持“树”的正直与力量。 这不是一棵普通的榕树,也不是一道普通的围墙。 宝城灵芝公园一角,有一节砖石围墙,没有了。 榕树围着墙体,长出躯干,将围墙的模样托起。 它的年龄,随着岁月饱经风霜,由幼稚至成熟,如一把绿伞,高举在头顶。 它平静地在这个社区公园一角,舒展着,浓荫,铺了一地。 它独立风中,怀抱一堵几乎倒掉的围墙,让根深深扎了进去。 一条条板根,依然如雨丝般,与岁月一道,从树干上撒下,是那样无限地接近土地。 板根,此时更像一块块坚实的脚印,积蓄并伸展着。一条有理想的板根,才会掷地有声。 榕树因此在灵芝公园构筑一道独特的风景,在相片中,在视频里,它既是背景,也是主角。 ——孙善文《围墙》 这种“原乡情结”首先体现在孙善文对故乡一草一木的热爱和对故乡农耕和谐生活图景的由衷欢喜。 村庄总在那里,每栋楼每座屋都站成了路标。我其实是看着村口一个影子归来的,那里端坐着一只石狗,坐着村庄的图腾,它已经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数百年,几乎与村庄同龄。外出的游子,总能从它身上的苔藓闻出故乡的味道。 每只虫鸟、每片树叶、每串稻穗都有自己曾经的家园,它们或来自高山另侧,或来自大洋彼岸,走得再远,它们的面容、声色都难于改变。如同故乡的土地,如同我们的肤色,如同我们的语言。 我在异乡,常常把村庄留在纸上,有时是溪流,有时是古屋,有时是老榕,有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此时,我的笔总是无法绕道。其实,再细小的石头,它都已停在我们村庄很多年,都比我老。它可能是儿童的把玩,被一代玩了又丢开了,又被另一代人丢了又捡起了,它与一代代乡民一起幸福地土生土长,依然没有离开这块乡土。 天上的云,没有自己的乡村,因此只能闲散地四处飘游。 ——孙善文《故乡》 溪流、古屋、老榕,甚至一块普通的石头,都深深烙印在作者的心头,让他不断回想故乡的温情与暖意。寥寥几句话,就把作者的原乡情结、作者对故土的深情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些乡村常见的事物,因为与作者快乐的童年时光相连,尤其是与作者的亲人相连,使得它们在作者的记忆中格外美好,令人神往。并且,时光是不能倒流的,有些东西失去就不会再来。比如童年,比如母亲的青春: 风车打理每一筐稻谷,清点着每一粒合格的谷子。 合格的谷子喂养着我们。而风车里扇出的风,却吹走了村子里一季季的苦楝花,吹走我的童年,以及母亲脸上曾经的芳华。 ——孙善文《风车》 比如曾经给我端酒杯的奶奶: 奶奶说,你想家了,就回来陪乡亲们拉拉家常,喝喝老酒,斟上满满的一壶,满满的一杯。 老酒很香醇,一壶,我醉了。它攸然滑过舌尖,过喉,入嗓,轻车熟路,火辣火辣的,暖和着我的耳根。游离的酒气,无数的嘱咐,在饭桌边慢慢地打转着。 我沉醉在奶奶的那张床上。那晚,无数的异乡与我同眠。 奶奶是不爱喝酒的,我在他乡,也绝少贪杯。但她每一次来电,都叮嘱我不能醉酒。奶奶,请您放心,我只醉在故乡,因故乡有您,我们喝的是老酒。 一只酒杯,因盛过老酒,也就盛着故乡的山和水,盛满奶奶的希望和牵挂。回家喝酒,只是一个老人期待相聚的理由。 故乡依然,却已没了奶奶端来的老酒。 奶奶坐在祖屋高高的神龛里,静静地看着屋檐下的老燕徘徊。我们默默地对视着,只感到杯杯乡情依然在为我洗涤风尘,一次次把我灌醉。 我还继续远行,酒杯已长留故乡。 ——孙善文《我把一只酒杯长留故乡》 又比如,曾经清澈的溪流: 故乡在变,故乡的南渡河也在变。 污水的随意排放,垃圾的存意丢弃,废料的蓄意倾倒,南渡河已成为一条疲惫的河。 我曾垂钓于河边,当钩起的不是鱼,而是一个个垃圾袋的时候,我已黯然伤神。 河里漂浮的塑料袋,顺流而下,红色的、绿色的、黑色的,是那么的刺眼,更是那般令人伤怀。 故乡总在那里。楼更高了,路更宽了,人更俊了。 故乡的南渡河,却在远去。 ——孙善文《故乡有条南渡河》
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中最为强劲的一脉。总体而言,乡土文学在题旨上开发了两种分歧的路向,一路是对乡村与农民的田园诗意化的乌托邦叙述,比如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另一路则是对乡村现实苦难的书写,比如鲁迅的《祝福》等。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滥觞以来,后一路向得到了某种加强。在孙善文的笔下,乡土生活的艰辛自然也有非常具体生动的呈现,但他更在意的却是书写乡土生活和劳动的诗意。如此看来,他的乡土写作更多地承续了沈从文等人的路子。沈从文所要表现的是他对一种理想的人性与人伦图景的想象,以及他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正如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分析《边城》时所言,“‘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沈从文通过《边城》等作品塑造的是一个未被“文明病”、“现代病”、“城市病”沾染的理想境界,传达的其实是他内心中对理想人性与美的境界的永恒的乡愁。同样,孙善文笔下的乡村生活场景,父母劳动的场景,村人团聚喝酒的场景,传达的都是一幅幅和谐的乡村人伦图景,也是一幅幅理想的充满美和诗意的图景。 孙善文散文诗作品中的乡村书写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其中的地域文化含量,在于他对乡土文化的追溯与认同。《行走的树》第四部分 “羁旅,一枚通往彼岸的船票”中的大部分篇什就是书写作者对历史人文的追溯和崇敬之情。作者故乡雷州所属的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多方面,岭南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近代岭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雷州,曾是历史上多名文人官员被贬谪之地,包括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他的足迹和字迹留在这里,他的坚韧不拔和清高孤寂也留在这里,也融汇成当地文化的重要内涵,成为激发作者“原乡情结”的固有元素: 这是1100年6月的一天。一叶轻舟从海南澄迈启帆,往徐闻而来。 苏轼北归了。岛上三年,所有坚定的行走,足以表达穿透的力量,以及初心的清高孤寂。 ——孙善文《渡海》
三 当然,成为孙善文散文诗作品审美对象的不仅仅是他曾经体验过的乡村生活,还有他眼下每天都要面对的都市生活。对于许多写作者而言,这也是一道不大不小的关卡。很多写作者,当他书写记忆中的乡村生活时,往往得心应手,而一旦面对都市和日常生活,却似乎缺少了审美距离和时间的沉淀,感觉笔下的文字总缺少一点什么。当然,这与我们悠久的农业文明及其所携带的农业文化的美学相关,我们对田园、自然以及相关的意象、词汇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城市美学多少有些生疏和胆怯,正如论者所言,“事实也在于,在一个农业社会中沉浸已久的文学世界,人们的审美乐于被一些静态封闭的田园生活所牵制,人们习惯于从大地、山野、蓝天和绿水中去感受文学的意味,却很难想象金钱交易、物质交换、商业关系和工业文明同样有助于文学想象和精神滋长的空间。于是,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种简单的批判手段轻易地打发掉一些值得思考、值得关注的重要命题。但事实上,人们只注意到中外作家们对金钱批判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金钱对滋养文学想象方面的作用。简而言之,即面对一种实际存在或众人期待的生活,批判不能只是先在的条件,也应是生活展开后思想和精神的回响。在没有充分的城市化生活实现之前,用原先的、固化的生活经验来开展所谓的批判,那必将是无力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城市化中的当代文学批判,理应努力展示出区别同时代普遍的话语习惯,以一种全新的生活场景和全新的生活体验,在一种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共同渗透下,构筑一种生态的、整体的、深刻的文化哲思和文学启示。”(陈超《文学视域中的“城市化”景观及其反思》)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一种对城市的刻薄与偏见。但是,天性淳厚的孙善文没有掉入这一窠臼。城市,在他眼中也是美的,充满诗意的。《行走的树》第三部分“城市,一封给时间的信”就是作者写给日新月异的都市的一封封情书。 月儿挂上了夜幕,宝安107国道灯火鲜艳通亮。 长长的车灯爬满路面,是夜色下绽放的阳光,从一辆车晒到另一辆车,从宝安107国道的这一头晒到另一头。车灯罩射出的光亮,如利箭一样,锁定了车辆的走向。 我是沿着簕杜鹃延伸的方向过来的。从南头及松岗,短短的32公里,足以丈量特区的每一个理想。红红的簕杜鹃,是深圳的市花,它纵情地在107国道开满一路,就希望每台路过的车辆及所装载的灵魂都得到温暖。 道路是城市的触角,挑逗着城市行走的步伐。高架桥,一次次将速度垫高。奔跑的车河,萌生着持久的力量。这流淌着的“沙沙”声,你别想追上,满满一条河,传递的都是脚步声。车轮的后浪推动着前浪,此时,不能停,停不了,一旦停下,必被滚滚的车浪淹没。 有一年,宝安一半分二,变成了宝安和龙岗;又接着,宝安一分为三,变成宝安、光明、龙华。107国道依然故我,道路的两侧,一边往南,一边向北,任由车流紧张流淌。 我们踩着前人的路,行走在107国道,特区的历史一年比一年垫高了路基。国道上的脚印,被一张张蓝图填满。 有思想的107国道,说要往河源、往汕尾行走,去远方。 ——孙善文《宝安107国道》 不是只有田园才有美,城市也有它的美。正如孙善文所发现的,乡村的美在于父母的劳作中,在沉甸甸的稻穗中;城市的美,也在它的发展中,在劳动和建设中,在它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营建中。当代文学应该出离“逃离城市、返归乡土”这一简单的线性行为与理念,以求得城市化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动态的互动和平衡,才能驾轻就熟地用文字最为恰当地去表达出当下城乡人口流动中的独特文化景观和中国经验。孙善文的散文诗作品虽然篇幅短小,但他依凭自身醇厚的天性和写作者的直觉,忠直地表达自己从乡村到都市一路走来的切身体验,与记忆对话,也与现实对话,反而规避了许多写作的窠臼,达成对70后一代人成长经验与乡土、都市体验的真切表达,这是文学对于执着者的奖赏,也是生活对于执着者的奖赏。(本文刊用于《伶仃洋》杂志,插图作者为著名摄影家黄华养先生,画面均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雷州美景)
本文作者简介: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特约评论员,《神剑》、《贵州民族报》、博客中国专栏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文学评论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篇小说选刊》2014-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评委、汪曾祺文学奖评委;《青年文学》90后专栏主持、《名作欣赏》90后作家专栏主持、《贵州民族报》中国文坛精英盘点专栏主持、原乡书院90后作家专栏主持。曾获钟惦棐电影评论奖、《安徽文学》年度评论奖、《橄榄绿》年度作品奖等奖项,主编“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在场丛书、海南作家实力榜丛书、“锐势力”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丛书等。
《行走的树》作者简介:孙善文,广东雷州人,现居深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南国散文诗》主编。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文学》(增刊)《散文》《山花》《延河》《湖南文学》《山东文学》《西部》《火花》《散文百家》《奔流》《诗选刊》《星星》《上海诗人》《绿风》《诗林》等100多家报刊及10多种年度选本。出版有散文诗集《行走的树》。曾获中国曹植诗歌奖、2018中国西部散文排行榜新锐奖等奖项。 文: 郑润良 摄影:黄华养 编辑:席笛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