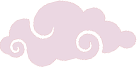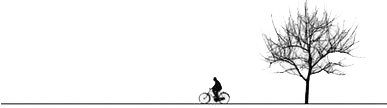| 经典百书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固守己见不变通的例子 › 经典百书 |
经典百书
|
1953年钱穆与唐君毅 钱穆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 是其学问研究方向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 即是他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 40年代初,钱穆先生之所以从历史研究转入对文化的研究,不是偶然的。日寇入侵,大好河山沦丧,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了人们对民族精神的关注。在钱穆看来,要拯救国家, 唤醒民众,凝聚力量抵抗侵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因此他便转向中国文化研究,希望通过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去寻找抗战救国的文化资源。而对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反传统思想的批判,则是他转入文化研究的现实动因。
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侵略者的枪炮轰开以来,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就一直困扰着整个中国人,特别是富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这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何去何从?怎样去衡估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传统文化看成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障碍,认为中国要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就必需要与传统决裂,全盘西方化。在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这股奉西化为圭臬的西化思潮应当说是很有市场的。钱穆在晚年自述中称他40年代初之所以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乃 “国内之社会潮流有以启之”。这里的所谓“社会潮流”,实际上就是指流行于当时学术界的全盘反传统思潮。钱穆对近百年来学术界流行的西化思潮作过比较深刻的分析。 他说近百年来不断有两条相反的潮流在相激相荡: 一条是潜伏在下层的“伏流”,那就是中华民族由于五千年来文化传统的积累,遭受到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而不断寻求挣扎的那种自觉自尊的激情,这条“伏流”表现着中国民族文化意识的潜在要求;另一条是显露在上层的“逆流”,那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统治阶层对自己历史文化极端蔑视、排拒的自卑心理和无限向外的依托精神,它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国有文化的自我否定和故意摧残。 正因为在民族复兴意识强烈要求的主潮浮层,有一股对自己文化传统极度轻蔑、厌弃的逆流在作指导,从而酿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悲剧。因此,中国人自己看轻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大隐忧和最大病害。而这种自卑媚外的文化心态,又障蔽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
图为授课中的钱穆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揭地狂飙席卷中国之时,钱穆正在江南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任教。他虽然蛰居乡村,但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心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不满。他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在纪念亡友张其昀的文章中,钱穆说20年代对北方《新青年》和南方的《学衡》两杂志的文章,皆悉心拜读,但内心却是赞同学衡派“昌明国粹 , 融化新知”的文化主张的。在1928年写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民初以来全盘西化思想给予了批评,认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孟子所谓“失其本心”。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对把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诿卸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痛切的指出:“……凡此皆挽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转而疑及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 , 而唯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钱穆并不否认中国文化演进到近代呈现出衰颓不振、病痛百出这一事实。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它必须要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整与更新。但是,调整与更新却不能自外生存,它必须要体认和依凭中国文化内部自身的机制。因为“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 数十世、 数百世血液浇灌、 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所以钱穆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内部的自我调整与更新,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他把这种自我调整、 更新机制称之为“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生长。”为此钱穆主张中国近代文化的种种病痛应用中国文化内部自身的力量来医治,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心,而不是与传统决裂,“尽废故常”。 可见,对蔑己媚外、菲薄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批判,是促使钱穆在40年代初转入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抗战时期钱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以昂扬民族精神为其主要内容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他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灵魂。在欧风美雨浸染的文化氛围里,在崇洋蔑己、全盘西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思潮中,钱穆转向文化研究,自觉以阐扬中国文化为己任,这对于培育当时国人的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向心力,重铸新的民族精神,有其贡献。台湾学者韦政通在《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一文中指出: “在抗日时期,对宏扬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钱穆先生)居功甚伟。” 2 《中国文化史导论》是钱穆先生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该书虽然主要是讨论中国文化,然而也多方面地涉及到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比较问题。钱穆在 《导论》 修订版序言中指出:“本书虽然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迄今46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以下所引《导论》,皆据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可见《导论》 不仅仅是钱穆讨论中国文化的著作,而且也是阐述他对中西文化基本看法的力作。仔细阅读全书不难看出,钱穆在《导论》中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和阐释实际上又主要是建立在中西文化两类型说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文化史导论》书影 钱穆系统阐述中西文化两类型说理论主要见于他 1952年出版的 《文化学大义》 一书中。不过这一理论在 《导论》 中就业已形成。 钱穆认为人类文化,穷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尤其是气候、物产之相异。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生出种种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慧发展方向乃至心理、性格之种种不同。由此种种不同,而引发出文化精神的截然相异。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在《导论·弁言》中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三种类型。这三种文化就其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言,实际上又可并归为农耕文化和游牧商业文化两大类型。 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在文化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他说中国文化植根于农村,是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农耕民族与土地相连,胶著而不动,其生活方式是安守田土,依时而行,因此在农业社会中生长的民族,“一向注重向内看”,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其文化以固守本土、安定守成、质朴厚重、沉着稳健、崇尚和平为特征。与“安足静定”、崇尚和平的中国农耕文化相反,西方文化则属于典型的“惟求富强”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与发源于草原高寒地带、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一样,起源于“内不足”。由于“内不足” 的经济状态,促使他们不断地向外寻求、征服,以“吸收外面来营养自己”。因此,商业文化比较注意空间的拓展和武力的征服,有强烈的战胜欲和克服欲,其文化以流动进取、崇尚竞争、内部团结、富有战斗性、侵略性和财富观念为其特征。
授课中的钱穆 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不同,中西文化的其它不同特点都是在这一根本差异的基础上衍演和发展起来的。比如在宇宙观上,由于中国文化是在平原农耕地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了在土地上发展生产,就必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长期在农业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中国人常常把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的一体,主张人与自然相互融和贯通。由于中国文化主张天人交贯,“求循人以达天”,于是又形成了顺乎自然、行乎自然的人生观。这集中表现为中国人希望自觉地遵从自然、顺应自然,力求将人生投入大自然中,与天地万物生息相处,协调共存。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所讲的自然,是生命化、 精神化的自然,人生是自然化、艺术化的人生,自然建立在人生中,人生又包蕴在自然中,表达自然即为表达人生,因此中国文化演进的趋向和途辙必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 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顺乎自然的有情人生观相反,西方文化 “注重向外看”,比较偏重于先向外探寻自然,因而他们看世界时,常常是外于两体对立的状态,“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所以西方文化在宇宙观、人生观上明显表现出了天人对立、役使天地的倾向。再如就中西学术而言,西方学术重区分,学术贵分门别类,宗教、科学、哲学、文化、艺术皆各自独立发展,而中国学术则重融通,一切学问皆会通合一,融为一体。”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相异,由此而导致了中西文化在宇宙哲学观、人生观、 思维行为方式以及学术上等方面的不同。 由此,钱穆先生在这里得出了 “中西双方的人生观念、 文化精神和历史大流,有些处是完全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的结论。钱先生的这一结论实际上是针对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而提出来的。
西化论者在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时,只看到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时代落差,过分注重和强调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趋向,忽略了对民族文化个性差异的分析,因而他们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 “古今之异”,是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钱穆通过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并非时间上的 “古今之异”,恰恰相反,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文化类型的不同,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相异。鉴于此,钱穆在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时,多从中西文化各自的民族性着眼进行比较,进而强调世界上各种不同体系的文化各自具有其独特的个性和价值。这样便肯定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民族性以及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价值。这实际上坚持了文化发展的多元论,是对西方文化中心说和全盘西化论的一种回应和反动,旨在以此来维护中国文化的价值。 既然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它们各自具有其平等的、独特的价值,那么就决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看成是人类文化唯一模式去衡估和评价其它文明。从这种文化发展的多元观出发,钱穆极力反对用西方的概念、术语去硬套和强解中国的学术思想,反对以西方文化的一元发展模式来衡定和取舍中国文化,力主站在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立场上,用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和研究中国文化。所以他在《导论》中强调说: “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我们先应该习得中国人的观点,再循之推寻。否则若从另一观点来观察和批评中国史和中国文化,则终必有搔不着痛痒之苦。”
在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和比较中西文化的方法问题。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是属于自成体系、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这两大文化的演进并非直线上升或下降,而是常循波浪式的曲线前进。 因此,应该把这两种不同型态的文化放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全程中去衡定评估,道其优长,切不能“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义与价值”,“单就眼前作评判定律”。为此钱穆指出,比较中西文化,我们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当是“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 3 在抗战时期,一些对钱穆文化主张持批评意见的学者把他当成一个典型的复古主义代表而加以批评,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钱穆先生全盘肯认传统、拒斥西方文化。其实这种批评并不全面。事实上,抗战时期的钱穆先生并不是一个全盘肯认传统、固定传统、赞美传统的复古主义者,他也有融会中西文化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比他其它任何时期,态度更为鲜明、积极。钱先生《导论》第十章“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实际上要是谈中西文化融合问题的。他在书中指出,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当前遇到了两大问题: 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 美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是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斫丧了。 1941年,在《思想与时代》杂志创刊号上,钱穆发表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 一文。在文中,他亦表达了与《导论》类似的观点。
《思想与时代》书影 显然,抗战时期的钱穆先生对西方文化并非采取一概排拒的态度,他也是主张融会中西文化的。当然,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实际上主要是指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不主从宇宙大全体探寻其形上真理 , 再迂回来指导人生”,而直接扣紧人生实际,主张人生与自然相融贯通,其文化的最高目标是“人生之艺术化”。因此,中国文化偏重在人文科学一端,自然科学最为缺乏。而西方文化则相反。西方文化比较偏重于先向外探究自然,在对外界自然有所认识和了解后,再回过头来衡量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因此,西方文化主张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这种把宇宙自然看作是人类对立面而加以役使和征服的观念,必然导致西方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形成追求物质利益的科学型的文化精神。所以西方文化总是在外面客观化,“在外在的物质上表现出它的精神来”。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虽然缺乏西方意义的近代科学,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排斥科学、反对科学,就不需要科学。相反,中国文化不仅需要吸收西方的近代科学来充实自己,而且吸收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也不会损伤中国文化原有的生机与活力。因为中国文化并非深固闭拒,它是一个包容性、消化力很强的开放型的文化体系,它对外来的异质文化总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去加以吸收和融合,这从中国文化对印度佛学的容纳和吸收即可得以说明。对此,钱穆在《导论》 中对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作了许多非常精彩的分析。
钱穆夫妇与余英时合影 显然,在钱穆看来,中国传统文化较之西方,其短处在自然科学,其长处在人文政教,并不是中国文化精神与近代西方科学根本不相融。他希望现代的中国人能像宋儒消融佛学那样去消融西学,用西方文化之长来补中国文化之短。 所以,他认定西方近代科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理想,实有充实恢宏之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系统里尽可渗进西方文化来,使中国文化更充实、更光辉。为此钱穆在 《导论》 中指出,目前的中国 “太贫太弱,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甚至更激进地提出:“此下的中国,必需急激的西方化。换辞言之,即是急激的自然科学化。”显然,在抗战时期,钱穆并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相反他对西方文化,特别是为中国文化所缺的西方近代科学,还是虚怀接受的。美国学者狄百瑞先生在论及钱穆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说: “钱穆最大的贡献 , 就是维护中国传统的观点以对付西方的影响。”钱穆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他认同传统、维护传统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这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他对中国文化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全盘肯定,而是择善而从,在肯认传统的同时又不乏批判意识。 钱穆在 《导论》 中对儒学缺点的分析 , 便是典型的一例。儒学为中国文化之中心,为中国文化之主脉,这是钱穆先生毕生服膺、认同的。但是,他对儒家思想也不是全盘肯认、一味颂扬,也没有把孔子抬到 “通天教主” 的独尊地位。钱穆在 《导论》 中称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也有他的缺点。这些缺点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1 第一,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周的物界与自然。 2 第二,太看重现实政治 , 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 3 第三,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使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的素朴与真实。 早在1926年出版的 《论语要略》 中,钱穆就明确指出,孔子学说是二千四百多年前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思想和学说深深地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不可能处处都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显然,这种对儒家学说采取历史的分析态度是正确的。同时,钱穆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应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种看法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
陈勇 陈勇,男,1964年10月生,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陈乔碧 主编:桃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