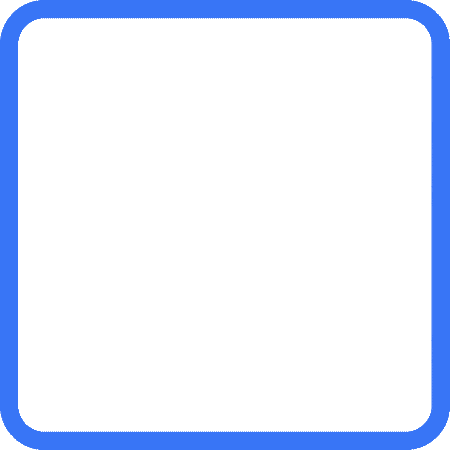| 徐爱国、李桂林:社会法学的一般特点及其在欧美的代表人物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特点 › 徐爱国、李桂林:社会法学的一般特点及其在欧美的代表人物 |
徐爱国、李桂林:社会法学的一般特点及其在欧美的代表人物
|
今天,我们摘编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李桂林教授合著的《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三版)第四编第一章《社会法学》中的相关介绍。如果说《法社会学信札》描绘的更多地是这一领域的“今生”,那么《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三版)就更多地是从历史的角度介绍其“前世”,读者可以概览式地了解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找到进一步拓展了解的门径。
社会法学的一般特点 及其在欧美的代表人物 01 社会法学的一般特点 社会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 对法律进行一种社会学的解释,产生于19世纪末。这种理论及其方法有三种名称,一是社会学法学,二是社会法学,三是法律社会学。三种名称实质上是指同一含义,只是各个思想家所研究的角度和着重点不同而已。他们都以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法,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法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并认为法或法学不应像19世纪那样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应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 这种理论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其后有英国的斯宾塞、奥地利的贡普洛维奇等人。到了20世纪,这种理论蓬勃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埃利希、庞德和坎托罗维奇。另外,有一些社会学家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的问题,有的学者也就将他们也列入社会法学的范围之内,比如杜克海姆和韦伯。他们与早期社会学法学家不一样,他们不仅主张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特别强调法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们不仅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调和,他们不是仅仅从人文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等某一个单独的角度去解释法律,而是综合各门学科解释法律现象。按照庞德的解释,社会学法学与其他法学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第一,社会学法学着重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内容;第二,它将法当做一种社会制度,认为可以通过人的才智和努力,予以改善,并以发现这种改善手段为己任;第三,它强调法要达到的社会目的,而不是法的制裁;第四,它认为法律规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指针,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模型。
【法国】 奥古斯特·孔德
【英国】 赫伯特·斯宾塞
【奥匈】 贡普洛维奇 尽管社会学法学在20世纪因各学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各派的许多基本观点是极为类似的,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1)社会学和实证主义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两者都与孔德有有关。这些理论是革命性的,它们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这两种方法都应用到了法学的领域,前者的应用就是这里所讲的社会法学,后者的应用则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2)社会法学的发展至为迅速,从现在的情况看,法理学和社会法学几乎成了两个相提并论的学科,而社会法学的书籍几乎超过了法理学的文献。从传统的意义上看,我们还可以说社会法学是法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现在我们似乎不能这样讲了,因为社会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太庞杂、太不一致,社会法学的研究人员也太广泛。 (3)一般认为社会法学的特点,一是应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的问题,二是强调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即法律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至于前者,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法学开辟了法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领域;至于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除了社会法学之外,其他现代法学同样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法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哲学,它们很少探讨那些原来属于法哲学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本质、法律的结构、法律的理想;而是更多地探讨法律的具体问题,比如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及这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法律的效果、法律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判决是如何通过法官的活动得出的、影响判决的社会因素是什么,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传统的法理学是法学的理论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社会法学更像是法学的一种技术。 02 欧洲的社会学法学 埃利希,耶林,韦伯 埃利希的“活法”理论 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Ehrlich,1862—1922)被公认为是法律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是《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和《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埃利希认为:“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自身,即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1] 既然法律发展的重心在社会,那么它的发展就不在于国家的活动。这里,埃利希指的是从法律和国家关系方面看,国家制定的法律只是法律中很少的一部分,早在国家产生以前,法律(包括立法和司法活动在内)就已存在。因此,国家制定法律和国家强制力并不是法律的要素。埃利希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下列三种因素从法律的概念中排除出去:第一,法律由国家所创立;第二,法律是法院或其他审判机关判决的基础;第三,法律强制是判决发生效力的基础。但以下这种因素却要保留下来,并必须成为理论的出发点:“法律是一种安排……法律是一种组织。也就是说,法律是一种规则,它分配每个成员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义务”[2]。埃利希在这里把法律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即国家的法律,另一类是社会秩序本身。这种社会秩序就是社会各种规则,而这些规则并不都是法律。除了法律以外,还有道德、宗教等。法律和其他社会规则的区别在于:法律的对象是社会舆论认为最重要的事件;此外,与其他规律相比,法律要以更明确的用语加以表达。
埃利希著作书影,见Internet Archive 埃利希认为,法院的法官只靠成文法是不够的。他指出,关于法律适用的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摆脱下面这些困难:每一次制定出来的规则,从本质上说都不是完整的;它被制定出来时,实际上就变成旧的东西了。最后这种规则既难治理现在,更不用说治理将来了。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具有本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用已往的精神来适用法律。所以,即使是稳定的学说和最强有力的立法,当它们一遇上现实生活的暗礁时,便粉身碎骨。因而,判决方法可分两类:一类是技术主义的判决方法,即传统的判决方法;另一类是自由的判决方法,即法官进行判决时,不是根据成文法律,而是根据法官“自由”发现的法律。这种判决并不意味着法官的专横。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而对法官的限制却不过是将责任转移到别人的肩上而已。传统的判决方法总想消灭法官在判决里的个性,但在司法审判中,个性因素总是有的。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保证法官的个性发展到足以使他能够负责处理这些职能。法官自由判决的原则,实际上并不触及法律的实质,而是关系到对法官的适当选择。 埃利希强调对“活法”的研究。他认为,“活法”是联合体的内在秩序,即与由国家执行的法律相对的社会执行的法律,简单地说,就是支配生活本身,不曾被制定为法律条文的法律。离开活法的社会规范,就无法理解实在法。活法的科学意义,不限于对法院所使用的、供判决之用的规范,或对成文法的内容有影响。活法的知识还具有一种独立的价值,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埃利希认为,这种活的法律的知识来源有两个:第一,现代法律性文件;第二,对生活、商业、惯例、一切联合的直接观察,这些观察对象不仅包括法律所承认的,而且还有法律条文所忽视和省略掉的东西。实际上,甚至还有为法律条文所不赞成的东西。埃利希的“现代法律性文件”是活的法律的首要来源,实际上指商业文件在法律实施中的统治地位,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埃利希认为,与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完成的无数的契约和交易相比,法院的审判只是一种例外的情况。现实生活中,只有少部分纠纷是提交享有审判权的人员去解决的。研究结婚契约、租契、买卖合同、遗嘱、继承的实际制度和合伙条款以及公司规章则更为重要。 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 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于1872年在维也纳法律协会上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为权利而斗争》。这是一篇著名的演讲,标志着一种新的法律研究方法的诞生,有人称之为目的法学,有人称之为一种社会法学。
耶林 在“法的起源”问题上,耶林批判了历史法学关于法的起源的看法。他提出,“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3]。法的生命即是斗争,这包括国民的斗争、国家权力的斗争、阶级的斗争和个人的斗争,正如正义女神一手持天平,一手握宝剑一样,健全的法律应该是公平和力量的统一。耶林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法,即客观意义上的法和主观意义的法。前者指的是由国家适用的法、原则的总体、生活的法秩序;后者指的是对于抽象的规则加以具体化而形成的个人的具体权利。 耶林论述的重点是主观意义的法。耶林以为,在历史法学看来,法的形式类似于语言的发展,是无意识的、自发、自然形成的。法表现为超越目的和意识的有机的内在发展。这种发展是依据法学的方法,将社会生活中自治发生的法律行为逐步积累形成的法的原则、制度明确化成可以被认识的抽象概念、命题和原则,其基本因素是法的自我发展和法学家的研究。耶林批评说,法的发展仅仅依靠这两种因素是不够的,它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立法活动。诉讼程序及实体法的重要修订最终由立法来完成,这是法的本质使然。立法是对于现存利益的一种安排,所以新法要诞生,经常要经过跨世纪的斗争。耶林说,法的历史上所记载的伟大成果,诸如奴隶制农奴制的废除、土地所有、营业、信仰自由等,莫不经过跨世纪的斗争而始告胜利。耶林指出,历史法学作为一种理论并不危险,但是这个学派带有极端宿命的色彩。他们认为,政治的准则不能被人所折服,人的最佳选择是无所事事;法通过民族信念缓慢显现出来,他们反对立法、崇尚传统的习惯法。耶林评论道,历史法学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弄清,法的信念只有依靠行动才得以形成自身,依靠行动才能维持支配生活的力量和使命。其原因在于历史法学受到了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影响,历史法学是法学中的浪漫派。耶林总结说,历史告诉我们,法的诞生与人的降生一样,一般都要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为法的诞生而必要的斗争,不是灾祸,而是恩惠。”[4] 《为权利而斗争》是一个标志,它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学理论的变迁。其中首要的是,它反映了历史法学是如何最后过渡到社会法学的。用功利主义取代浪漫主义,用追逐权力和利益取代崇拜民族精神,从注重客观权利到注重主观权利,直接为社会法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在耶林的另外一部著作《法律的目的》中,耶林对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到庞德那里,法律则被视为是对于利益的一种调整和保护。 韦伯的法律理想类型 韦伯称,理论的研究“不是要用抽象的一般公式把握历史现实,而是要用必然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具体生成的关系体系把握历史现实”[5]。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的结构,每种统治结构类型都有其相应的合法性原则,这个原则要么是理性的规则,要么是个人的权威。韦伯区分了三种典型的统治结构:一是“理性化”的统治,以官僚体制为典型特点;二是“传统”的统治,以家长制为代表;三是“个人魅力”的统治,政治的结构建立在个人的权威基础上。[6]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政治现象,主权与家庭、血缘团体及市场共同体一样,都是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政治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之处,仅仅在于它在其领土之内行使特别持久的权力,有一套合法性的法律规则。这种规则体系就构成了“法律秩序”。[7]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1918年 在韦伯那里,“形式/实质”和“理性/非理性”是法律秩序理论的两对基本尺度。人类早期社会的法律以非理性的法律为主,它们可以是形式的非理性,比如巫术和神判;也可以是实质的非理性,比如家长的个别命令。法律从非理性向理性和形式体系方向的发展,便是现代法律制度形成的标志。而现代法律制度相应地区分为实质的理性和形式的非理性。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人,韦伯心目中法律秩序的最佳模式便是形式理性的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代表就是19世纪德国的学说汇纂学派。[8] 不管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还是在他的《经济与社会》中,韦伯都明确表示,近代法律制度只产生于西方世界,伴随着资本主义成长而发生。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着其经济社会的原因,也有着宗教伦理方面的精神原因。政治因素加上精神因素,资本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君主和教会的政治斗争中,不仅需要技术的生产手段,同样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照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新教伦理中的刻苦、节俭、纪律和节制品德,又与法律的统治相暗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合理的成文宪法,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根据合理规章或者法律由经过训练的官吏进行管理的行政制度的社会组织……仅存于西方”[9]。 韦伯认为,中国法的特点就是世袭君主制权威与家庭或者血缘集团利益的结合[10],中国法是一种“家产制的法律结构”[11]。法律体系形成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严格形式法与司法程序,法律具有可预见性,另外一个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掌管官僚体系。[12]以此为标准,中国古代社会不会产生西方式的法律秩序。就前者而言,地方习俗和自由裁量高于并抵制着一般法。“自由裁量高于一般法”是通用的命题,法官的裁判带有明显的家长制作风,对不同的身份等级的人和不同的情况力图达到一种实质的公平。因此,中国不会出现西方社会所特有的法律平等或者“不计涉及任何人”的审判方式。中国社会“法令众多,但都以简明与实事求是的形式而著名”,“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所寻求的总是实质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13]就后者而言,中国不存在着独立的司法阶层,不能够发展也没有想到去发展出一套系统、实质和彻底的理性法律,也不存在可以一体遵循的先例。没有哲学,没有神学和逻辑,也就没有法学的逻辑,体系化的思维无法展开,中国古代的司法思维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经验层次上。[14] 03 美国的社会法学 霍姆斯,庞德 霍姆斯的《法律的道路》 1897年1月8日,时为美国麻省最高法院法官的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律的道路》的演讲。这是他一生中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讲。在西方法学中,特别在美国法理学历史上,这篇演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霍姆斯开宗明义地说,我们学习法律,不是去研究一个秘密,而是去研讨一个众所周知的职业。他说,在美国社会,公共权力掌握在法官手里,当人们想要知道在何种条件和何种程度上将要受到这种权力的威胁时,他们往往就付钱给律师,让律师为他们辩护或提供法律咨询。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一种职业。法律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预测,即预测公共权力通过法院这一工具对人们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霍姆斯严格区分法律和道德。他说,不可否认,法律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人和外在表现。法律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道德的发展史。法律实践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好的公民和善良的人们。但是,要学好和弄懂什么是法律,就必须区分法律和道德。他说,在尽量避免公共权力的制裁方面,一个“坏人”要比一个“好人”更具有理智。也就是说,区分法律和道德的现实意义在于:一个并不在意和实践伦理规则的人最有可能避免支付金钱和远离审判。从实际上讲,坏人只看法律的实在结果,从而由此进行预测。而好人总是用模糊的良心准则从法律里外来寻找其行为的理由。从理论上讲,法律充满了来源于道德的术语,通过语言的力量就可以应用法律,而不必从道德上再去认识它们。而且,诸如权利、义务、恶意、目的和疏忽等法律术语的内容并不比其道德含义简单。如果把一个人的道德意义上的权利等同于宪法或法律上的含义,其结果只能导致思想的混乱。在此基础上,霍姆斯提出了他著名的法律概念。“如果我们采取我们的朋友,即坏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毫不企求什么公理或推论,但他的确想知道马萨诸塞州或英国的法院实际上将做什么。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法院实际上是将作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其他自命不凡的什么,就是我所谓的法律的含义。”[15]
霍姆斯肖像 应该说, 强调法律与道德的紧密关系是自然法学的共同特点。法律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法律之外的权威,法律的实现就是某种伦理的实现。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康德都是这样说的,“权利科学研究的是有关自然权利原则的哲学上的并且是有系统的知识。从事实际工作的法学家或立法者必须从这门科学中推演出全部实在立法的不可改变的原则。”[16]而区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分析法学的显著特点。奥斯丁说:“法理学科学,或简单和简明地说法理学,只涉及实在法,即所谓严格的法律,而不涉及它们的善与恶。”[17]法律就是主权者命令和制裁的统一,“恶法亦法”。到19世纪末的霍姆斯时代,形而上学的自然法在受到分析法学和历史法学的猛烈批判后,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霍姆斯也是如此,他严格区分法律和道德,主张混淆法律和道德只能造成执法的混乱。在这里,霍姆斯倾向于奥斯丁的法律与道德的区分。应该说分析法学区分法律与道德,使法理学向前进了一大步,使法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成为可能。但霍姆斯决不是分析法学论者,因为在霍姆斯之前分析法学与历史法学论战后分析法学在西方法理学中已不再被广泛接受。这里,霍姆斯至少在两个方面使他与分析法学划清了界限。第一,他承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至少是在历史上司法实践上的紧密关系。第二,他对法律概念的独特见解。他不是从理论上对法律下定义,而是从具体司法角度去总结法律的含义。即一个坏人对法院将作出何种判决的一种预测。可以说霍姆斯已不属于19世纪西方已有的各种法学学派,他是一种新的法学学派的奠基者。有人称之为实用主义法律思想或实用主义法学[18],有人称之为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先驱[19]。 霍姆斯对法律与逻辑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传统法律观念的一种批判。批判的第一个目标是分析法学。一般地讲,分析法学关注的是“分析法律术语、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相互关系”[20]。以极端的德国实证主义法学为例,他们只要法的逻辑把握,不要法的价值判断。从司法实践上讲,他们要求法官绝对地忠诚于法律,司法原则是从法律的权限和程序上来确定合法性,而不问法律的社会经济和道德基础。由于这一缘故,德国实证主义法学被后人称为“概念法学”或“机械法学”。霍姆斯严厉地批判了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主义观点,使他与分析法学区分开来。他不是仅仅从实在法本身来分析或解决法律问题,而是从法律之外,特别是从法律的历史发展及法律后面的社会利益来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霍姆斯在其另一著作《普通法》中,也明确指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种经验既包括历史的经验,又包括社会的经验。不过,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经验。批判的第二个目标是理性主义法学。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直接影响了法律理论。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它被称为“古典自然法学”。逻辑,包括演绎和归纳,是这一历史时期法律思想的一种基本方法。格老秀斯首先将笛卡尔的数学应用到法律领域。他说,人类社会存在一项自然法的数学公理,从这个基本公理出发可以推演出自然法的一般原则。[21]在这种方法之下,自然法高于实在法,立法机关高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法官判案依据不得超越立法机关正式颁布的法律,即法官不能有自由裁判权。这种强调逻辑的理性主义法学构成了西方现代法律的理论基础,因而,逻辑的方法直至19世纪末都影响着西方法律界的思维方式。霍姆斯对逻辑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一种批判,正像当代现实主义法学家一样,他也被认为是对西方“法治主义”的一种背叛。 霍姆斯强调法律学习中的历史学习。他一度信仰过历史法学,曾“对历史地解释英美法律做出过杰出贡献”[22]。因此,不奇怪霍姆斯提倡法律学习中历史学习的重要性。但是,霍姆斯并不囿于历史。他认为,历史的学习是法律学习的基础,是法律学习的第一步,历史的研究是为了现在。历史是取代逻辑的方法之一,除了历史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利益和社会目的。为此霍姆斯建议律师们还要学好经济学和统计学。这反映了霍姆斯从一个历史法学论者向一个现实主义法学论者过渡的显著特点。事实上,《法律的道路》的发表在法律思想史上是历史法学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此后,历史法学作为一个法学流派已不复存在。但历史方法作为一种法律研究的方式通过其他法学流派得以保存下去。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 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是美国法学界最有权威的法学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会法学长期以来在美国法学中占有主导地位。他通过其主要著作《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法制史解释》、《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和《法理学》等,表达了他的社会法学思想。 庞德认为,法学是一专门术语,在实际使用中常被弄得混乱不堪。为了弄清确切含义,他从词源上加以分析。他指出:法学在英语中是jurisprudence,德语中是Jurisprndenz,二者都从拉丁语jurisprudentia得来。在拉丁语中,jurisprudentia是一合成词,由jur和isprudenre二词构成,前者解作义理,引申为法律,后者解作先见,引申为知识,即法学。在实践中,法院利用法学处理争讼,沿用日久,遂歧义孳生:古代罗马法学者用它表示法律见解;现代罗马法将它解作判案所循之途径;法语字典中,它被解作法院处理讼端时所持之态度;在英语国家,它被借用为“法院的判决”或者“法官所选择的法律”,甚至认作“法律”的同义异音之词。在现代社会中,法学是关于正义的科学。既然法学属于一门科学,其研究方法应是:第一,笃信谨守的研究;第二,穷源竞委的研究,即历史的方法;第三,条分缕析的研究,即分析的方法;第四,哲理的研究,即哲理的方法;第五,批判的研究。第一种方法仅限于对法律制度中规则及原理进行考核与注疏,因其过于拘谨,不足以成为科学方法,其他均属于科学的正当方法。在以上五种之外,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即庞德推崇的社会法学家所持的研究方法,他们将法律当做社会机器来研究,法律自身为社会而存在,其职能在于为社会服务。[23]
1916年的罗斯科·庞德 庞德用社会学法学的观点来解释法律,他说,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一直对此争论不休。但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是很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使用了法律这一名词。也就是说,法律这一概念具有三种意义,或人们在三种不同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概念。第一种意义是现在法学家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运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第二种意义是指一批据以作出司法或行政决定的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如通常所说的财产法、契约法等。第三种意义是指司法和行政过程,即为维护法律秩序而根据权威性指示以解决各种争端的过程。庞德认为,只有用社会控制的观念才能将这三种意义加以统一。总的说来,“法律就是一种制度,它是一种依照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的权威性律令来实施的,具有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24]。 庞德认为法律概念是十分复杂的,因各个学派的不同解释而带来很大的混乱。各学派所讲的含义又各不相同。如,分析法学所讲的法律,主要是指权威性律令中的立法因素。历史法学了解社会控制的连续性,但却看不到他的分化,因而也看不到社会法学所讲的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哲理法学仅注意法律中的理想成分。这三派都看不到法律中的司法和行政过程的意义。而20世纪的现实主义法学却把法律的这一意义当做它的全部意义。 庞德认为,社会学法学家目前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创立、解释和适用法律方面,应更加注意与法律有关的社会事实。为此,他在早期的论文《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提出了六点纲领,以后又在1959年的《法理学》一书中扩大为八点,其中第四点和第七点是新加的。[25]他进而提出了社会学法学与其法学派的区别: 可见,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大纲在理论上是相当系统的,从立法到司法,从法律程序到学说,从制度到组织等各个方面说明了社会学法学派别的理论相区别。由此可知,庞德所强调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
·注释· [1] Eugen Ehrlich,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reface. [2] Ehrlich,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of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23—24. [3]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4]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5]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6] 〔德〕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337页。 [7] 同上书,第342页。 [8] 同上书,第211页。 [9]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0] 〔德〕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1]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简惠美译,载《韦伯作品集》第V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12] 同上书,第216—217页。 [13]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简惠美译,载《韦伯作品集》第V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8页,第215页。 [14] 同上书,第217—218页。 [15] 〔美〕霍姆斯:《法律的道路》,载《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霍姆斯法学文集》,明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16]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第38页。 [17] Austin, On Jurisprudence,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85, p.172. [18]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282页;吕士伦、谷春德:《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增订本),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335页。 [19]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Hommes, Major Trends in the History of Legal Philosophy, N.H P&C, 1979, p.311. [20]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21] Hommes, Major Trends in the History of Legal Philosophy, N.H P & C, 1979, p.89. [22] 〔美〕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23] 参见〔美〕庞德:《法学肄言》,载《庞德法学文述》,雷沛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24]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页。 [25]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287页。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290页。 *推送中使用的人物肖像均取自wiki media。 推送正文摘编自徐爱国、李桂林:《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229—246页。文字有删节调整。欲了解完整内容,请直接阅读原书 图 书 推 介
本书以体系简洁、内容扼要、论述通畅、语言朴素为宗旨,以方便学习者的学习并掌握所学内容为目标,对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当代的西方法律思想进行了分析介绍。通过本书的学习,有助于更为深刻地了解西方法律制度发展和运作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充分了解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对从事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者以及对西方法律思想感兴趣的社会读者也极具参考价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