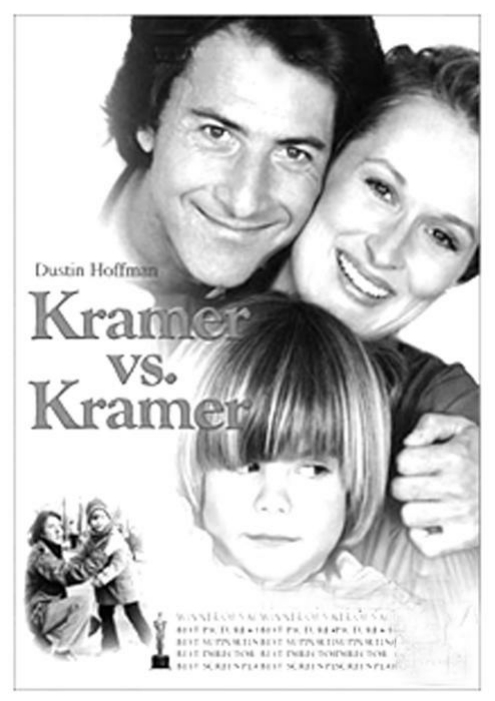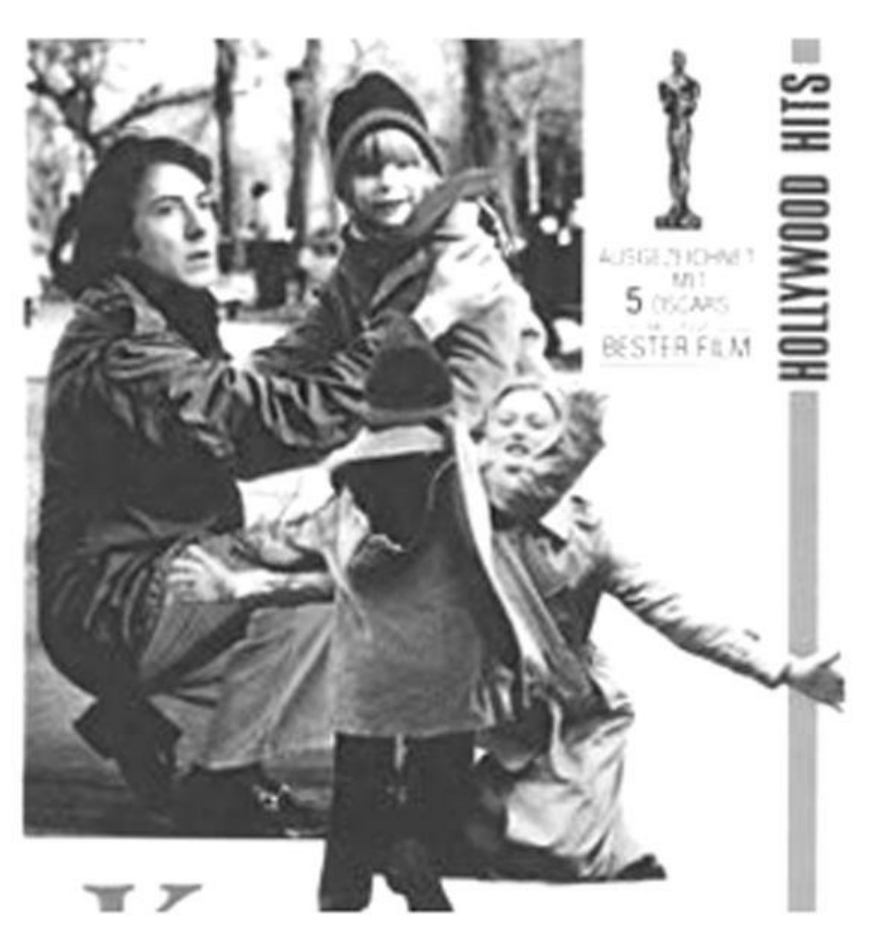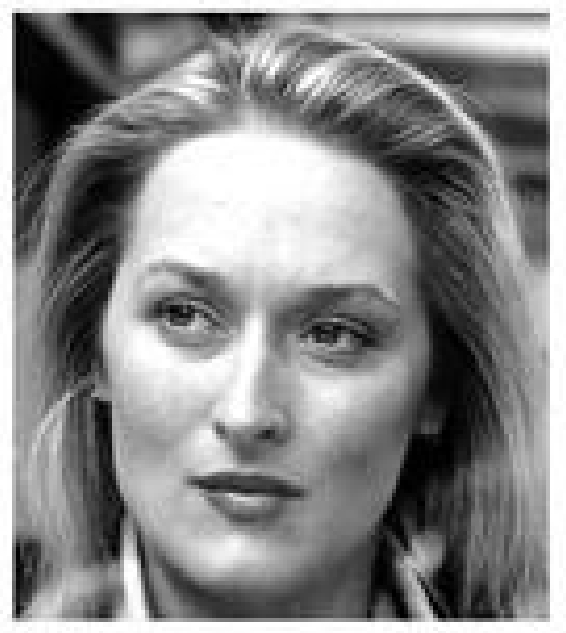| 奥斯卡影片《克莱默夫妇》:男权思想的胜出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乔安娜哭着离开的照片图片克莱默夫妇 › 奥斯卡影片《克莱默夫妇》:男权思想的胜出 |
奥斯卡影片《克莱默夫妇》:男权思想的胜出
|
奥斯卡影片《克莱默夫妇》:男权思想的胜出
时间:2022-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克莱默夫妇》:男权思想的胜出背景资料英文名:Kramer vs.Kramer编剧:艾弗里·科尔曼 罗伯特·本顿导演:罗伯特·本顿主演:达斯汀·霍夫曼 梅丽尔·斯特里普出品: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荣誉:1980年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共5项大奖。至此,影片明显的男性审视角度是毋庸置疑的。
《克莱默夫妇》:男权思想的胜出 背景资料 英文名:Kramer vs.Kramer 编剧:艾弗里·科尔曼 罗伯特·本顿 导演:罗伯特·本顿 主演:达斯汀·霍夫曼 梅丽尔·斯特里普 出品: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荣誉:1980年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共5项大奖。
内容简介 泰德·克莱默是一位广告职员,他整天忙碌而无暇顾及妻子乔安娜和6岁的儿子比利。终于有一天,乔安娜再也无法忍受每日无聊的生活,离开了丈夫和儿子,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了乔安娜,泰德的生活一片混乱。他无法兼顾繁忙的工作和照顾孩子两件事,经常遭到上司和儿子的不满。幸亏邻居帮忙,泰德终于对付过去,并逐渐和儿子变得亲密无间、难以分离。 转眼间一年多过去了,泰德忽然接到乔安娜的电话,两人在一家餐馆见了面。如今乔安娜已是收入丰厚的设计师,她回到纽约是想获得比利的抚养权,两人不欢而散。一场官司不可避免。然而就在此时,泰德却不幸失业。他几经努力,终于在24小时内又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法庭上,双方的律师全都咄咄逼人。虽然有邻居出庭作证说泰德是位好父亲,法官还是把监护权判给了乔安娜。为了避免给比利带来影响,泰德放弃了上诉,但泰德在法庭上的陈词也已经打动了乔安娜。父子俩分离在即,两人在一起做最后一顿早餐。就在等待中,乔安娜打来了电话,告诉他自己改变了主意,不再要求获得比利的监护权了。泰德父子终于不必分离。 获奖原因分析 影片由导演罗伯特·本顿亲自改编艾弗里·科尔曼的同名小说而成,反映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婚姻、家庭的种种问题,以及女性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诸多艰难和男权思想的强大。
影片是一部社会伦理剧,也经常被看做是一部展现男权思想的影片,反映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守主义思想的回潮以及女性在实现个体价值路途中的艰辛。影片上映后,很快在欧美各国引起热烈反响,美国《时代》周刊称它是一个在电影和生活中都很少见的奇观,又有评论称其是“最赚人眼泪的片子”。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展现女权主义思想的影片,迎合了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一轮的妇女解放运动,不过我们不能被影片的表象迷惑,我以为这是一部表象女权,内蕴男权,在男性/男权与女性/女权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最终男性/男权思想胜出的影片。 1.第二性的女性——乔安娜 影片开始于妻子乔安娜独自的黯然神伤:温柔地为儿子比利盖好被子,却无法掩饰内心彻骨的忧伤。接下来,镜头切换到了丈夫泰德的公司。此时的他正在老板办公室,双腿跷在桌子上,兴致盎然地讲着乏味的故事。回到家后,他完全沉醉于升迁的喜悦中,对妻子的忧伤全然不觉。直到乔安娜告诉他要离开的决定后,泰德起先以为她在开玩笑,随后恼怒,继而指责妻子:“你可真会挑时间。”他为自己一直晚归辩解的理由就是“我忙着赚钱养家”。这使得许多女性观众对乔安娜的家庭主妇生活感同身受:生活表象的平静下,隐藏着女性精神世界里的迷茫、困惑与无助,而丈夫却根本不予理会。随着故事的继续,我们看到了勇敢的乔安娜努力保卫自己的独立个性,追求生活意义。她不但经济上做到了独立,而且运用法律武器争取自我的合法权利,力图主宰自己与家庭的命运。如果说此时影片向观众展示塑造的仍然是一个有着女性意识的女性的正面形象的话,而此后这一形象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
在法庭上,律师问乔安娜,泰德是否曾经虐待过她和她的孩子,是否酗酒,是否对她不忠,是否让她生活在物资不足之中。乔安娜如实回答没有。律师便笑了,这笑里藏着男性对于乔安娜式女性的讽刺,也同时提出了社会对于她们的第一个质问:安逸而平静的生活之下,为什么还要出走?这是男性世界对女性寻求独立和自我价值体现的公然不屑。随后律师残酷地质问乔安娜,她人生中经营的最重要的关系——夫妻关系的失败是否证明了她的失败?乔安娜默认了。这是以律师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第二次责问,他们认为是由于女性的离开才造成了婚姻的解体、家庭的不幸。而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男人对于家庭,经常处在一种置身事外的状态。于是,虽然后来乔安娜成功地逃离了家庭进入到社会,甚至于她也成功地得到了法律上对儿子的监护权,但到最后,她却放弃了,她明白当她逾越了传统的性别次序进入男性世界时,她也失去了家庭。一个成功出走的“乔安娜”的光辉形象至此已经黯淡无光。导演深有意味地设定:告知乔安娜这一结果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女性。女性在被放逐的境遇里苦苦挣扎,最终却自己放逐了自己。这使我想到了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张洁在中篇小说《方舟》的题记中所写的:“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至此,影片明显的男性审视角度是毋庸置疑的。在他们眼里,女性永远都是附属的第二性。正如卢梭认为:男女两性的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这种生理上的差别决定了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母亲和妻子。男人/男性和女人/女性,事实上并没有真的平等。 2.第一性的男性——泰德
作为丈夫,泰德·克莱默漠视了妻子乔安娜的忧伤、痛苦,他极男权地以为如果“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没有打老婆虐待孩子”“没有外遇”,可以“努力养家糊口”这些“美德”完全具备,就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了。而当乔安娜离家后,他却连一顿像样的早餐都做不成。妻子在他心中,正如女性在绝大多数男性心中的形象一样,他们需要的是温顺、耐心、听话的妻子,而非有着独立意识的女性。他们以为自己幸福了,妻子便幸福了。如果这时候观众还比较同情乔安娜的遭遇的话,那么影片接下来展示的内容则使得观众的天平绝对倾斜于泰德。 首先,当泰德和比利发生矛盾时,懂事的比利先向泰德道歉,并问泰德,妈妈的离开是不是因为他不乖。泰德边安慰儿子边解释,“妈妈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一直想让她成为我想要的那种太太,她一直在努力使我开心。当她做不到时,她想和我谈谈,而我却只顾自己的事,没有听她倾诉。我以为只要我高兴,她就会高兴,其实,她内心里非常痛苦……”这番话使得观众开始原谅泰德。 其次影片用了大量篇幅展现父子相濡以沫的深情,比如忙得焦头烂额的泰德抽时间参加儿子的万圣节晚会,在台下为儿子加油;耐心地教比利骑自行车,帮他系鞋带;当比利不慎摔伤,泰德抱起比利狂奔进医院等。泰德由此成为了一个称职的、完美的父亲,完成了从一个“缺席的父亲”到完美父亲的转变。而所有这一切使得观众完全站到了泰德一边,深深同情父子俩的遭遇。于是等乔安娜再次出现时,观众对她的同情、怜悯的感情淡漠了,甚至于对乔安娜要带走比利产生了厌恶情绪。 泰德成了一个完美的父亲,但还是原来的丈夫。当乔安娜重新回到纽约,提出要带走比利时,泰德勃然大怒,把酒杯摔到墙上,愤然离去。他和乔安娜有一段对话: 乔安娜:我一生都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妻子、母亲或是女儿。就连我们在一起时,我也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离开的原因。在加州,我找到了自己,找了份工作……我对自己也了解了很多。 泰德(表情严肃):比如说? 乔安娜:我了解到我很爱我的孩子,我有能力照顾他。 泰德:你能确定他会跟你吗? 乔安娜:你不能拒绝我。 泰德(用手恶狠狠地指着乔安娜):不用你告诉我该怎么做,不要那样对我说话。 此后在法庭上,泰德仍然说,“乔安娜,别那样做,拜托你,别再度毁了他的生活。”可以看出,泰德作为丈夫,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仍固执地认为妻子抛夫离子是不可宽恕的,妻子的出走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毁掉了他如日中天的事业,也毁掉了儿子的幸福。显然,泰德的内心是极其保守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他是第一性的,也是不容侵犯的,乔安娜独立的生存是他不愿看到的。
而法庭上乔安娜的好友玛格丽特全然不顾法官的制止,力劝乔安娜放弃比利:“乔安娜,一切都变了,泰德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不知道他有多努力,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如果你见过他们在一起有多快乐,也许你就不会来打官司了。”胜诉的乔安娜泣不成声地对泰德说:“我来这儿是接孩子回家,却突然意识到这儿才是他的家。”这些则是男性/男权中心主义者赤裸裸地为男权社会所唱的赞歌,男人才是家,才是归属。 由此,可以看出电影始终在隐秘地诉说:乔安娜/女性离开丈夫/男性寻找自我是错误的,工作会让女人/女性失去爱情、婚姻和家庭,并且得不到道德上的认可。反过来说那些放弃了事业的女性则受到赞扬,但她们不会去在意事业和她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在意她们个人价值的得失问题。在社会已进入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男性中心主义仍然不相信个人的选择价值,不相信女性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女性每前进一步,男性则会变着法地把女性重新围困,这让人感到心痛和悲哀。 (李金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