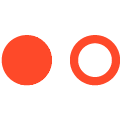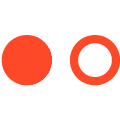| 【学术撷英】龚世琳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乌托邦之死 › 【学术撷英】龚世琳 |
【学术撷英】龚世琳
|
莫尔 01
《乌托邦》的写作背景 托马斯·莫尔,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天主教的圣徒和殉道者,亨利八世的王庭重臣,生于1478年,正当里士满伯爵(亨利七世)与理查三世争夺王位之际,卒于1535年,时值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关键之期。在莫尔的所有作品中,《乌托邦》(书的全称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为他赢得了最多的赞誉,成为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乌托邦》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记述了拉斐尔(莫尔塑造的人物)批判讽刺英格兰的政治和经济现状。第二部分借拉斐尔之口描述了乌托邦——一个遥远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制度和相关事务。据莫尔的好友伊拉斯谟记述,莫尔在闲暇之际先写作了《乌托邦》的第二部分,而后又补足了第一部分。[4]因此,第一部分可以作为莫尔对第二部分内容的补充说明,此补充不但使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更加明晰,同时也突显了他的写作意图。 《乌托邦》(拉丁文版)最早于1516年底出版,由此可得知,此书应该是在1516年之前完成的。莫尔自己并未留下对《乌托邦》一书的详细解释,我们已经难以通过直接的文献记述追踪莫尔写作《乌托邦》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莫尔的生平以及英国的政治状况来揣摩本书的写作背景。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问,在此期间,他结交了一大批人文主义者,深深为人文主义[5]折服。虽然囿于父亲的担忧,莫尔后来被迫从牛津退学改学法律,但他对古典学问的热爱与钻研并未就此消解。相反,法律和政务的相关实践更是促他思考起学问与英国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来。1515年莫尔出使荷兰,负责处理英国与当地商人之间的羊毛贸易纠纷。[6]在出使期间,他继续阅读伊拉斯谟的书稿,并同荷兰的北方人文主义者彼得·吉利斯(Peter Gillis)等人交流。[7]1515年9月,莫尔在布鲁热(Bruge)出使期间开始构思写作一本小册子,想向身处历史剧变中的人们(确切的说是君主与贵族)[8]描绘一个理想之邦。 纵观莫尔的一生,他经历了王权争夺之战、都铎神话的开启、至尊王权的建立这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难想象,动荡多变的政局和“新”英国必然给莫尔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从战争中复苏的“新”英国亟待一位英明之主带领国民重塑辉煌的历史。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皆以恢复王权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统治重心。英国在14-15世纪的内耗和权力争夺让亨利七世认识到,王权之所以衰微,乃是缺乏一个强大的国王。于是,他上台后便联合中等阶级大力打压贵族力量、充斥王室财政、取缔贵族武装。[9]亨利七世将英国逐步从战乱带向繁荣,的确显示出一副救国之主的态势。莫尔毫不掩饰自己对英主的期待和盼望,但他也警惕着英主或许会变成暴君。正当亨利八世继位后大肆开展对外战争,消耗国库,继而对民众苛以重税之时,莫尔似乎看到了危机。 《乌托邦》诞生在莫尔深切思考英国未来、构建人文王国之时;也诞生在英国向上攀登、重建繁荣之际。《乌托邦》是莫尔对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的致敬之作,同时也是他在“哲人为王”难以成真的现实窘境之中,尝试提出替代性统治策略的立法之作。莫尔对“一”的信仰和他对秩序的坚持贯穿《乌托邦》全书。在他看来,秩序的建立和持续运转离不开一位“贤明君主”,更离不开一套“圆满”的运行机制。尽管莫尔对自己的“乌托邦”社会充满信心,但他在现实政治中遭遇的挫折似乎也在宣告,对“一”和秩序抱有信心的人们都必将经受梅菲斯特的诱惑,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或与“一”共荣,或将其败坏。 02
乌托邦统治的确立 在《乌托邦》的第二部分,莫尔借拉斐尔之口向人们介绍了一个拥有一千七百四十年历史的“乌有之乡”——乌托邦。[10]乌托普(Utopus)国王登上了四面环海的岛屿,开启了乌托邦国的新纪元。在这片看似“遗世独立”的国土之上,[11]财产公有、城市整齐划一、人们分工有序、实行共餐制、人们视金钱如粪土、生活幸福快乐。莫尔将这个国家称为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媲美的完美城邦。我们知道,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理想国》中,也正是以哲人的身份勾勒出了一个或许只能在天上存在的理想国度,[12]他还指出只有哲学家才能构建和统治这个国家,得出了著名的“哲人王”论。“哲人王”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理想国”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据柏拉图说,《理想国》中的“哲人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城邦唯一的统治者,便在于他既可以上达理念世界,又能下降到现实世界,最终还能返璞归真。换言之,“哲人王”因拥有通达的能力被赋予了统治权。在莫尔笔下,虽然拉斐尔告诉读者,乌托邦是由乌托普国王建立而成,但他却并未言明乌托普此人的确切身份。[13]只是我们依稀得知,“乌托普登岛取得胜利,并使乌托邦岛屿上未开化的淳朴居民成为有文化和教养的人。”[14]可见,乌托普不但是建国之父,同时也担任教化之责,俨然一副“君师合一” [15]的统治者面貌。[16]这样一位“君师合一”式的统治者既取得了政治统治权,又手握文化统治权。作为城邦统治者的乌托普究竟因何被赋予统治权力呢?他究竟是不是“哲人王”式的人物?他是否像“哲人王”那样具备上达下知的能力呢? 就乌托普“君师合一”的身份而言,莫尔似乎默认了乌托普本人兼具建国和教化之德,也默认了他“哲人王”的身份。乌托普武力建国的“成果”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又是如何完成“哲人王”的统治的呢?换言之,他是如何合法地实现其文化统治的呢?莫尔在处理这一问题选择将文治与宗教结合起来,他告诉我们,乌托普即便贵为乌托邦的建造者,却也无法独自确立一统的宗教(文治),这一论断将全能的乌托普又打回了世俗君主的原型。 据拉斐尔言,乌托普对于宗教问题不轻易做出判断,因为他无法确定上帝的意愿。于是,乌托普在登岛后便立下规定, “每人信从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是法律上认可的,一个人也可以向别人宣传自己的教,劝其接受,但只能用温和文静的方式,讲出道理为自己的教作辩护,如果他劝说无功,不应将其他一切的教都恶毒地摧毁,不得使用暴力,不得诉诸谩骂。如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龂龂争辩,态度过分激烈,他将受到流放或奴役的处分。”[17] 这种具有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性质的规定被后人称道,同时也是《乌托邦》提倡“自由”的明证。[18]然而,这种“自由”是有边界和限制的。例如, “乌托普把宗教的全部问题作为一个尚有待解决的问题,容许每个人选择自己的信仰。可是有例外,如他严禁任何人降低人的尊严,竟至相信灵魂随肉体消灭,或相信世界受盲目的摆布而不是由神意支配。”[19] 可见,信仰自由只在宗教信仰者内部适用,无神论者是被排除在外的。无神论者不但被“自由”排斥,还受到人们的鄙视,因而无法成为乌托邦真正的公民。有趣的是,乌托邦人虽然剥夺了无神论者的一切政治权利,却并没有驱逐他们,反而“允许并鼓励他们在教士或者重要人物面前为无神论做辩护”[20]。如此看来,乌托邦的统治者似乎对无神论者仍然抱有积极的期待,坚信“理性”[21]终会将他们招安。于是,无神论者成为乌托邦边缘地带的流民,在极小的范围内秘密地享有“自由”。 据说,乌托普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对无神论者的限制),一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定,避免因宗教争端引起内乱;二是为了促进宗教自身的发展。温和的宗教政策自然有利于消除宗教争端,保证国家安定,但它又如何得以促进宗教自身发展呢?这便同另一则限制性条件相关了。乌托邦人尽管信仰不一,却一致承认只有一个至高的神,此神乃是全世界的创造者和真主宰——“密特拉”(Mithras)[22]。可见,即便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人也受到一些限制性条件的约束。“一神论”[23]是排斥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为什么在乌托邦岛上,“一神论”能够与宗教信仰自由并置呢?想要弄清楚这一难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乌托邦人为什么选择信仰“密特拉”?他们究竟是被迫选择信仰“密特拉”,还是像无神论者那样被“理性”招安而信仰“密特拉”?据说“密特拉”就是“自然本身,由于其无比的力量和威严,任何民族都承认,万物的总和才形成”。拉斐尔言,乌托邦岛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较有见识的人(the wiser),只信某个单一的神”[24],也就是“密特拉”。此外,为了不让读者认为“乌托邦人是因武力而被迫信仰‘密特拉’”的,莫尔强调,若能用温和而合理的方式处理问题,真理(“密特拉”)凭其本身的自然威力迟早会自己呈露出来。因此,乌托普虽能以武力征服乌托邦人的领土,却无法(或不愿)用同样的方式征服乌托邦人的信仰。[25]换言之,乌托普要成功教化民众,就必须借由“真理”本身显其威力。据莫尔说,“密特拉”不为人所知,奥妙无穷,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悟解。[26]虽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无法理解神祗的这些人当中是否包括乌托普本人,但他明确暗示我们,乌托普选择了与“密特拉”合作。正是这种合作让他具备了化信仰于民的能力。换言之,乌托普与“密特拉”的合作既让他解决了宗教难题,也使其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就这样,乌托普在乌托邦岛上润物细无声地推行“密特拉”信仰,有力地促进了“宗教”自身的发展,使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归顺于政治统治,建立了卢梭意义上的“公民宗教”[27]。 看来,在“密特拉”信仰之上推行宗教宽容政策,不过是统治者为了保证国家安定而选择的统治方式而已。这种方式并不会阻挡“密特拉”在乌托邦岛上的暗流涌动。推而广之,被剥夺政治权利且无法公开宣讲的无神论者,因为看似不具备威胁统治的能力而显得不足为惧,仍为统治者所容。这样看来,乌托普与“密特拉”的合流正是其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有力支撑。通过与“密特拉”的合作,乌托普便取得了君师合一的“师”的地位。就在莫尔提出这一大胆设想的二十年后,他因反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为天主教殉道而死。反讽的是,恰恰是这位将莫尔处以死刑的“暴君”亨利八世,在英国完成了王权对基督教的“招安”,将代上帝立言变为世俗政治的事实。 问题还在继续,有着一千七百四十年历史的乌托邦并不只有乌托普这一位君主,乌托普以“圣人为王”的姿态坐实了统治者的交椅,但乌托普以降的君主(统治者)又是如何持续拥有其统治地位的呢?换言之,乌托普运用武力征服和信仰统治完成了他的“哲人王”统治,但其后继者又是如何继承这种“统治”,使其持续具有合法性的呢? 03 乌托邦统治的延续 前文提到,乌托普通过与“密特拉”的合作取得了替天行道的文化领导权,成为乌托邦的“师”。反之,“密特拉”也正是通过归顺乌托普而获得了存续的权力。乌托普逝去后,“密特拉”便成为乌托普的化身,替乌托普行道。“密特拉”神是古代波斯祆教的主神之一,是光明之神。正如乌托普为乌托邦岛民带来幸福生活那样,“密特拉”也为人们带来了“光”。[28]此外,“密特拉”这一词在古梵语里有“契约”的意思。[29]作为契约之神的“密特拉”成为乌托邦人的唯一神和永恒神,这本身是否就意味着乌托普的统治正是以契约的方式得到乌托邦人的尊崇呢?[30]倘若如此,乌托普的后继者也能因“密特拉”(契约)继承乌托普的统治,而这个契约能否得以存续取决于后继者是否尊崇乌托普的治国方略。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因契约继承国家统治权的君主是否像乌托普本人那样拥有上达下知的能力呢?乌托邦如何保证王位的后继者如乌托普那样成为哲人式的王呢?[31] 在乌托邦这个整齐划一的国度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可以被免除劳作,专心学术研究,他们同时也承担着给乌托邦人公开讲学的职责。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中,“乌托邦人选出了外交使节、教士、特朗尼菩尔,乃至总督”。[32]换言之,乌托邦的统治实际上是掌握在这个特殊群体手中的。我们有理由推断,乌托邦的教化问题与这个学术群体密不可分。有趣的是,此处那个一开始便以“君师合一”的形象出现的乌托普国王却突然消失了。莫尔虽明确表示,乌托邦的官员由城邦子民选举产生,官员因民主选举而享有其合法性,学术群体因其学术研究而享有成为官员候选人的资本,却他并未说明这些官员与统治者,即这些官员与国王乌托普及其后继君主之间的关系。虽然莫尔在《乌托邦》第二部并未言明统治者与学人群体之间的关系,但他却在稍后补足的第一部中安排了可供读者探寻的线索。 在第一部的对话中,莫尔劝拉斐尔进入王廷当一位伟大国王的谋臣,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聪明勤奋用于为公众谋福利”,才能与其“宽宏而真正富于哲理的气概相称”。[33]为了劝说高傲的拉斐尔,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搬出了柏拉图的“哲人王”论,认为“只有哲学家做国王或是国王从事研究哲学,国家最后才能康乐”。[34]哲学家做国王和国王从事哲学研究是两回事,前者暗含了哲学家可以攫取权力,后者则暗示了哲人群体应劝导和教化已经取得统治权的国王向善向学。莫尔将这两种不同的抉择并举,可见在他心中,无论是哲人攫取权力自己当国王,还是已经成为国王的人从事哲学,对于国家而言都是有利的。既然它们都有利于国家和公共福利的,便是可取之道。那么,像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这样通过战争和继承法取得王位的国王,是否天生便是能够达知真理的 “哲学王”呢?显然不是。在莫尔的时代,确切说来在现代早期的英国,没有所谓的“哲学王”,只有因势利导、不惜代价成就霸业的君主。既然没有在世的“哲人王”,那么作为哲人的莫尔自然要担负起教化和辅佐君主的重任。尽管“圣人为王”、攫取权力已难以实现,但“王为圣人”尚是哲人实现理想城邦的救命稻草。面对拉斐尔拒绝的言辞,莫尔不禁悲叹,“假如哲学家不屑于向国王献计进言,康乐将是意见多么遥远的事”[35]。莫尔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的母邦一定会有一位像乌托普式那样谨慎、果决、睿智的君主。他在自己的从政生涯中,也的确试图通过自己掌握的人文知识将亨利八世“培养”成为一位明君。他坚信,只要哲人愿意教导和辅佐国王,圣人治国便是可行的。而在书中,拉斐尔(莫尔本人)却警告他(读者)“如果国王本人不从事研究哲学,国王就绝不会赞同真正哲学家的意见”。[36]因此,哲学家为了保全自身,便将说谎当作了自己的本分[37]。虽然莫尔本人明知“哲人”介入政治需要担负风险,但他仍然选择,只要乌托邦真实可寻,他愿意且能够在抵达乌托邦国土的航程中承受任何反噬。不知是为了慰藉莫尔的崇高理想,还是为了化解“哲学家应该说谎”的难题,拉斐尔随即向莫尔叙述了一个能够承载“王为圣人”甚至“圣人为王”理想的“乌托邦”。 此时,当我们再次回到乌托邦岛,便可轻易得知乌托普的后继者究竟是如何再次成为“君师合一”式的统治者的了。一方面,这些后继者通过密特拉的契约,继承了乌托普的王位,成为法理上的“君”。另一方面,正像莫尔进入亨利八世王廷辅佐君主那样,乌托邦的学人群体也通过辅佐统治者使理想城邦得以延续。换言之,在学人群体的辅佐下,后继的统治者便得以达知真理,因而继续成为乌托邦的“师”。莫尔对乌托普和乌托邦统治者的想象承载了他对理想君主的期待,而那个在乌托邦岛上拥有特殊权利的学人群体恐怕就是以莫尔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群体。莫尔正是通过利用学人群体坚守和传承制度设计的方式,让乌托普及其后继者都能成为教化大众的“哲学王”,最终完成了知识与权力的合谋。 无论是乌托普本人,还是由其后继者和学人群体共同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都可以作为“秩序”的守护者和代言人。但这种单一、固化的统治模式是否存在潜在的危险呢?倘若统治者不再贤明,统治集团不再奉行乌托普建邦的理念,乌托邦这片乐土如何延续?他告诉读者,“乌托邦的公共法令或是贤明国王公正地颁布的,或是免于暴政和欺骗的人民一致通过的”[38]。其言下之意是,贤明国王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原本是一致的,二者都指向一个公共利益。莫尔在这个问题上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统治者的设想提前了百年之久。当霍布斯指出“君主国中,主权者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回事”时,不知其脑海中是否闪现了乌托普之名呢?但莫尔也指出,当君主不再贤明时,民众为了免于暴政和欺骗,是也可以跨越君主,再造乌托邦的,此中已然暗含了乌托邦中的“革命”因子。然而,莫尔对于人民如何反抗暴政又言之甚少。他似乎不愿意相信,乌托普确立的良好制度会产生一位“暴君”。应该说,他不愿相信,经过人文主义淘洗的君主会抛弃他自身得以存续的“合法性”。而现实恰恰就是如此残忍,当亨利八世处死莫尔之时,莫尔或许才意识到,自己苦心勾画出的“理想城邦”蓝图本就潜伏着“暴政”。 04 莫尔之死与乌托邦的幻灭 16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已不复往日之辉煌,以路德教为首的新教教派如“洪水猛兽般”冲击着整个欧陆天主教。被基督教用彼岸救赎美化的“一”在持续千年之后,终于受到“多”的不满与反叛。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基督教秩序遭到破坏,而本来依赖于秩序而得以延续的信仰自然也被动摇。从《乌托邦》所呈现的统治状况来看,莫尔似乎还无法设想出一个没有在世君主,没有“一”的国度。他不但为《乌托邦》的统治制定了完备的计划(乌托普与“密特拉”的合流),还为使这种统治能流芳百世制定了辅助计划(学人群体秉承乌托普遗命辅助治国)。虽然莫尔深谙秩序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保守地对待秩序问题。莫尔对腐朽奢华的罗马教廷以及固化的宗教体制十分不满,他在《乌托邦》第一部中就直截了当地借拉斐尔之口批评了当时的宗教局面。更有趣的是,莫尔在宗教改革浪潮之前便提出一种“新”的宗教形态的,可见其用意深远。[39]他在天主教一同天下的局面趋于被打破的时刻抬出了“密特拉”神,似乎有意用异邦神的秩序代替已有的天主教秩序,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十分激进的。 早在古罗马时期,从祆教演变而来的密特拉教就曾同基督教一争天下。无独有偶,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且其教义亦有相似之处。公元4世纪,基督教终于战胜密特拉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40]拉斐尔在向莫尔描述“乌托邦”的理想国度的终章,也向莫尔透漏,如果乌托邦的国民在信仰问题上“弄错了,或是如果比起他国家的这个信仰还有更美好的并且更为神所赞许的,他就祈求神慈悲为怀,让他有所了解”[41]。换言之,如果统治者宣扬的宗教不符合“密特拉”精神,民众可以选择不信仰。[42]莫尔想用“密特拉”重建秩序不假,但这秩序究竟是什么?从《乌托邦》一书来看,“密特拉”信仰似乎应当将财产公有、民主选举[43]、以农为本、一夫一妻、会餐制等一系列思想囊括在内,而这种信仰又必须通过“哲人王”和学人群体的合作得以实现。当知识(智慧)借助权力构建国家和教化民众之时,谁也不能保证权力不会反噬知识(智慧)。 《乌托邦》一书问世后,莫尔于1517年进入亨利八世的王宫为国王服务,逐渐成为亨利八世王庭的重臣。在此期间,亨利八世曾与他一起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推崇人文主义。莫尔也曾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明君”。然而,复杂的欧洲政治格局和英国的现状,使亨利八世不得不重新考虑施政纲领。这位有名的“暴君”在不久之后便选择了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亨利八世于1534年通过了《至尊法案》(Supremacy Act),确立了国王对宗教的绝对领导。莫尔因拒绝承认法案而被关进伦敦塔,于1535年被砍头。亨利八世用权力和武力征服宗教的做法,与乌托普和“密特拉”合作有何区别?莫尔希望通过人文主义涵养君主,也期待着建构起一个符合学人群体理想的社会。但他却忽视了,在君主眼中这些“理想”是可以被随时舍弃的筹码,多年的从政生涯将他的理想一一击溃。那么,当莫尔用殉道行为捍卫信仰之时,他究竟捍卫了什么?是自由?还是“密特拉”?如果他捍卫的是“密特拉”,他捍卫的究竟是“密特拉”信仰的内涵,还是其实现方式呢? 就在莫尔殉道、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确立“至尊王权”之后,经受了宗教运动洗劫的大不列颠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一大批学者和作家投入到人文主义的浪潮之中,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成为整个欧洲最耀眼的文化圣地。英国建立了民族国家,大不列颠终于崛起,这一结果离莫尔在《乌托邦》中的理想究竟还有多远?莫尔对柏拉图的复归绝不仅仅是一个为了显示其人文主义立场的复古游戏,而是包涵深切的政治和人文关怀的。在《理想国》的结尾处,柏拉图对格劳孔说:“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44]乌托邦的历史也有一千七百四十年之久,而从乌托邦成书之年到当下也恰好五百年。五百年沧桑,乌托邦被践行,被毁灭,或将继续被建构,被毁灭……它自身存在的裂隙和矛盾又能否得以缝合和调解?这是我们将在未来一千年的旅程中继续探索的问题。 [1] 刘小枫,《莫尔及其乌托邦》之《中译本重印说明》,考茨基著,关其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页。 [2] 关于以莫尔写作《乌托邦》的立场来论述“理想政制”真实性问题的相关研究,参见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对人文主义的批评》一节,奚瑞森、亚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88-391页;see Richard Rex , “Thomas More and The Heretics: Statesman or Fanati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More, edited by George M. Logan.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3-115. [3] 鲁思·列维塔斯,《乌托邦之概念》,李广益、范轶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7页。 [4] 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第112页。有说法认为莫尔是在沃尔西主教的鼓励之下补足《乌托邦》第一部分的,See Peter Ackroyd, The Life of Thomas More, New York : Nan A. Talese, 1998, p177. [5] 学界对“人文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其历史效果也较为复杂,此处的“人文主义”泛指14-16世纪欧洲兴起的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代表的思想的总称。 [6] 凭借其优异的法学背景和实践经验,在《乌托邦》成书前后,莫尔曾多次被亨利八世派往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处理英国商人与当地商人之间的矛盾。 [7] 北方人文主义者:泛指阿尔卑斯山以北,与意大利相对的德国、荷兰等国家的人文主义者。See Peter Ackroyd, The Life of Thomas More, New York : Nan A. Talese, 1998. James Mcconica, “Thomas More as Humanis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More, edited by George M. Logan,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2-42. [8] 莫尔在写作《乌托邦》时采用拉丁文而非英格兰的民族语言,可见他对文本的受众是有相当期待的。彼得·艾克罗伊德认为,莫尔用拉丁文写作,恰恰暗示其延续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院派和修辞学家关于理性和启示的辩论,即法律究竟是出自上帝或国王,还是人们之间自然协定和结合的结果”。See Peter Ackroyd, The Life of Thomas More, New York : Nan A. Talese, 1998, p173. [9] 钱乘旦,《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112页。 [10] 乌托邦(Utopia)一词由两个希腊词οὐ (没有) 和 τόπος (地方)组成,意为“子虚乌有之地”。 [11] 莫尔描绘的“乌托邦”虽是人间乐土,但其富饶繁荣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外邦和殖民地的掠夺之上的。 [12]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389页。 [13] 乌托普登上乌托邦岛必然经过了武力争夺,莫尔在此虽未明说,却以征服者“取得胜利”暗示了暴力的存在。即便暴力建国是可推测的,但乌托普本人的身份仍然被隐藏了。虽然莫尔在给伊拉斯谟的信中表明自己就是“乌托邦”的君主,但本文试图讨论的不是莫尔与“乌托普”的对应关系,而是作为“乌托邦”统治者的乌托普在统治方面具备哪些特质。关于乌托普的暴力建国及其合法性问题,参阅张沛,《乌托邦的诞生》,《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14] Thomas More, Utopia, edited by Edward Surtz,S. J.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1964, p133.(译文引自戴镏龄译本: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版。) [15] 这种“君师合一”的统治者形象在英国思想史上并不少见。莫尔之后,培根在他的习作《新大西岛》中也塑造了一位能替天行道王者“所罗蒙那”,而稍后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更是将世俗君主作为“可朽”的上帝,赋予其全知全能的法力。培根与霍布斯均是在英国宗教改革后至尊王权得以成功确立的情景中,看到了替天行道的“在世的上帝”,而莫尔却是在此之前便“预测”了政治统治如何收服宗教,如何确立“在世上帝”的过程,其洞察力令人惊叹。 [16] 建国之父和教化之则实际体现为乌托普作为征服者和建设者的双重身份。See Dominic Baker-Smith,“Reading Utopi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More, edited by George M. Logan. Cambridge, UK;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49. [17] Thomas More, Utopia, pp219-221. [18] Stanford Kessler在“Religious Freedom in More’s Utopia”中列举了研究者对《乌托邦》中“宗教自由”的不同阐释,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莫尔将“宗教自由”视为一种积极的改革力量,另有人则认为莫尔在讽刺和质疑“宗教自由”的可能性。总得来说,这两种推测皆是在本文于开篇提出的两种阐释《乌托邦》的方式的框架内进行的。这一“巧合”恰恰印证了,如何认识《乌托邦》中的宗教和统治问题,对于我们阐释《乌托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Kessler认为一些西方学者鉴于《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因素而忽视了莫尔在“宗教自由”方面的建树,在他看来,莫尔提出的“宗教自由”具有非常强烈的基督教(天主教)改良色彩。See Stanford Kessler, “Religious Freedom in More’s Utopia.”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4, no. 2, 2002, pp207-230. [19] Thomas More, Utopia, p221. [20] Thomas More, Utopia, p223. [21] 在莫尔看来,理性即遵循自然的指导,而自然的指导的核心是对上帝的爱和敬。换言之,“理性”的内核是对上帝和善的“信仰”。 [22] Thomas More, Utopia, p217. [23] 密特拉神(Mithras)是古代波斯祆教(拜火教)的太阳神,他与阿帕姆·纳帕特(Apam Napat)和马兹达(Mazda)并列为伊朗-雅利安人的抽象神中最重要三位神,这三个神各自都能被称为“主”,因此每一个神是独立的、一神的。(参阅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39页。)莫尔或许以此暗示乌托邦的信仰仍然是“一神论”的。 [24] Thomas More, Utopia, p217. [25] 事实上,“密特拉”信仰的推广必然不全是“温和”的:作为契约之神的密特拉肩负双重职能,一方面,他是一切契约的保护神,是守约之人的朋友;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切违背契约者的敌人,惩罚违背契约的人。因此,他是战争之神。因此,作为战争之神、裁判之神代言人的“密特拉”可以随时对违反契约,不信仰密特拉的人使用武力。换言之,“密特拉”信仰本身就包含了“暴力控制”的涵义。 [26] Thomas More, Utopia, p217. [27] “密特拉”对各种宗教信仰的整合,恰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述,“我们就应该宽容一切能够宽容其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密特拉”作为契约之神,监督人类各种行为,裁判哪些合乎契约,哪些不合乎契约。在祆教的《密特拉颂》里,密特拉被想象为一个警醒的守望者,千耳、万眼,洞悉人间万物。每天,在太阳普照群山之巅以前,密特拉就循着太阳的轨道,由白马拉车出巡;他手执青铜仗,身佩长矛、弓箭、刀和投石等兵器……消灭一切胆敢违背契约的恶徒。(参阅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第40页)足见,乌托邦的“密特拉”教有明显的专制特征,这种专制特征在卢梭那里同样得到体现,一旦“公民宗教”成为排他性的与暴君制的时候,它就会使全民族成为嗜血的和绝不宽容的”。(参阅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版,第175页。) [28] 《旧约·创世纪》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此处的“密特拉”正是乌托邦人的“耶稣”。同样,“密特拉”或乌托普正是乌托邦人的救世主。 [29]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第39页。 [30] 莫尔利用“密特拉”的契约职能暗示统治的合法性,虽不及后世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在主权让度上的论述明晰,在当时已属惊人之举。 [31] 《理想国》第六卷苏格拉底和阿德曼托斯也曾讨论国王或统治者的后代是否生而有哲学家天赋,苏格拉底的答案是肯定的。 [32] 特朗尼菩尔又称首席飞拉哈,是总督之下的高级官员,而总督则是一个城市的主要长官。城市的市政管理皆在这些官员手中。 [33] Thomas More, Utopia, p57. [34] Thomas More, Utopia, p87. 莫尔在此处援引了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五卷、第六卷的相关论断——“哲学家应成为国王或统治者”、“确定哲学家为最完善的护卫者”。 [35] Thomas More, Utopia, p87. [36] Thomas More, Utopia, p87. [37] Thomas More, Utopia, pp99-101. 莫尔引用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496E中的比喻:哲学家在下雨时为了避免自己被淋湿,而不会外出劝雨中的人们避雨。在说话人苏格拉底看来,在不能容纳哲学家的城邦中,哲学家保持沉默(而非说谎),一方面是为了不参与城邦的恶,另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力量弱小不足以抵抗野兽。他进而得出结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才能充分地成长,进而能保护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莫尔借拉斐尔之口区分了深谙政治统治的哲学家和坚守经院哲学的哲学家之间的区别,得出一个结论,在他们所处的国家里,说谎乃是哲学家的本分。 [38] Thomas More, Utopia, p165. [39] 狭义的宗教改革通常以1517年路德《九十五条论纲》开始,而《乌托邦》于1515年成书,1516年出版。 [40]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第179页。古罗马时期产生了一种脱胎于祆教“密特拉”信仰的“密特拉”教,普鲁塔克的《庞培传》中即描绘了小亚细亚地方的海盗信仰“密特拉”教。 [41] Thomas More, Utopia, p237. [42] 莫尔用殉道完成了对亨利八世神权政治的不信仰,虽为“自由”献身,但实际也落入自己拟构的乌托邦陷阱当中。 [43] 乌托邦的官员是民主选举产生,但这些官员的候选人只能从有学问的人之中选择。因此,这是一种有限的民主选举方式,其实质仍未超出“学人群体”治国这一基本主张。 [44] 柏拉图,《理想国》,第430页。 编辑 | 董 越 责编 | 魏域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