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国学术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东方与西方的科学原文有哪些 › 南国学术 |
南国学术
|
在迄今已被译为近四十种外国语言的《东方主义》译本中,有两个阿拉伯语译本即赛义德母语的译本引人注目。其一是叙利亚诗人和批评家迪布(Kamal Abu Dib)的译本,1981年由设在贝鲁特的阿巴拉研究所出版。其二是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开罗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艾那尼(Muhanmmad Enany)再度将《东方主义》用阿拉伯语译出,由鲁雅(Al-Ru’ya)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比较两部译作,其不同个性甚至在书名的副标题上也可见一斑。迪布译作的副标题是《知识、权力和建构》,艾那尼译本的副标题则为《西方的东方概念》。迪布译本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本土化,避免使用西方流行术语,诸如“话语”“拟像”“范式”“代码”等等,即便这些术语在阿拉伯语中早已屡见不鲜。为此,赛义德在《东方主义》1994年的再版后记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艾那尼的译本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有意识走通俗路线,用现代阿拉伯语对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思想。在篇幅长达二十页的“译序”中,译者说道:“我翻译《东方主义》的使命,是基于两个考虑。其一是清晰接力爱德华·赛义德的相关概念,即便用阿拉伯语境来重建有些英语结构,殊属不易。其二是在现代阿拉伯语境中,保留爱德华·赛义德风格中的特殊品质。”这个宗旨比较在先一心求“雅”的迪布的译本,可谓更看重“信”“达”。该译本初版很快售罄,一度跻身埃及畅销书榜首之列。 一 东方主义与霸权 《东方主义》初版于1978年。作者在书的“致谢”部分说,他虽然关心东方主义由来已久,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1975—1976年间写成的,那时候他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在1994年的“再版后记”中,他又说道,像他这样一种将权力、学术和想象糅合于一体,来回顾过去两百年来欧美视域中的中东、阿拉伯和穆斯林叙述,能不能吸引广大读者,心里是没底的。2003年,该书又出版了二十五周年纪念版,作者增添了新的序言。今天,在该书面世四十多年之后,回过头来重读赛义德所写的著名“导论”,依然可以感觉到一种貌似感伤主义的情怀作态扑面而来: 在1975至1976年可怖的内战期间,一个法国记者造访黎巴嫩,伤心地记下了市区地带的满目疮痍景象:“它曾经似乎是属于……夏多布里昂和奈瓦尔的东方啊。”当然,他没有认错地方,特别是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总是一种欧洲的发明,从古代起,它就始终是一块充满了罗曼蒂克、异国情趣、神思梦牵、美妙回忆和美丽风景的土地,那里的经历精彩绝伦。如今,它在渐行渐远。一定意义上说,它已经消逝,那个时代结束了。 之所以说那是一种情怀作态,照赛义德的意思,那是活该。他接着指出,在这幅图景中,东方人,自打夏多布里昂(F-R. d. Chateaubriand,1768—1848)、奈瓦尔(G. d. Nerval,1808—1855)时代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东方人,其生生死死是无足轻重的;对于欧洲旅人来说,举足轻重的是表征:如何来表征东方人和他们的当代生活?这就事关紧要了。所以,诚如是书两条题记中所引的马克思(K.H. Marx,1818—1883)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他们不能表征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表征。”这句话对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可谓画龙点睛。 赛义德发现,法国人、英国人,再下来是德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瑞士人等等,都有一种他愿意叫做“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传统。美国人则有所不同,他们的东方观要现实得多。美国人言东方,更多的是指远东,主要是中国、日本,还包括韩国、印尼和中东,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居于首位。而在欧洲的“东方主义”传统里,东方不仅紧邻着欧洲大陆,也是欧洲最为广大富饶、最为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的来源,还是它文化上的对手,是它最深邃、最常见的“他者”形象之一。不仅如此,“东方”作为与欧洲或者说西方处处相反的意象、观念和人格经验,也帮助欧洲界定了自身。 东方的这一切,无疑是出自想象,但它也是“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鉴于此,东方主义不是别的,它是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上来表达和表征这个传统的话语模式。这个模式不是随性而来,其背后的支撑基础是制度、语汇、学术、想象、教义,甚至殖民官僚政治和殖民风格文体。赛义德坦言,他谈东方主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指义。第一个指义,它是一个学院派概念。即是说,大凡教学、写作、研究以东方为主题的,不论他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文献学家,它就是一个东方主义者或者说东方学家。虽然与东方研究、区域研究、国别研究这类学科相比,“东方主义”这个概念太含糊,而且带有早期殖民主义的强烈政治色彩,不过它终究还是坚持到了今天。这如该书的另一条题记所言,那是19世纪殖民主义高峰时期英国首相迪斯雷利(B. Disraeli,1804—1881)的一句话:“东方是一种职业生涯。”东方主义第二个指义也是它最普遍层面上的意义。对此,赛义德指出: 东方主义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的基础是“东方”和“西方”(大多数时候写作“Occident”)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区别。是以多不胜数的作家,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以及帝国管理人员,都接受了这个区别,由此出发来构筑有关东方、东方人,以及其习俗、“心灵”、命运等等的理论、史诗、小说、社会描述和政治纲领。 这一最普遍意义上的想象中的东方主义,赛义德指出,可以将诸如埃斯库罗斯(Αἰσχύλος,前525—前456)、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雨果(V. Hugo,1802—1885)和马克思这一类名字包括在内。它与前面的学院派指义,其实从来就是互通的。 东方主义的第三个指义是霸权。用赛义德本人的话说,这是比较前面两个指义更侧重历史和物质的释义。他认为,大体从18世纪后期起,东方主义便崭露头角,成为应对东方的特定机制。它发布关于东方的陈述,确立关于东方的权威观点,以及描述东方、教授东方、殖民东方、统治东方。总而言之,东方主义是主导、重构、掌控东方的一种西方文体。在这一方面,赛义德自谓福柯《知识考古学》《监禁与惩罚》这两本书中的话语观念,给了他很大启发。所以,他的看法是,假如不是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我们就无从理解东方主义这个庞大的系统性学科,无从理解欧洲文化如何能够在后启蒙时代,通过它在政治方面、社会学方面、军事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科学方面,以及想象方面,来应对甚至创造东方。不仅如此,“东方主义占据着这样高的权威地位,以至于我相信不论是谁来书写、思考东方,以及与东方交往,可以不顾及东方主义对他思想和行动的钳制”。 由是观之,东方主义就是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络,凡西方人言说东方,无一能够摆脱它的纠缠。这里的空间分界,显然远超过了单纯地理即物理空间的界限。故而赛义德强调,他谈东方主义的前提,就是东方并不是地理事实,并不是就在“那里”,就好像西方也并不是就在“这里”。他认为,维柯(G. Vico,1668—1744)所说的“人类创造自己历史,其知识空间就是他们造就的世界”这条至理名言,同样可以推广到地理学上来。它意味着,像“西方”“东方”这样的地理和文化的实体——更不用说它们还是历史的实体,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地方和区域。所以,就像西方自身一样,“东方”这个概念也有着自己的历史,有着自己的思想、意象和语汇传统。而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它成为真实的存在,并且与西方互相呼应。所以,东方、西方这两个地理实体是互相支撑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映照着对方。 为了说明“东方理论”的霸权性质,赛义德除了列举福柯外,还大量征引了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的相关论述。他指出,葛兰西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作过区分,前者是自愿构成的社会,或者至少是理性地、非强制性地联合了学校、家庭、工会这些社团;后者是国家机构,包括军队、警察、中央官僚集团,其政治角色是直接控制。这里就涉及了文化霸权的问题。秉承葛兰西的传统,赛义德这样重申了“霸权”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文化当然是见于市民社会内部的运作之中。在市民社会里,观念、制度和其他人物的影响,不是通过主导控制,而是通过葛兰西所言的赞同来实施的。因此,在任何一个非极权社会中,总有某种文化形式支配着其他文化形式,一如某种观念比较其他观念影响更大。这一文化的领导权形式,就是葛兰西予以命名的“霸权”(hegemony)。对于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生活的一切理解中,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赛义德指出,就是这个霸权,或者说施行文化霸权的结果,使得东方主义续命直至今天,而且照样是无比强大。它使欧洲成为“我们”,使一切非欧洲的地区成为“它们”。它意味着,欧洲人的身份比一切非欧洲的化外之民与文化都要高人一等。欧洲的东方观念亦然,它是“先进”与“落后”的鲜明对照。 关于东方主义的策略,赛义德强调说,它始终是建立在这一形态各异的优越性上面。以至于但凡西方人与东方人交往,无不占据上风。这在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直抵今天的欧洲上升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科学家,学者,传教士,商人,以及士兵等等,都在出没东方、思念东方,因为他们想去就去、爱想就想,东方本土对他们几无阻拦。故而: 在“东方知识”这个总标题下,顶着西方对东方的霸权保护伞,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个错综复杂的东方拔地而起,它相当适宜在学院中学习,在博物馆中展出,在殖民机关中重构,在事关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和历史主题中作理论阐发,在发展、革命、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性格的经济与社会性理论中来作例证。 赛义德这一大串叫人眼花缭乱的排比足以显示,东方主义在当代西方学术、文化乃至革命和宗教领域中的无所不在。不仅如此,赛义德指出,对于东方的这一切想象性考察,多多少少总是建立在至高无上的西方意识之上。这个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从未受到过挑战,东方世界就浮现在这一意识的核心部分。由于立足西方意识的西方人来考察谁是东方人、什么是东方,这些总体性概念的逻辑不仅来自经验世界,同样来自一系列欲望、压抑、投资、投射的组合。概言之,东方主义界定出的东方世界,其物理空间是无关紧要的;凭借“话语”“权力”“霸权”这些受惠于福柯和葛兰西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流行观念,让赛义德毫不犹豫地将东方主义打造成为了社会空间批判的一个样板。 二 从文学批评到东方主义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赛义德是如何走上东方主义这条独特研究道路,成为了日后如火如荼的东方主义第一推手的呢?这要从他的一个标题“纯粹与政治知识的区别”谈起。赛义德指出,人们都会说,关于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1564—1616)、华兹华斯(W. Wordsworth,1770—1850)的知识无关政治,反之关于当代中国和苏联的知识则是有关政治的。而他本人的正式职业属于人文学科,算起来与政治并不相干。这其实是笼统而言的。因为,一个人文学者写华兹华斯,一个编辑编济慈(J. Keats,1795—1821)的诗集,说他们无关政治,是说他们的工作对现实并不具有平常意义上的政治效果;但英国、法国以及近来的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事情但凡牵涉到帝国的海外利益,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就会给其市民社会施加一种紧迫感,这就是一种直接的政治压力了。这意味着,人文科学中的知识生产,永远不可能忽略或否认作者与自己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故而对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同样不可能否认他写作行为的政治环境: 他首先是作为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来谈论东方,其次才是作为个人。在这种境遇下,你是欧洲人或者美国人,并非无足轻重的一个事实。它过去意味着,现在也意味着,你会意识到,即便是模模糊糊,你也是属于一个在东方有着实实在在利益的大国;更重要的是,你属于地球上的这样一个区域,它有着一段几乎直溯荷马时代的卷入东方事务的明确历史。 赛义德作如是言说,是不想把帝国主义控制这种“昭然若揭”的事实,机械地用来作为文化与观念领域的决定性因素,他需要另辟蹊径。但是,即便另辟蹊径,从他书中述及的历史事实来看,也足以证明,欧洲和美国对东方的兴趣是政治性的。而产生这一政治兴趣的,是文化。正是文化与残暴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因狼狈为奸,使东方成为一个变来变去、扑朔迷离的地方。它的真实空间在哪里,已经无足轻重;它显而易见矗立在现在叫做东方主义的这个领域中,这就够了。 由是观之,东方主义不妨说是预演了一个真实与想象两相结合的“第三空间”。正如赛义德所言,它决不单单是一个政治题材或领域被动地反映在文化、学术、学院之中,也不是一个关于东方文本的大杂烩,不是在表征或表达某个穷凶极恶、旨在控制“东方”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恰恰相反,它是地理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哲学文本的一种分布。对此,赛义德强调说,它不仅是处心积虑将世界在地理上平分两半,一半东方,一半西方,而且通过学术发现、文献重构、心理分析,以及景观和社会学描述,精心策划并维护了一系列“利益”。所以,说到底,东方主义是与政治权力密切联系的一种话语,虽然这联系似乎并不是一目了然、直截了当的。既然东方主义是一个文化与帝国主义政治的事实,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于档案材料的真空里面,而是有着清晰的知识线索。诚然,让文化去搅和政治被认为有伤大雅,而且在赛义德看来,文学研究特别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没有认真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为解决这个帝国主义与文化或者说东方主义研究的困顿,赛义德从两个方面寻找答案。首先,差不多19世纪,以及在先时期的每一位作家,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帝国意识。比如,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专家很快就会承认,像约翰·穆勒(J. S. Mill,1806—1873)、马修·阿诺德(M. Arnold,1822—1888)、卡莱尔(T. Carlyle,1795—1881)、约翰·亨利·纽曼(J. H. Newman,1801-1890)、罗斯金(J. Ruskin,1819—1900)、乔治·艾略特(G. Eliot,1819—1880),甚至狄更斯(C. J. H. Dickens,1812—1870),这些彼时的自由派文化英雄,都对种族和帝国主义抱有明确立场。以穆勒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这两本书为例,公开表明,他书里的观点不适用于印度,因为印度不说在种族上,至少在文明上也低下一等。其次,更为重要的似乎是: 相信政治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影响了文学、学术、社会理论与历史撰写,并不意味着文化有失颜面,成了贬值的东西。恰恰相反,我的全部观点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像文化这样无所不知的霸权系统,其对作家和思想家的内在制约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抑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系统何以能够一以贯之,长盛不衰。 正是秉承这一理念,葛兰西、福柯、威廉斯(R. H. Williams,1921—1988)的著作虽然风格各异,却在殊途同归地展开阐述。即以威廉斯1962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谈论“帝国的作用”的那一两页篇幅而言,在向人们揭示19世纪文化的丰富性方面,已胜过许多整本整本的封闭式文本分析了。 赛义德因此宣称,他所研究的东方主义,是专注于个别作家与英、法、美这三大帝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他们的文字都是在这三个国家的学术和想象国土里生产出来的。而他本人作为一名学者,最感兴趣的不是总体的政治真相,而是细节。由此来看东方主义引出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类型:其一,哪些其他类别的知识、美学、学术与文化力量参与建构了东方主义这样的帝国主义传统?其二,文献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与经济理论、小说以及诗歌写作,如何服务于东方主义广义上的帝国主义世界观?其三,东方主义内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修正、升华甚至革命?其四,在这一语境中,原创性的意义是什么,延续性的意义是什么,个性的意义又是什么?其五,东方主义怎样从一个时代过渡或者说再生产到另一个时代?其六,如何将东方主义这个文化与历史现象看作是一个有意志的人类作品,而不仅仅是无条件的推理?面对这些问题,赛义德表明的态度是,任何一种人文主义探讨,必须能够阐明上述特定语境中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性质、相关主题,以及历史情境。《东方主义》面世之后,在一路风靡的同时,也招致不少反对意见。赛义德说,他写作此书并不是要将一个完整的世界分成“西方”“东方”两个部分。然而,反对意见之一,恰恰就是质疑赛义德用想象性话语,将全球空间割裂成了两个世界。例如,塔夫茨大学的莉莎·罗威(Lisa Lowe)教授在《批评地带》一书中,除了从女性主义角度质疑赛义德东方主义学说外,还明确反对以东方为西方他者镜像的立场。作者开篇就指出,《东方主义》这本书固然让她受益匪浅,但是,“我的研究最终是要挑战该书的这一假设,那就是《东方主义》一厢情愿、一股脑儿将东方建构成了西方的‘他者’”。她也“重读”了同样受到赛义德关注的一些英法作家,包括孟德斯鸠(C-L. d. Secondat,1689—1755)、福楼拜(G. Flaubert,1821—1880)、福斯特(E. M. Forster,1879—1970)等,同时引入新的视野,诸如后结构主义作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罗兰·巴特笔下的“中国乌托邦”等,以表明赛义德东方主义的批判范式其实是疑云密布的。 三 方法论问题 关于人文学科中的方法论,就是找出一个起点,一个启动原则。而赛义德研究东方主义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策略方位”(strategic location)。即如何来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地位,尤其是他与他所叙写的东方物质世界的关系。二是“策略形成”(strategic formation)。这是分析不同文本之间关系的一个方法,即探讨不同的文本系列和文本类别甚至类型,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而在整个文化之中脱颖而出,得以广为传布。这里同样涉及地理空间问题。固然,英国、法国早在17世纪末叶,就主导着地中海东岸地区。可是,假若东方主义研究只看到这一点,那就是忽略了其他国家的重要影响,诸如德国、意大利、俄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贡献。在这些国家里,赛义德特别关注的是德国。他指出,19世纪中叶,德国学术已达到很高水平,英法学者却视而不见,导致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中的卡索邦(Casaubon)先生没法完成他的《神话大全指要》,原因就是不擅长德国学术。而德国学术在盎格鲁—法兰西,还有后来美国人的心中,此时已毋庸置疑地代表着欧洲的领先水平。这是一切东方主义的研究所无法回避的。不仅如此,德国的“东方”几乎无一例外是学术的东方,至少是古典的东方。它是诗歌、传奇,甚至小说的题材,但它从来就不是真实的东方,与夏多布里昂、拉马丁(A. M. L. d. Lamartine,1790—1869)、奈瓦尔等人笔下的真实埃及和叙利亚判然不同。赛义德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认为它意味深长,那就是德国最有名的两部写东方的作品:歌德的抒情诗《西东合集》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 Schlegel,1772—1829)的《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前者的灵感来源于莱茵河上的一次旅行,后者是埋首巴黎的几家图书馆所得。所以,“德国东方学术所做的,便是用技能来美化和深化英法帝国主义从东方几乎是原初面貌收集过来的文本、神话、观念以及语言”。要言之,这里的方法分工,便是英法提供素材,德国再做深加工。至于“策略”,赛义德强调他使用这个术语作为方法论的核心,纯粹是为了挑明每一个写东方题材的人必然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握东方、接近东方,不为它的高深、宽广以及可怕的多重维度压倒而不知所措。这意味着,凡叙写东方,必须将自己定位在东方的坐标之中,将这坐标转译入他的文本。这一空间方位包括,他采用何种叙述声音,搭建何种结构,以及他作品中的意象、主题和母题类型。所有这一切汇聚起来,可组合成各种方法来对话读者、涵盖东方;最后,表征东方或为之代言。而这一切策略都不是抽象论道,任何一位叙写东方的作家,甚至荷马(Ὅμηρος,约前9世纪—前8世纪),都会认定某个东方先驱、某种在先的东方知识,他会提及它们,那也是它写作的基石。不仅如此,每一部论述东方的著作,都亲密联系着其他著作,联系着作者、机构,以及东方本身。这些作品、读者和东方某些特定方面的关系总体,便形成了一个可供分析的形式,如文献学研究、东方文学中的人类学研究、旅行札记、东方传奇等。这个形式在不同时间、不同话语、不同公共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外事部门等等中的反复出现,就使它有了一种权威意味。赛义德强调,上述东方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不在于文本内部的特征,而在于外在文本的特征,即东方主义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这不但适用于想象性文本如文学和艺术作品,同样适用于所谓的真实性文本如历史、语言学和政治著作。读者关注的是风格、修辞、场景、叙述技巧,以及社会和历史背景,而不是表述的正确性。因为,表达的外在性总是有点似是而非:倘若东方能够表述自身,它一定会表达自己;既然它无能为力,那么就必须由别人当此重任。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这又呼应了前面他引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东方“不能表征自己,只能被别人来表征”那句格言以为题记。赛义德指出,欧洲早在17与18世纪之交,就开始关注东方语言的悠久历史,它比《旧约》中的希伯来语系更为悠久。拜伦(G. G. Byron,1788—1824)、歌德、雨果们在其作品中用浪漫主义手法再造了东方,令东方和东方人大放异彩,这其实与真实的东方是大相径庭的。是以西方有语言学的东方、达尔文(C. R. Darwin,1809—1882)的东方、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的东方、斯宾格勒(O. A. G. Spengler,1880—1936)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东方,然而从来不存在一个纯而又纯的无条件的东方。同样,凡言东方主义,必有其物质形式,从来就不存在诸如东方的“观念”这样的天真东西。有鉴于此,赛义德坦言,就方法论而言,他不同于那些研究观念史的学者。他不仅考察学术著作,同样也考察文学作品、政治论文、新闻文本、旅行札记,以及宗教和文献研究。换言之,他的混血视角具有广泛的历史性与“文类学”性质,因为他相信,所有的文本都是世俗的,流转在不同的文类与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但在这一点上,赛义德表示,他与他的偶像福柯有所不同。对于福柯来说,大体相信个别文本和个别作家无关重要,但赛义德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福柯所言固然有理,却不适用于东方主义。故而对东方主义这个特定的领域,赛义德的分析采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其目的是揭示个别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之复杂综合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赛义德对他的《东方主义》方法论的最后说明是,写作此书,他心里面装着好几类观众: 对于文学与批评的学生来说,东方主义提供了一个奇妙的例子,显示出社会、历史和文本性之间的交互关系;不仅如此,我以为东方在西方扮演的文化角色,也对文学共同体呈现了东方主义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逻辑等相关问题的联系。对于东方专业的当代学者,从高校学者到决策者,我写此书有两个目的,一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他们的学术谱系呈现出来;二是批判他们的著作大多数时候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立论依据,希望由此引发讨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本研究应对的总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它们全都不但联系着西方关于“他者”的概念以及对“他者”的应对,而且事关西方文化在维柯所谓民族世界中扮演的独一无二重要角色。最后,对于所谓第三世界的读者而言,本研究不但是走向理解西方政治与这些政治中非西方世界的一个步骤,更是理解西方文化话语“力量”的一个步骤。 赛义德称,这个被置入引号之内的力量一语,过去多被人误解为“上层建筑”,但这里他明确阐明,它不是别的,就是令人生畏的文化主导结构。 赛义德上述以形形色色想象空间涵盖现实空间来归纳东方主义研究、以文化替代上层建筑来作为研究主导脉络的方法论,同样并非没有疑问。任教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印度裔比较文学教授阿赫迈德(Aijaz Ahmad),在他收入书评文集《理论之中:阶级、国家、文学》中的《东方主义及其后续》一文里,便是在相继而来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视野。阿赫迈德虽然与赛义德在许多政治观点上意见相同,而且支持赛义德在巴勒斯坦知识分子中的领军地位,但质疑《东方主义》联手福柯后结构主义和奥尔巴赫(E. Auerbach,1892—1957)等人的人文主义为理论基础,指出,“在用什么理论来理解世界,以及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上面,我与他有着根本性的分歧”。阿赫迈德的尖锐批评在东方主义后殖民研究中同样后续不断,赞成的、反对的各执其辞,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介入帝国主义空间文化批判的典范之说。 四 两部希腊悲剧 本着东方主义的批判视野,赛义德对西方文学进行了纵横捭阖的大量评述。他认同法国哲学家巴什拉(G. Bachelard,1884—1962)在1957年出版的《空间的诗学》中的一个著名观点:因为相关的经验和记忆,走进一栋房子,会有一种亲密、秘密和安全的感觉,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他引巴什拉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说: 房子里的客观空间——它的角落、走廊、地下室、房间,远远没有人们赋予它的诗意来得重要。那通常是一种特质,具有我们可以命名、可以感觉到的想象和比喻价值:如是,一栋房子可以是鬼屋,可以充满家庭温馨,可以像牢狱,也可以是奇境。所以,房舍通过一种诗意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的甚至理性的感觉。这样空洞的或无名的空间,这里就被我们转化成了意义。 不仅空间,赛义德认为时间也是如此。诸如“很久以前”“起初”“最后”,同样是可以具有诗情画意的。因为,想象地理学和历史,帮助我们的心智压缩了距离和差异,什么近在咫尺,什么远在天边,它会有自己的感受。同样的道理,比如我们的感觉对于16世纪和塔希提岛,就会更有一种“家园感”。 赛义德进而分析了现存最早和最晚的两部希腊悲剧,一部是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一部是欧里庇得斯(Ἐυριπίδης,前480—前406)的《酒神的女祭师们》。埃斯库罗斯参加过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他的兄弟就阵亡于马拉松。《波斯人》首演是在公元前472年,这部剧作以波斯王宫为背景,由报信人报告波斯舰队全军覆没萨拉米斯海战的消息。它虽然是以波斯人的视角叙述战争,但显而易见带有作者本人当年目睹的血战经历。所以,诚如《东方主义》的题记所言,它毋宁说是西方人代言东方的一个古代样本。赛义德指出,埃斯库罗斯描述了信使报知国王薛西斯一世率领的波斯大军魂归萨拉米斯之后,笼罩在波斯人头上的愁云惨雾。他引了歌队的一段歌词: 到如今整个亚洲大地 都在虚空中绝望悲泣。 薛西斯一往无前,噢噢! 薛西斯一败涂地,哇哇! 薛西斯的计谋悉尽流产 在大海的战舰之中。 可为何大流士 也曾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却未让他百姓遭祸殃 这位帝都苏萨人,敬爱的先王? 赛义德对此的评价是,这里的关键是,亚洲人通过欧洲人的想象在说话,而欧洲被描写为战胜亚洲的胜利方面,后者是大海彼岸敌对的“他者”世界。是以留给亚洲人的只有虚空、失败和大祸临头感,那就是他们挑战西方的回报。大流士一世战胜欧洲的辉煌岁月,毕竟是一去不返,只能回光返照在哀歌之中了。 《酒神的女祭师们》是现存欧里庇得斯悲剧作品的最后一部,写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带了一帮亚洲信众,回到忒拜(Thebes),要报当年的杀母之仇。当初狄俄尼索斯母亲塞默勒(Semele)是死在自己的亲姐妹手里,盖因她们出于妒忌,不承认她是宙斯的新娘。塞默勒跟宙斯怀下的孩子,凶手以为也是胎死腹中。这孩子就是狄俄尼索斯,他其实没死,而是长大成神,去了亚洲,向人类传播他的狄俄尼索斯新信仰。既抵忒拜,一国女人无不走火入魔,蜂拥而至旷野间欢歌狂舞,变身成为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师。这当中有一个女人,就是塞默勒的一个妹妹,忒拜当今年幼国王彭透斯(Pentheus)的母亲阿加芙(Agave)。彭透斯该是太为年轻,不解神一旦记恨意味着什么,一意驱逐疯疯癫癫的狄俄尼索斯宗教。狄俄尼索斯化身凡人传布新教,被彭透斯拘捕打入地牢后,发动地震摧毁忒拜宫殿。爬出废墟的彭透斯赌神发誓,要发兵与酒神的迷狂女祭师们开战,却又架不住好奇心,被依然是凡人身的酒神诳骗易装,加入女祭师队伍,一样如痴如醉迷狂起来。然后,狄俄尼索斯曝出彭透斯真实身份,被疯狂的女祭师们撕成碎片。第一个动手的,就是彭透斯的母亲阿加芙。此剧中有阿加芙手提彭透斯脑袋登场亮相的血腥场面,脑袋插在酒神手杖上面,她向父亲卡德摩斯夸耀徒手杀死了一头狮子。父亲让阿加芙看一眼手杖上是谁的首级,道明真相后,父女抱头痛哭,连女祭师们也为之动容。最后,狄俄尼索斯辉煌真身亮相宫殿上空,下令分头放逐阿加芙和卡德摩斯。父女哀悼死去的彭透斯,也哀悼彼此的命运。这个结局使人想起索福克勒斯(Σοφοκλῆς,前496—前405)的《俄狄浦斯王》中的结尾,一切真相大白后,俄狄浦斯刺瞎自己双眼,自我放逐荒野。可以想见,三个人一样是前路漫漫,凶险莫测。 赛义德认为,《酒神的女祭师们》是雅典地区所有悲剧中最具有亚洲特色的。狄俄尼索斯这个西方的酒神,显然与东方神话中无奇不有的恐怖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彭透斯这位年轻的忒拜国王,惨死在他母亲和那一群酒神女祭师手里,是因为他挑战狄俄尼索斯,否定他的权威,不承认他的神性,由此受到恐怖的惩罚,最终也如悲剧结尾所示,反衬出这位乖戾大神的恐怖法力。他并且指出,现代学者在赞美这部巨作非凡的知识谱系和审美效果之余,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欧里庇得斯显然感觉到了狄俄尼索斯信仰的一个新侧面——它肯定受惠于异域狂欢宗教,如本迪斯(Bendis)、塞伯莱 (Cybele)、阿多尼斯(Adonis)、伊西斯(Isis)信仰。这些信仰都是从小亚细亚和黎凡特地区(Levant)传入欧洲的。对此,他总结说: 上面两部剧作中,把东方与西方分别开来的两个方面,将持续成为欧洲想象地理学的基础母题。一条分界横亘在两块大陆之间——欧洲孔武有力、表达明晰,亚洲一败涂地、地处遥远。埃斯库罗斯“表征”亚洲,让年迈的波斯王后、薛西斯的母亲来代表她说话。那是欧洲在言说亚洲。这一言说的特权不属那个傀儡主人,而属真正创造者,他生死予夺的大权表征、激活并且构造了熟悉边界之外的那个否则将沉默无声、险象环生的空间。 这又是东方无言,非得西方代言的主题。赛义德认为,东方有别于西方见之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埃斯库罗斯的合唱队包含了一个剧作家构思出来的亚洲世界,它与东方主义学术的博学门面之间有一种类似关系,因为后者把握那个浩瀚无边、变幻无定的亚洲世界,虽然时有同情,却总是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由此过渡到第二个方面,即东方的主题暗示着凶险。赛义德对此的说明是,东方的恣意妄为损害了西方的理性,东方神神鬼鬼的各类花招,与西方的自以为是的价值规范背道而驰。是以东西方的差异,首先就体现在彭透斯对那帮歇斯底里酒神女祭师的严厉拒斥中。后来,当他自己变身为女祭师时,其死于非命与其说是屈服于狄俄尼索斯,不如说是一开头就错估了狄俄尼索斯的恐吓。所以,欧里庇得斯后来请出卡德摩斯和盲先知提瑞西阿斯(Τειρεσίας),让这两位见多识广的老人来提示教训:要统治民众,“君权”是独力难当的,还需要有判断。而判断意味着正确把握外来强权,以作专业应对。如此东方的神神鬼鬼疯狂行径就不可小觑,因为它们挑战了理性的西方心灵,让它旷日持久的野心和权力有了一个新的对手。 结 语 赛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西方强权文化殖民的近代史,就像他一以贯之的文学批评视角和立场一样,并非没有争议,但是它开辟了一个学派的奠基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学派的宣言,即是该书的“导论”部分。批评意见指责它突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将本质上属于政治和经济的殖民主义作文化至上的解释,以及人为地从文化上将完整的世界星球分为“西方”“东方”两个想象空间等等。这些反对意见,在多年以后的学术规范中,有幸也罢,不幸也罢,反而发展成了常识。 美国学者亚当斯(Hazard Adams)、塞尔(Leroy Searle)在他们主编的著名文选《柏拉图以降的批评理论》中,在赛义德名下全文收入了《东方主义》的“导论”部分。两位编者认为,在《东方主义》之前,还没有哪部著作像它那样构造出一个整合了哲学、人类学、文学、政治学的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批评和研究框架。而相关的早期著作,如法侬(F. O. Fanon,1925—1961)的《全世界的受苦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谈的要么是迫在眉睫的事关民族解放战争的实践问题,要么是底层民众的主导权问题。但是,赛义德不同: 赛义德的整合模式无论是在学院派内,还是在其他领域,都影响到一个利益同盟。不用说,他这本书也引来了批评和反对意见,因为正是这个把它树立为样板、让年轻学者和批评家来加效仿的同盟,提醒我们注意,学院研究与其他人众(这里叫做“东方主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深层同谋关系,以及职业知识分子对于剥削要么谴责、要么赞扬的政治态度。 所谓学院派与东方主义学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也是从文学批评推进到文化批评必然会遭遇的问题。由是观之,《东方主义》正是演绎了从文学向文化批评的扩展进路——以东方为背景,讨论了从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到雨果、夏多布里昂、乔治·艾略特等大量19世纪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殚精竭虑,将威廉斯、葛兰西、福柯等人的批判理论运用到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之中,从而造就政治文化与文学文本联姻的一个经典。而从空间批评的角度来看,与其耿耿于怀它是变相鼓吹的文化决定论,由此界出“西方”“东方”两个壁垒森严的空间,不如说是赛义德的这本大著对想象空间钟情太多,而多多少少忽略了跟它对应的真实空间,即意识形态批评背后的物质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华·索亚在他影响了空间批评一代学人的《第三空间》一书中,给予了赛义德高度评价。他认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演绎了一种“想象地理学”,代表了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打破学院里学科壁垒的努力。它显示,针对殖民主义文化控制的反抗和民族解放斗争,不仅是表达了一种时间序次,同样也是批判地再思考了地理政治的空间安排,即便它依然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遗风。所以: 赛义德解构形形色色的东方主义二元对立,其基础在于强行推广种种“想象地理学”。它们主导了传统的空间表征,也主导了物质的空间实践。在这些真实和想象的东方主义地理学中,中心的建构强大无比,井井有条,监测四方;反之,边缘则连连败阵,默默无言,位居附庸,只有服从,没有自己的历史。通过批判殖民主义的空间实践以及它对空间、知识和权力的令人生畏的表征,赛义德也打开了表征的后殖民主义空间和权力,而导向一种崭新的地理诗学修正。 按照索亚的说法,赛义德写作《东方主义》,是走边门进入了第三空间。什么是“第三空间”?它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既是想象的,又是真实的。这样来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想象地理学,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所悄悄开启的“空间转向”经典性方位,距离不过是一步之遥。至此,我们或者同样可以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是在历史性与空间性之间迄今迷雾密布的互动游戏中,走边门开辟了一个方兴未艾的空间批评新领域。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基金项目 此文是作者承担的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5ZDB084)的代表性成果。 信息来源 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1年第1期第39—50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如果您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的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后,可以下载所有文章PDF版。网址是:https://ias.um.edu.mo/2020-contents/
|
【本文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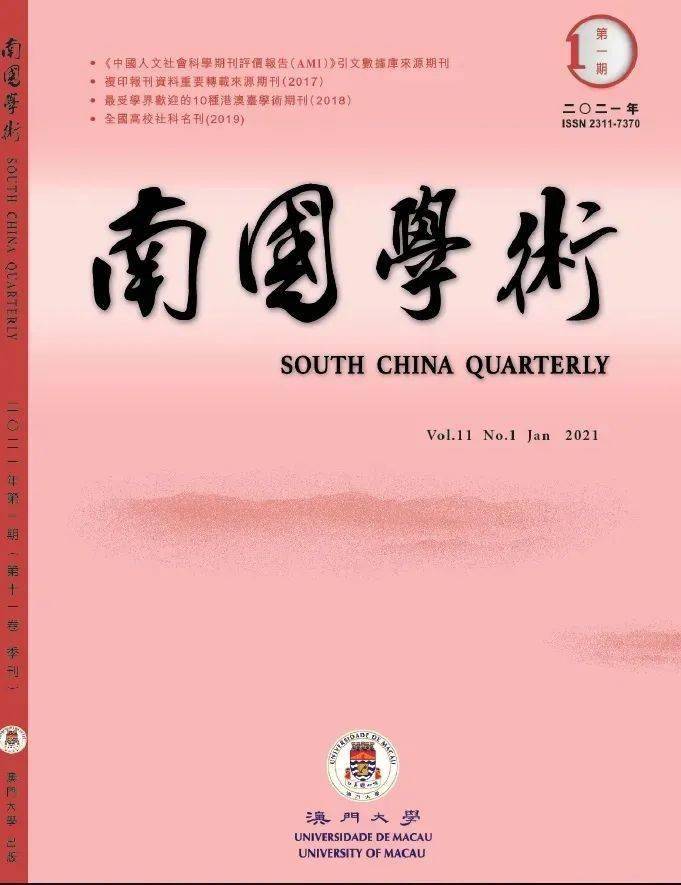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