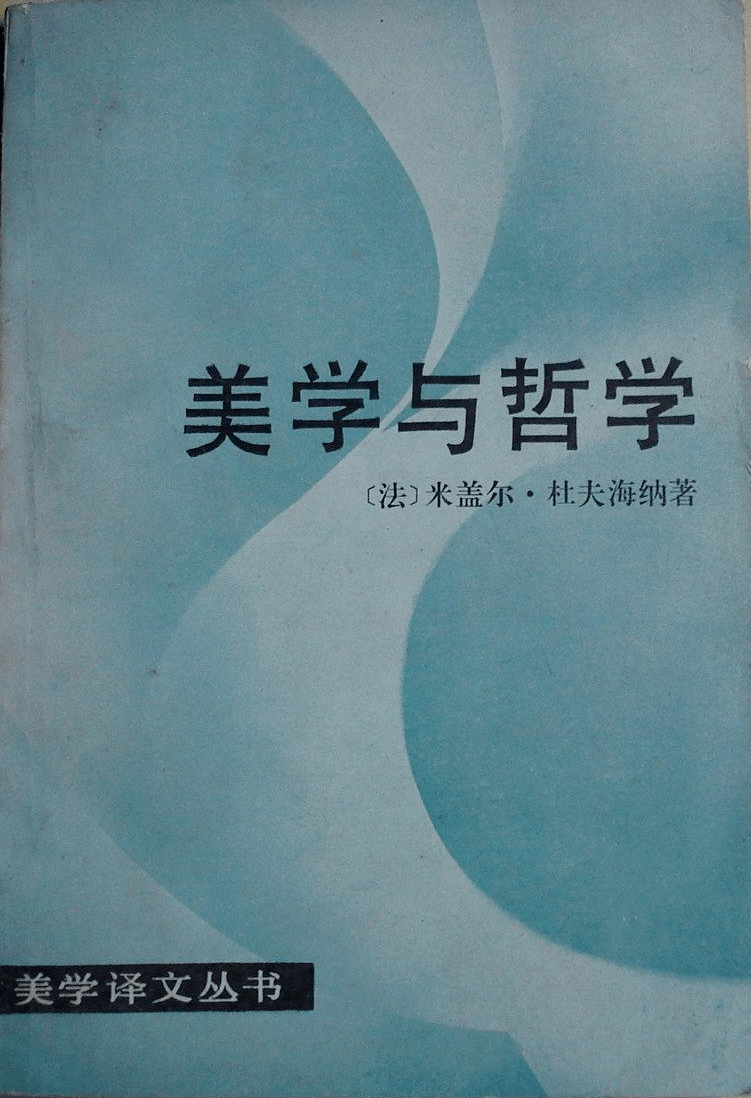| 张晶︱审美感兴与中国古代诗词的气氛之美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11选5计划手机app › 张晶︱审美感兴与中国古代诗词的气氛之美 |
张晶︱审美感兴与中国古代诗词的气氛之美
|
气氛的审美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并不会因为相关的审美范畴广为人知,就可以与之互换或被其遮蔽。气氛与意境,在很多情形下可以互通,但气氛以其浓郁的氛围和鲜明的情感指向而成为审美接受的最佳入口。典型者如《诗经·桃夭》所营造的非常热烈的喜庆婚嫁气氛,“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2],颇能说明气氛之美。《楚辞》中的《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3],给人以一种神秘的气氛感。宋玉《九辩》所营造的悲秋的气氛成为一种原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4]杜甫《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5],也是肃杀悲凉的气氛。李白《远别离》“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6],呈现给读者的是迷离惝恍的气氛;而其《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7],气氛又是何等轻快。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8],是伤感而缠绵的气氛。李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9],则是一番伤怀与凄凉的气氛。气氛之于诗词,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诗人或词人以自己独特的心绪营造出笼罩诗词整体意境的气氛,而读者之所以被诗词吸引,也由气氛而入。 首先,气氛之营造是诗人感物的结果,诗人的触物兴情即感兴,是营造气氛的最为关键的节点。气氛的烘染是整体性的,使人感觉在作品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气氛的营造离不开“气氛之物”,如以诗词为例,即是在诗词的意境中最能“点燃”气氛的物象。气氛是以某种情感为主导的,从而形成了具有强烈情感意向的氛围。而最能表征或呈现这种情感意向的某物,也就是气氛之物。一首诗、一阕词或一支散曲,就是以气氛之物作为点燃气氛的物象。作品的意蕴也许无法以语言解析,如严羽所说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10],而气氛之物却使读者既感到朦胧,又被导入某种浓郁的气氛之美中。波默这样谈论气氛之物:“当我们为了理解而把物理对象和技术上可操控的能量称为光并以明亮来称呼可察觉的气氛时,那么人们就可以说,两者之间显然还存在着某种东西,即某种气氛之物,某种虽然作为对象而且是可以探明的东西,但它也是,如果人们涉身其中的话,气氛上可觉察的东西。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有关朦胧(Dämmerung)的论题那里运用过这个区别。朦胧是某种蔓延扩展着的东西,其出现人们是可以确定的:朦胧是某种气氛之物。但它也是某种能环绕着人的东西,即某种气氛,一种人们可以察觉的、在自己的处境感受中参与着其现实性的气氛。”[11]本文所说的“气氛之物”,未必与此完全对应,而是指称中国诗词美学中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气氛之物在中国诗词的佳作中,是足以引发或点燃作品审美气氛的突出物象。这种物象也可能是一个最具高光点的物象,也可能是一组物象。前者如《诗经·桃夭》的“桃之夭夭”,就是诗人营造气氛最为鲜明的物象。而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则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12]一组物象作为气氛之物。气氛之物在气氛营造中的意义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气氛之物,也就不会有作品中独特的气氛的产生。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所举之例,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13]等等,本是用来讨论词语状物的功能,说的都是《诗经》中的名篇,而“桃花之鲜”“杨柳之貌”“日出之容”“雨雪之状”,都可以视为这些篇什中的气氛之物。担负气氛之物角色的,基本上是自然之物而非社会事物,因为能作场景、气氛之对象者,都是具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物象。刘勰讲的恰恰都是自然物象。 其次,气氛在作品中具有情感意向上的统一性。作品中的气氛之物可能有若干,从而形成意向的统一性,使作品的气氛愈益浓郁化。如果以现象学眼光看,气氛之物正是如胡塞尔所说的“客体化意向”[14]。呈现在诗歌中的物象,是诗人用语言描述并加以结构的。而通过诗人的情感的意向化,这些物象又指向一种统一的情愫,因而也就有了统一的义涵。从诗人的角度讲,成为作品气氛之物的物象,都有一个浓郁化的过程。以“秋”为例,波默有这样的论述,他说:“仍需追问的是,这种义涵类型是通过何种方式而有助于我们营造诗中的秋天气氛的?对此,需要再次注意的是,自然里的五彩缤纷的小路,晚秋的玫瑰和紫星菊并非像章(Insignien),而是其表征(Symptome)。只有在语言领域,它们才变成了像章。这些作为秋天标志的词语,其习俗化,不在于它们被刻板固定地使用,而是在于浓郁化过程(Verdichtungsprozeß),在于人们或许也会说的那种提喻法(Synekdoche)。秋天之所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那些义涵物的意义而变得浓郁。每一个义涵都以自己的方式而总是意味着同一个东西,即秋天。”[15]如果我们忽略那些无关我们论题的意思,“浓郁化”应该是营造气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与过程。诗人的某种情感在作品中不断凝聚,也通过气氛之物使之不断升华,从而生成具有强烈意向性特征的气氛。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16]山河破碎的气氛是通过“草木”“花”“鸟”“烽火”“家书”“白头”等气氛之物愈加浓郁化的。再如许浑《金陵怀古》:“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画楼空。梧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17]此诗在同类题材诗词中具有代表性,所写六朝亡国的衰败、凄凉气氛非常浓重,令人挥之不去,诗人正是以气氛之物的不断浓郁化来营造的。
《陆机集》书影,中华书局1982年版 再次,气氛之美是审美主体的处身性体验。气氛之物看似客观,都是诗人采撷进入作品的自然物象。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18]言其受自然物象的感染而产生情感波动,从而产生创作诗文的冲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通篇都是讲文学创作与自然物象的关系。中国古代美学以情景交融为基本模式,可见自然物象在作品中的突出地位。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些物象是如何进入作品的?它们仅仅是作家、诗人随意采撷入诗的吗?再则,这些自然物象难道仅是对自然界的反映或摹仿吗?当然不是。从气氛之美的意义上看,作品中的物象作为气氛之物,都是以主体的审美体验而获致的。任何自然物象都是诗人所感。这种主体的审美体验,并非仅是心灵的抽象感受,而是主体的身体处于其间,通过肉身的观照而产生的。正如陆机在《怀土赋序》中所说:“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19]词如李煜《相见欢》(一作《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20]这篇名作中的凄凉气氛可谓深矣。而词人“独上西楼”的处身角度,使人感同身受,正如俞平伯所评:“虽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凄凉的气氛,却融会全篇。如起笔‘无言独上西楼’一句,已摄尽凄惋的神情。”[21]波默认为,“处于情感波动中的人的身体——这种波动是通过身体上的反应体现出来的。因而,史密茨就能对感受做出如下界定:感受是‘没有定位地涌流进来的气氛[……],即以情感波动的[……]方式侵袭着其所植入的某个身体的气氛。这样,这种情感波动就抓住了被侵袭的[……]形体’”[22]。他由此指出:“气氛显然是通过人或物身体上的在场,也即通过空间来经验的。”[23]就文学作品而言,在那些以气氛之美感染我们的杰作中,气氛的营造与抒写是以主体的身体在场为标志的。即便主人公隐于其间并未直接出现,但实际上主体也是“在场”的。诗人王昌龄的这段论述颇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凡诗人,夜间床头,明置一盏灯,若睡来任睡,睡觉即起,兴发意生,精神清爽,了了明白。皆须身在意中。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有。若不书身心,何以为诗。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24]“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有”,是何等精警的诗歌美学命题!作诗必须以身体的在场作为基本条件,如果“不书身心”,是无法写出好诗的。这个“身心”,并非抽象之物,而是有着肉身性质在其中,气氛之美也以处身性为其基础。“身在意中”直接说明了诗歌意境生成的身体角度,同时,也道出了身体在场为气氛生成的必要条件。王昌龄在讲“诗有三境”时也明确提出“处身于境,视境于心”和“娱乐愁怨,皆张之于意而处于身”[25],这对我们理解诗歌意境和气氛极有启示意义。气氛的感受是以知觉作为根本途径的,这也是气氛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从现象学看,身体正是知觉的必要条件。正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正是某些以身体为其处所的现象构成为知觉的充分必要条件,身体成为从此以后彼此分开的实在世界与知觉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知觉不再是对某些事物的一种占有(即在这些事物本身所在之处找到它们);它应当是身体之中的一个内部事件,它产生自这些事物对身体的作用。”[26]对于诗歌而言,不管是气氛之物“闯入”诗人视域并被采撷入诗,还是读者感知气氛,身体的在场都是必要条件。
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书影,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二、感兴作为气氛之美的关键契机 诗词中的气氛之美,离不开气氛之物,而气氛之物进入作品、成为营造气氛的要素,并非刻意求取的结果,而是诗人的心情与外物相触遇,从而产生了创作冲动。它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诗人所能先期预见或者筹划。从中国美学的创作观念来说,此即“感兴”。感兴是感于物而兴,用宋人李仲蒙的话说,是“触物以起情谓之兴”[27]。感兴必以受到外物触发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感兴与感物同义;但是感兴的直接结果是兴发诗人的情感,这是一种从自然情感升华出来的审美情感。气氛是与诗人的审美情感直接相关的。与自然情感相比,审美情感带有明显的形式感和弥漫性,同时也更为稳定和长久。审美情感弥漫于作品所创造的空间之中,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丰满的感性”或“灿烂的感性”。正如波默所说的那样:“情感和想象之物都要被纳入丰满的感性中。感性的第一论题并非人们知觉到的物,而是人们感受到的东西:气氛。当我进入某个空间,我就以某种方式被这个空间所规定了。此空间所带有的气氛对我的处境感受(befinden)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只有当我处在气氛中,我才知觉和识别这个或那个对象。”[28]因此,由感兴而生成的审美情感,既是创作的内容,也是创作的动力。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可以说是从“赋比兴”之“兴”向感兴转化的关键,其篇末赞语所说的“诗人比兴,触物圆览”[29],其实是切中感兴的本质的。刘勰认为兴的根本功能在于起情,他的界定是:“兴者,起也。”又说:“起情故兴体以立。”[30]这就使兴有了确定的理论内涵,兴的作用就在于起发人意,主要是指主体之情。感兴的过程决非有意求取,而是偶然的触发,因而在感兴的相关论述中,都突出了偶然性。诗论中如《文镜秘府论》“十七势”之“感兴势”所说,“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31],指出了“人心至感”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人心与“万象”“爽然有如感会”,是邂逅相遇式的。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说:“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亦由或默或语,即铜鞮伯华之行也。”[32]这些论述谈的都是感兴的创作观念,也都蕴含着偶然的意味在内。这种偶然的属性,使作者的创作冲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言之“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33],联类不穷的物色来袭,从而在作品中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气氛之美。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书影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诗词作品中的气氛之美,既非定型化的,也非理性化的,而是如氤氲般无所不在,却又难以说解。波默这样描述:“对这种范围广阔的、在很多职业中已专业化的认知(即人们是如何制造气氛的)的提示,同时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认知将带来一种意义重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不是作为自然强力,也不是作为命令性的话语而发挥其作用的。它侵袭的是人的处境感受,作用于心情,掌控着情调,激发着情感。这样的一种力量并不登台亮相,而是在无意识中发挥其作用。尽管它在感性领域活动着,但与任何其他强力相比,它是更加不可见的、更难以把握的东西。”[34]这里所言的确是气氛的重要特征。 气氛之物进入诗人的神思之中,成为气氛之美的生发点。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之心受到外物的触发,而非有意求取,感兴成为基本的创作模式。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5]“志”并非像很多学者认为的是理性的观念,而是情感发动后那种一发而不可收的意向性运动。《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6]“之”是明显的动词,是朝着一个方向的运动,因此,可以将“志”理解为情感发动后的矢量运动。“情志一也”更说明了这种性质。气氛之美是整体性的而非单一的,当然也有非常突出的单个意象成为气氛之美的主要载体,但大多数情况则是由多个气氛之物形成总体的氛围。这些气氛之物,其实是由诗人所感而同向聚合,反过来又使诗人情感进一步浓郁化。 比、兴同为诗歌创作方法,不过也有差别。比主要是指直接的比喻,本体与喻体往往是一对一的,其义涵颇为明确;而兴则往往取譬引类,以若干意象形成一种气氛。《诗大序》孔颖达疏引郑司农之语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37]《文心雕龙·比兴》:“兴则环譬以记讽。”[38]都指出了这个特点。 感兴乃触物兴情,这种情形下映入主体视域的物象是非常充盈且鲜明的。《文心雕龙·比兴》篇末赞语所说的“触物圆览”,也包含了物象的充盈与高光度。《诠赋》又言:“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39]虽是讲赋的感兴而作,然其理也适用于诗词。“符采相胜”,是说以文辞描绘出明丽的画面。《诠赋》赞语又有“写物图貌,蔚似雕画”[40]之语,正是说作品在视觉上的鲜明呈现。笔者觉得,现象学的重要概念“表象的充盈”似乎可以说明气氛感知中这种丰富的感性。胡塞尔说:“作为理想的完备充盈是对象本身的充盈,它是构造它的那些规定性之总和。但表象的充盈则是从属于它本身的那些规定性之总和,借助这些规定性,它将它的对象以类比的方式当下化,或者将它作为自身被给予的来把握。因而这种充盈是各个表象所具有的与质性和质料相并列的一个特征因素;当然,它在直观表象那里是一个实证的组成部分,而在符号表象那里则是一个缺失。表象越是‘清楚’,它的‘活力’越强,它所达到的图像性阶段越高,这个表象的充盈也就越丰富。”[41]这是胡塞尔在论述直观意向的充实统一时所言及的表象的特征,对我们理解气氛之物很有帮助。杜夫海纳称审美对象为“灿烂的感性”[42],也是说通过审美感兴呈现在主体眼中的物象是鲜明而有内视感的。彭锋曾对气氛有较为清晰的论述,他说:“与‘灵光’专用于视觉艺术不同,‘气氛’可以用于人、空间和自然。比如,我们可以说某个春天的早晨气氛清爽,也可以说某个花园有家的气氛。在这些用法中,气氛指某种不确定的、弥漫的却与对象紧密相关的东西。”又指出,“‘意境’与‘气氛’的关系,第一体现在它们的不确定性上”;“第二,描述‘意境’的词汇与描绘‘气氛’的词汇基本可以互换,但是用它们来描述‘象’‘意象’和‘显现’有时候就显得有点别扭”;“第三,‘意境’和‘气氛’的情感特征更加明显”;“第四,‘意境’和‘气氛’都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43]。笔者对这些观点有赞成也有不同看法。“不确定性”的确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意境更多的是内在的可视性,而气氛则更指向处身的弥漫性。关于彭锋提出的第三点,笔者认为,在情感性特征方面,气氛是远远超过了意境的;气氛越是浓郁化,也就意味着情感越是强烈,客体的气氛正与主体的情感不期而遇。
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书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气氛之美与其感兴的方式密不可分,感兴以触、遇为情感发生方式。正如苏洵《仲兄字文甫说》所说:“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44]“触”首先是视觉上的冲击,物象映入诗人的眼帘,使人产生情感波动。感物之感,首在目击。沈周《书画汇考》说:“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45]所言是山水画,其实也是诗学感兴的普遍规律,触物即触目,外在物象与诗人目光不期然而遇,并由此产生情感波动而进入创作状态。吴雷发《说诗菅蒯》云:“大块中景物何限,会心之际,偶尔触目成吟,自有灵机异趣。”[46]触物就是外物以其鲜明充盈的物象“闯入”诗人的视觉。刘勰以“物色”作为客体的审美范畴,是很有道理且很有创造性的。物色并非事物的内在属性,而是其外在形貌。借用佛学术语,便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47],色就是现象界。《文心雕龙·物色》赞语“目既往还,心亦吐纳”[48],既揭示了物色的视觉性质,又指出了心灵的主体功能,二者是往还吐纳的关系。感兴触物兴情,通过引譬连类,也就是所谓“成套的”物象,在诗人的情感兴发上,当其流连万象之际生发出强烈的气氛。郑毓瑜说:“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感物’与‘连类’,既称感,则感物当属心的活动(‘沉吟视听之区’),但这活动的作用又是在‘连类’——联系相关物类(‘流连万象之际’),换言之,‘感物’引发‘连类’,而连类就是感物的内容与体现。而‘人’在这个类推体系中是唯一能‘感知’同时又‘应显’的枢纽;人身能够接收来自天地万物的信息(包括阴阳惨舒、四时动物、日影短长),同时又将这信息反映给原本发出信息的世界(寒暖、舒躁、凄迟)。”[49]作品中的气氛之美也由此而生。
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书影,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并非任何物象都可以进入作品之中,进入作品并成为气氛之物,需要与诗人的情感相契合。《文镜秘府论》“感兴势”所说的“人心至感”,可谓前提。梁肃《周公瑾墓下诗序》说:“诗人之作,感于物(一作感于物象),动于中,发于咏歌,形于事业。”[50]诗人的主体情感与外在物象是互感互动的。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赞语所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51],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诗人之情并非仅是被动受感的,而往往是一种主动投射;在与物色的触遇中获得的“兴”,是对诗人最好的回馈。 对气氛的生成与营造而言,感兴所触之物,正是主体的知觉与外物相接的触点。这也是相关于气氛的知觉如何生成的关键。诗人以处身其间的知觉把握外在事物,必有一个相接之点,这正是触物的实质所在。“目既往还”与“心亦吐纳”之间,是要有一个触点来作为媒介的。纪昀《清艳堂诗序》谈到这种“相遭”的情形时说:“凡物色之感于外,与喜怒哀乐之动于中者,两相薄而发为歌咏,如风水相遭,自然成文;如泉石相舂,自然成响。”[52]这也是说触物。触物所接者,必为充盈的物象,而其进入作品之后,也必多为作品中的气氛之物。这个过程并非理性思考,更非逻辑推演,而是感性的升华。在作品中所呈现的物象,虽然是触物所及,却已是作品的有机成分,其所负载的情感,已是审美情感,它基本上是以气氛之美烘托出来的。从自然情感到审美情感的生成转换过程中,气氛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正是气氛使接受者进入一种浓郁的审美感受之中,如果缺少了气氛,作品的审美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三、通感与诗词的气氛之美 在诗词气氛之美的生成过程中,通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感以不同感觉的互相打通,使作品呈现出付诸审美知觉的丰富性与陌生化,在营造气氛方面厥功至伟。愈是打破了个别感觉而形成了更多感觉因素在内的新的审美知觉,愈是使读者感受到浑然一体的气氛之美。波默即以很大的篇幅谈通感:“在《论灵魂》(Über die Seele)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人们是如何能把诸如甜与明亮相互区分开来的,并且——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相应地断定甜与明亮之间的一个亲缘关系?亚里士多德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暴力’手段,即他宣称,所有的感官像线条一样聚集在一个点上,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一个统一体。后来人们从中得出了共同感理论,即得出了一种超越五种感官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个别感官领域汇聚其中的一种更高级别的感官。”[53]这里所说的“更高级别的感官”,就是通感。他主张,第一性的、根本的知觉现象,即气氛,基本上不具有个别感官的特征,而是一种处境感受,也即通感。钱锺书《通感》一文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54]这也就是通感。通感在中西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呈现。钱锺书举了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一些经典个案,如针对宋祁《玉楼春》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说:“‘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55]此乃典型的通感,是视觉与听觉的融合。他还举了白居易《琵琶行》和《礼记·乐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以及李商隐的一些诗句,并细致分析说:“白居易《琵琶行》有传诵的一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它比较单纯,不如《乐记》那样描写的曲折。白居易只是把各种事物发出的声息——雨声、私语声、珠落玉盘声、鸟声、泉声——来比方‘嘈嘈’‘切切’的琵琶声,并非说琵琶大、小弦声‘令人心想’这种和那种事物的‘形状’。一句话,他只是把听觉联系听觉,并未把听觉沟通视觉。《乐记》的‘歌者端如贯珠’,等于李商隐《拟意》的‘珠串咽歌喉’,是说歌声仿佛具有珠子的形状,又圆满又光润,构成了视觉兼触觉里的印象。”[56]钱锺书的分析颇为细致,是关于通感的经典论述。笔者由此进一步生发,认为诗人将日常经验中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现象,在作品中合成为一种新的超越于个别感官经验的审美知觉方式,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知觉,并非个别感觉的混合。诗人从自然情感升华到审美情感,这是一条尤为重要的途径。
钱锺书《七缀集》书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无论是视觉与听觉的联姻,抑或是视觉与触觉的混融,诸多感觉的融合打通在诗词创作中都是高难度的挑战。诗人的审美知觉与世界相接,创造出既有陌生化效果又奇妙难言的审美感知,这种奇妙难言,却是被气氛所笼罩。诗词的气氛之美,恰是无法拆解、难以言喻的。这又是“气氛”作为美学概念的不可取代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气氛却真的是与“韵外之致”或意境难分彼此。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57],以之说明气氛之美,似也颇为贴切。但本文之所以建构气氛之美,当然是要揭示气氛的独特之处。在笔者看来,气氛具有类似于意境的特征,但它的情感指向尤为鲜明,对于审美感知的导引愈加强烈。通感在气氛营造方面的作用,也许是最为突出的。 “红杏枝头春意闹”,仅仅就是视觉和听觉的联合吗?如果如此解析,那么就把美妙无比的气氛加以简单理解或者割裂了。“春意闹”并非仅止于视觉与听觉的联合,而是将各种感觉混搭,以形成一种全新的气氛。在审美知觉中,视觉与听觉是主要元素,而当通感形成之后,就不仅是视觉与听觉的相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新的知觉了。这种知觉呈现出以往的“图式”所没有的新质,拓展了主体的审美经验。通感给人的审美知觉,超乎一般的知觉之上,具有强烈的张力,极大拓展知觉的维度,使作品散发出更为浓郁的气氛之美。 杨恩寰说:“审美知觉作为一种审美能力,是多种感觉力的综合,作为审美知觉活动,是多种感觉的综合活动。其中,视觉和听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视觉和听觉社会化、理性化程度高,活动范围广,易于同感性欲求分离,并把理性因素带进知觉中来。……很显然,构成审美知觉的主要是视觉和听觉,却又缺少不了其他感觉……审美知觉乃是各种感觉协同活动,在这种长期的协同活动中,各种感觉之间经常出现暂时联系,以至形成彼此沟通、转移、互渗现象,从而丰富了审美知觉的功能。心理学把这种沟通、转移、互渗现象叫做‘联觉’。”[58]这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联觉”也即通感的心理机制,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视觉与听觉的连接或融通,是通感的常态,但其含义并非仅仅如此。杨恩寰的意思是,在这种通感产生的审美知觉中,除了视觉和听觉之外,还有其他若干感觉类型参与进来。这个过程当然并非通过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是以感性的形式进行着的。李元洛说:“妙用通感,可以使形象鲜明生动,迁想而妙得,让读者油然而生新颖奇特的美的感受,同时,由于形象对审美主体产生多种感官刺激,因而能够激发人们丰富的审美联想与情感,这是通感所具有的特殊美学效果。”[59]他还结合中国古代诗词,举例分析了通感的主要类型,如听觉与视觉的通感、视觉听觉与触觉的通感等。笔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谈论气氛与通感的关系,不能全然停留在心理学层面,而是要从诗词的语言魅力上加以理解。诗人以通感的手法创造出诗句,使作品中的气氛之物尤为鲜明精警,这就是古人时常称道的“秀句”。
杨恩寰《审美心理学》书影,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诗词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当然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媒介的,诗人通过语言文字创造出具有内在视觉效果的形象。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语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60]诗要用语言来创造意象,正如《文心雕龙·神思》所谓“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61]。这里的“意象”,正是中国美学中最常见的核心范畴“意象”之本义,是具有内在视觉性质的。但意象不止于视觉,而是可以融视觉、听觉与触觉等为一体的。以视觉为主的意象可以兼有听觉,而以听觉为主的意象也可兼有视觉。“大珠小珠落玉盘”,虽有听觉效果,难道没有视觉的美好?陆机《拟西北有高楼》“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62],将视觉、听觉和嗅觉融为一体。在通感的创造方面,语言文字的媒介功能被发挥到极致;反过来说,语言文字作为媒介,也使通感变成了可贵的现实。语言文字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它可以创造画面,也可以形容声音;它可以表达触觉,也可以表现嗅觉。当它们在作品中融合成无比新鲜的意象时,就会使作品中的气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形态,使人们的审美知觉得到令人惊奇的拓展。鲍桑葵说:“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也有一个物质的或者至少一个感觉的媒介,而这个媒介就是声音。可是这是有意义的声音,它把通过一个直接图案的形式表现的那些因素,和通过语言的意义来再现的那些因素,在它里面密切不可分地联合起来,完全就像雕刻和绘画同时并在同一想象境界里处理形式图案和有意义形状一样。”[63]鲍桑葵论述了诗中语言的媒介性质,并且告诉我们在诗中可以描述出“直接图案”的效果,也就是内在的视觉效果,但其实语言的功能不止于此,它还可以表现听觉的、嗅觉的、触觉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将这些感觉元素混搭为一个全新的意象,从而产生迷人的气氛。
鲍山葵 (鲍桑葵)《美学三讲》书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诗人运用通感使诗歌语言获得了极大的张力,使诗的美感并非止于单一的感觉,而是创造出声、色、味等融而为一的浓郁气氛。钱锺书针对王维《过青溪水作》“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以及杜牧《阿房宫赋》“歌台暖响”这些典型地运用了通感的诗文说:“把听觉上的‘静’字来描写深净的水色,温度感觉上的‘寒’‘暖’字来描写清远的磬声和喧繁的乐声,也和通常语言接近,‘暖响’不过是‘热闹’的文言。诗人对事物往往突破了一般经验的感受,有深细的体会,因此推敲出新奇的词句。”[64]叶燮《原诗》就杜甫的“晨钟云外湿”一句做过深刻分析:“又《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晨钟云外湿’句,以晨钟为物而湿乎?云外之物,何啻以万万计?且钟必于寺观,即寺观中,钟之外,物亦无算,何独湿钟乎?然为此语者,因闻钟声有触而云然也。声无形,安能湿,钟声入耳而有闻,闻在耳,止能辨其声,安能辨其湿?曰云外,是又以目始见云,不见钟,故云云外。然此诗为雨湿而作,有云然后有雨,钟为雨湿,则钟在云内,不应云外也。斯语也,吾不知其为耳闻耶?为目见耶?为意揣耶?俗儒于此,必曰‘晨钟云外度’,又必曰‘晨钟云外发’,决无下‘湿’字者。不知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65]“晨钟云外湿”当然是典型的通感:钟声是听觉意象,而“湿”是触觉,另外还有视觉等的加入。但如果我们都这样解诗,也未免胶柱鼓瑟了。以通感为诗的诗人,只是调动各种审美的敏感,而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境界与气氛。我们可以如此这般分析,但一定要分出何为视觉、何为听觉,恐怕要被叶燮骂为“俗儒”了。 中国诗学讲求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审美价值观念,与这种由通感方法营造的气氛有直接关系。诗人以不同感觉之间的挪移、互渗而形成的全新意象或境界,是以逻辑思维的理路难以说清的。钱锺书曾分析过逻辑思维与通感的分野:“按逻辑思维,五官各有所司,不兼差也不越职,像《荀子·君道篇》所谓:‘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公孙龙子·坚白论》说得更具体:‘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目不能坚,手不能白。’一句话,触觉和视觉是河水不犯井水的。陆机《演连珠》第三七则明明宣称:‘臣闻目无尝音之察,耳无照景之神。’《文选》卷五五刘峻注:‘施之异务。’然而他自己却写‘哀响馥若兰’,又俨然表示:‘鼻有尝音之察,耳有嗅息之神。’‘异务’可成‘借官’,同时也表示一个人作诗和说理不妨自相矛盾,‘诗词中有理外之理’。声音不但会有气味——‘哀响馥’‘鸟声香’,而且会有颜色、光亮——‘红声’‘笑语绿’‘鸡声白’‘鸟话红’‘声皆绿’‘鼓[声]暗’。香不但能‘闹’,而且能‘劲’。流云‘学声’,绿阴‘生静’。花色和竹声都可以有温度:‘热’‘欲燃’‘焦’。鸟语有时快利如‘剪’,有时圆润如‘丸’。五官感觉真算得有无相通、彼此相生了。”[66]钱锺书所举这些通感的诗句,如果以“理”解之,则是“不可理喻”的,而在诗学中,“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却是一种绝妙之境。王夫之《古诗评选》认为“经生之理,不关诗理”[67],“诗理”是不同于普通的理性思维的。叶燮认为,通感的经典案例是臻于诗中“至理”的,他说:“然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之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68]通感对于气氛的营造来说,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正因其不可言、无以解,生成了非常浓郁的情感气氛,给人的感受也就是多维度的,这足见通感营造气氛的强大力量。 气氛之美是我们欣赏中国古代诗词的独特角度,通过这个角度,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全息性地感受诗词佳作的魅力。21世纪以来的气氛美学研究,其观点和理论元素给我们以启示,让中国诗学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观照角度。虽然它并非专门考察诗歌,而是生态美学中的一维,但气氛之美确乎又是诗词中的普遍存在。感兴对诗词创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触物起情是气氛营造的契机。本文力求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所言不切者可能不少,只是想以此打开欣赏中国古代诗词之美的另一个窗口而已。 注释 [1][11][15][22][23][28][34][53]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第124页,第66—67页,第18页,第19页,第3—4页,第27页,第79页。 [2][36][37]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第7页,第14页。 [3][4] 洪兴祖撰,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第293页。 [5][16]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3页,第1521页。 [6][7]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57页,第1022页。 [8] 周建国选注:《李商隐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9][20]李璟、李煜著,王仲闻校订,陈书良、刘娟笺注:《南唐二主词笺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8页,第160页。 [10]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2]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71页。 [13][29][30][33][35][38][39][40][48][51][6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第603页,第601页,第493—494页,第65页,第601页,第136页,第136页,第695页,第695页,第493页。 [14][41]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39页,第1069页。 [17]许浑著,罗时进笺证:《丁卯集笺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5页。 [18][19][62]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第16页,第60页。 [21]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24][25]王昌龄:《诗格》,张伯伟编校:《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第172页。 [26]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80页。 [27]胡寅:《与李叔易书》,容肇祖点校:《崇正辩·斐然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6页。 [31]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页。 [32]张怀瓘:《书断》,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42]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43]彭锋:《意境与气氛——关于艺术本体论的跨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44]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中国古典美学丛编》,第296页。 [45]沈周:《书画汇考》,俞剑华编:《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页。 [46]吴雷发:《说诗菅蒯》,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35页。 [47]陈秋平译注:《金刚经·心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7页。 [49]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页。 [50]梁肃:《周公瑾墓下诗序》,《中国古典美学丛编》,第270页。 [52]纪昀:《清艳堂诗序》,《中国古典美学丛编》,第286—287页。 [54][55][56][64][66]钱锺书:《通感》,《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4页,第63页,第66页,第68—69页,第70—71页。 [57]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司空图著,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7页。 [58]杨恩寰:《审美心理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59]李元洛:《诗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405页。 [60]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63]鲍山葵(鲍桑葵):《美学三讲》,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65][68]叶燮:《原诗》,《清诗话》,第600页,第599页。 [67]王夫之著,李中华、李利民点校:《古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猜你喜欢 宋长建︱女子之喻与中国古典诗学批评 吴光兴︱文集“首赋”体制之建构——以两汉之际学术演变为背景 孟琢︱文学与小学之间:黄侃手批《文心雕龙札记》发微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中外 文学艺术史论、批评。 欢迎相关学科研究者, 特别是青年学者投稿。 文艺研究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购买往期杂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