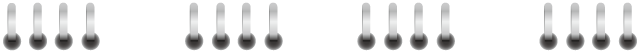| 【学术撷英】陈戎女|荷马的英雄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阿司喜欢谁 › 【学术撷英】陈戎女|荷马的英雄 |
【学术撷英】陈戎女|荷马的英雄
|
格劳科斯啊,为什么吕底亚人那样用荣誉席位、头等肉肴和满斟的美酒敬重我们?为什么人们视我们如神明?我们在克珊托斯河畔还拥有那么大片的密布的果园、盛产小麦的肥沃土地。我们现在理应站在吕底亚人的最前列,坚定地投身于激烈的战斗毫不畏惧,好让披甲的吕底亚人这样评论我们:‘虽然我们的首领享用肥腴的羊肉,咂饮上乘甜酒,但他们不无荣耀地统治着吕底亚国家:他们作战勇敢,战斗时冲杀在吕底亚人的最前列。朋友啊,倘若我们躲过了这场战斗,便可长生不死,还可永葆青春,那我自己也不会置身前列厮杀,也不会派你投入能给人荣誉的战争;但现在死亡的巨大力量无处不在,谁也躲不开它,那就让我们上前吧,是我们给别人荣誉,或别人把它给我们。(《伊》12.310ff) 大部分前来作战的英雄都是各地的王者(basileus),像萨尔佩冬一样,他们并不匮缺土地牛羊,他们并非为财富而战,而是为荣誉。但赢得名誉必须冒牺牲他自己甚至家庭的危险。要成为英雄,就无法获得其他的安慰。赫克托尔(Hector)明知战争后家国无存,自己的躯体将受敌人侮辱,仍决心在战场上赢得尊荣,因为他看重别人如何看他,而非他个人利益如何。古希腊人看重的是独特人性的光耀,而非普通的人类尊严。(我们现代人已经不认可这种道德观。) 为了这种单纯的荣耀,英雄必须面对死亡。死生的选择使英雄的命运带有悲剧意味,荷马的英雄以最突出的方式显示了生命的悖谬:最宝贵的生命常常就是处于危急之中的生命本身。英雄证明了他的勇气,赢得了他的荣耀,却可能建立在死亡之上,对于他的亲人,这就是苦难(基托1998.73)。荷马史诗因而迷漫着宿命论的悲剧气氛(这种气氛如一股红线延续到古典时期的悲剧)。荷马没有把阿基琉斯写成杀死赫克托尔的胜利者,却一再强调他会早死的命运,这带有强烈的悲剧性,又带有希腊特有的超越性——明知要死亡或失败仍要放手一搏。不过死要死得其所,用阿基琉斯的话说是“高贵之士杀人,杀死高贵之人。(《伊》21.280)”荷马史诗里没有默默无闻的将领,叱咤战场的都是有名有姓的英雄,没有无名小卒。 以上是对荷马史诗英雄主义的概述。具体观之,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勾勒了多位英雄的形象,但其英雄主角的生命经历和追求却大相径庭:《伊利亚特》围绕阿基琉斯的忿怒(mēnis)铺陈故事,尊崇“力量”(bíē)和荣耀;《奥德赛》则描写奥德修斯(Odysseus)如何凭借智谋(mētis)忍辱屈尊,归乡后重整秩序。 一、阿基琉斯——“英雄世界里最成功最易逝的花” 1、阿基琉斯的忿怒与脆弱 阿基琉斯是“阿开奥斯人中最英勇的人(best of the Achaeans)”(《伊》1.243)。他的生命经验和追求最能体现《伊利亚特》的英雄主义主旨:追求荣耀和名声。《伊利亚特》一开篇是“阿基琉斯的忿怒”。如何看阿基琉斯的忿怒?从史诗结构看,阿基琉斯的忿怒不仅是《伊利亚特》的“引子”(正是从这一怒铺陈了下面的故事),而且其忿怒的内在戏剧变化决定了史诗外在情节的演进。从人物看,英雄(特别是王者)的忿怒不是私人的情绪表露,而是对事件不公的反应,一般来说要求得到补偿,所以忿怒在荷马的英雄世界里并不罕见。但阿基琉斯的忿怒非常人之怒,mēnis一词专指“神明的忿怒”。“神明的忿怒”通常针对凡人的冒犯之举,当人忘乎所以,忘记自己的分寸,会遭到神谴。用mēnis指“阿基琉斯的忿怒”,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是女神的儿子,有半神的身份,而是因为“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álgea,《伊》1.2-3)”。[3] 阿基琉斯忿怒的起因是为了一个女人,但他和阿伽门农争夺的绝不仅是女人或床伴,而是属于各人的份额和战利品,这是众人承认的战场荣誉(诗中多次提到克律塞伊斯[Chryseis]和布里塞伊斯[Briseis]是“荣誉礼物”[4],《伊》1.139, 164, 185, 356, 507)。阿基琉斯本来就和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得到的荣誉礼物不相等”,现在又被阿伽门农蛮不讲理夺走战礼,他的尊严被冒犯,因而产生“致命的”忿怒。“阿基琉斯的忿怒”使希腊联军两位首领的矛盾激化:阿伽门农的王权和地位受到年轻一代的挑衅,阿基琉斯的荣誉被当权者蛮横侮辱。对这件事的原因的解释,阿基琉斯后来归结成宙斯的意图,是宙斯“让凡人深深陷入迷误”(《伊》19.270-71),回应了《伊利亚特》一开篇所说的阿基琉斯致命的忿怒“实现了宙斯的意愿”(《伊》1.7)。总体来看,“阿基琉斯的忿怒”的产生、发展、突变和最后的消解编织出了《伊利亚特》史诗的经纬。[5] 剑拔弩张的军队议事大会解散后,阿伽门农向阿波罗献上了百牲大祭,然后派人从阿基琉斯营帐里带走了布里塞伊斯。紧接着的一幕海边哭诉,出现的是一个孩童般脆弱、依赖母亲解决困境的阿基琉斯。如果说阿基琉斯相信自己的勇力和判断,“总有一天需要我来为其他的战士阻挡那种可怕的毁灭”(《伊》1.341-42),他就应该知道阿伽门农迟早会为自己的莽撞后悔,重礼请他重返战场,这样来看,他不必求母亲插手此事。但荷马并不惮于让他笔下的英雄表现出脆弱的一面,阿基琉斯向母亲流泪哭诉,像受了委屈的孩童一般,荷马没有顾忌这样会有损英雄的伟岸形象,相反却让英雄的天性显得更加真实。文本的叙事也支持了阿基琉斯的做法,正因为女神忒提斯哀求宙斯,宙斯允诺她的愿望会成为事实,“暂且给特洛亚人以力量,使阿开奥斯人尊重我的儿子[阿基琉斯],给予他应得的赔偿”(《伊》1.509-10)。之后,希腊人因忒提斯“充满灾难的祈求”节节败退,阿基琉斯才显现出不可或缺性。由此来看,海边哭诉一幕并非多此一举,阿基琉斯也由此呈现出“英武而脆弱”的形象。按现代的性格分析法,阿基琉斯这样类型的英雄实在有性格缺陷,他自恃勇力过人,让自己几近陷于某种迷执和疯狂(Clarke 2004.81)。但奇妙的是,英雄的光芒并不因这样的性格缺陷而黯淡。换句话说,恰恰因为他是女神之子,并非凡胎,他不必性格完美。他的脆弱,正如他的“脚踵”一样,成就了他的命运。 2、阿基琉斯的选择和命运 我们早就从阿基琉斯的母亲忒提斯那里知道了他“命运短促,活不了很多岁月,你注定要早死,受苦受难超过众凡人”(《伊》1.416-17)。在第一卷,荷马就用“预示手法”告诉我们阿基琉斯可能早死,此后史诗的结构一直笼罩在这个预言的框架下。接着荷马把这位主角放在一边,八卷以后,第九卷他才重新现身。此间的战斗,其他各路希腊英雄纷纷出马,不敌特洛亚人,此时希腊人才明白了涅斯托尔(Nestor)所说的阿基琉斯是“战斗危急时全体阿开奥斯人的强大堡垒”的意思(《伊》1.284)。请阿基琉斯重返战场的议题摆在了桌面上来。
阿基琉斯 第九卷阿伽门农派“劝说团”前来阿基琉斯的营帐,许下重礼,请他重新披挂上阵。阿基琉斯的出场颇有诗意,此时他和伙伴帕特洛克罗斯正弹奏弦琴,怡然自得(《伊》9.186),似乎画面另一边战场的激烈格杀根本没有搅扰他的闲情雅兴。两种截然不同的场面形成的张力,恰好可以凸现出阿基琉斯身上不同于其他战争同僚的气质——一个孤高寂寞的英雄形象,虽然置身战场,却仿佛游离于战争之外。这是荷马的高妙所在,“老诗人极少让他出现于情节中,而让其他人喧嚣呐喊,他的英雄端坐在帐内,是为了尽量不让他在特洛亚面前的一片混乱中世俗化……理想者不可以世俗的面目出现。而让他隐退,诗人确实没有比这更美好更温柔的方式来歌咏他。”(荷尔德林1999.201-202)阿基琉斯确是荷马笔下“理想的英雄”,因而他的英雄气质既不同于识大体、背负家国兴亡重任的赫克托尔,也迥异于多谋善断、忍辱苟活的奥德修斯。 面对劝说团许诺的重礼,阿基琉斯不为所动,却提到他的生命可以有两种轨迹: 有两种命运引导我走向死亡的终点。要是我留在这里,在特洛亚城外作战,我就会丧失回家(nóstos)的机会,但名声(kléos)将不朽;要是我回家,到达亲爱的故帮土地,我就会失去美好名声,性命却长久,死亡的终点不会很快来到我这里。(《伊》9.411-16) 这是阿基琉斯第一次明确提到他的命运抉择,要么选择荣耀和死亡,要么选择无名和长寿。此时阿基琉斯已经准备打点行装返家。这是他对命运的真正选择吗?阿基琉斯对命运的认识还未到转折之时。他虽然知道荣耀与死亡相随,荣耀和生命他只能选一个,但他显然还没有经历生命之苦。他那番惜命的言辞,说任何财富“全都不能同性命相比”,“人的灵魂一旦通过牙齿的齿篱,就再夺不回来,再也赢不到手(《伊》9.405, 408-09)”,虽然是有感而发,但并非知人之语。等到帕特洛克罗斯之死让他对生命-苦难有了切身体会,阿基琉斯才会“顿悟”,做出真正的选择。 3.阿基琉斯的铠甲和顿悟 “铠甲”在荷马时代的战争中是荣誉的象征,和女俘一样,也是“荣誉礼物”。战场上战胜者一般会剥下战败者的盔甲,以彰显胜利和荣耀。阿基琉斯那副不朽的铠甲绝非凡品,乃天神所赐之物(《伊》17.195-96)。这副独一无二的铠甲代表阿基琉斯的身份和荣光。帕特洛克罗斯披挂阿基琉斯的铠甲出战,阿基琉斯的人虽未到,但他的气势已经在战场上起作用了。结果这个“假阿基琉斯”果然重创特洛亚人,一连串敌手纷纷倒在他的枪下。但帕特洛克罗斯忘记了阿基琉斯不可恋战(特别不要和赫克托尔作战)的叮嘱,一直攻杀到特洛亚城门,死在阿波罗神-欧福尔波斯-赫克托尔的一系列杀害者手中(《伊》16.790ff.)。这时赫克托尔做了一件不妥当的事,剥下了那幅辉煌的铠甲,换在了自己身上(《伊》17.192ff.)。此举冒犯了阿基琉斯的尊严和荣誉,而且冒犯了天神,连宙斯看到此景也说“可怜的人啊,你不感觉自己的死亡已经临近,现在竟然穿上了那个别人都害怕的最杰出的英雄的不朽铠甲!”(《伊》17.201-03) 当阿基琉斯从快腿的安提洛科斯那里听闻帕特洛克罗斯被杀死的噩耗,荷马用了一系列希腊人表现悲恸的典型动作描写他的反应,他双手抓泥土撒在自己头上,躺在地上抓扯头发,失声痛哭。帕特洛克罗斯之死是整个《伊利亚特》外部情节的转折点(即亚理士多德所说的“突转”),也是阿基琉斯内心体验的转折点。可以说,帕特洛克罗斯就像阿基琉斯自己,在死亡中,帕特洛克罗斯的角色与阿基琉斯由二而一(Whitman1958.136-137)。好友之死让阿基琉斯体验到一种作为共同命运的死亡,从而“顿悟”。他由此明白,他必须再次选择战场,也就是选择死亡,“因为我的心灵不允许我再活在世上,不允许我再留在人间。”(《伊》18.90-91)阿基琉斯如梦初醒,他本可以救很多人(包括帕特洛克罗斯)免于一死,然而他的忿怒让心灵失控,坐在船前袖手旁观。挚友之死让他的生命顿然失去意义,死者已去,生者何堪,阿基琉斯切身感到他的生命成为苦难,“成为大地的负担”(《伊》18.104)。帕特洛克罗斯之死还让阿基琉斯洞悉了自己的命运之谜:之前他以为早死是可以不选择、可以躲避的命运,现在他明白了命运选择只有一种,他“随时愿意迎接死亡”(《伊》18.115)。这就应验了神的预言——阿基琉斯的选择完成了“命运为他纺织在线轴上的一切安排。”(《伊》20.131) 阿基琉斯是《伊利亚特》的第一号主角,但第十六卷之前,阿基琉斯出现书中的地方不过区区二三处。《伊利亚特》后四分之一的篇幅才以阿基琉斯为中心展开。这样的谋篇布局正是荷马的匠心独运之处。整部《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象征性的死亡作为要完成的命运,这是贯穿史诗始终的底蕴。前四分之三的篇幅似乎都是为他顿悟后的重新选择做铺垫,他人虽没有出现,但他的死亡命运却一直笼罩在叙事中,让人总是感觉他的在场。一旦阿基琉斯真正重新杀入战场后,故事直接围绕着他和赫克托尔的决战展开,但那层要实现命运的气氛却淡多了。阿基琉斯的生存似乎都只为了杀死赫克托尔赢得荣誉的那一刻。这朵“英雄世界里最成功最易逝的花”(荷尔德林语)在热烈绽放后,注定要凋谢在特洛亚斯开埃城门前。荷马又一次巧布迷阵,我们没有在《伊利亚特》文本中直接看到阿基琉斯之死。 二、“凡人中最善谋略,最善词令”的奥德修斯 《伊利亚特》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善用言辞、计谋、夜袭、埋伏的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刚一亮相,荷马特别强调他外表不起眼,“但是在他从胸中发出宏亮的声音时,他的言词却像冬日的雪花纷纷落飘下,没有凡人能同奥德修斯相比”(《伊》3.219-24)。如此推崇奥德修斯的言辞,是因为言辞与智慧相关。奥德修斯在《伊利亚特》中的身份是演说家、劝说团的使者、战士。前两种身份与其善于言辞和计谋相关。到了《奥德赛》,奥德修斯直接凭借智慧和言辞(主要是谎言)完成了另一类型英雄的塑造。面对战后的新世界,奥德修斯并不以勇力取胜。与《伊利亚特》的尚武相比,《奥德赛》更重智。 1、奥德修斯的追寻 《奥德赛》的环境比《伊利亚特》复杂得多,同样是十年的时间,《伊利亚特》发生的事件定格在特洛亚,而《奥德赛》里奥德修斯跑遍地中海“四处漫游”。《伊利亚特》里的英雄只需在战场格杀,赢取战斗的胜利;《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却面对复杂的人和事,其处境和际遇几乎涵盖了古代社会的所有模式:独目巨人波吕斐摩斯的野蛮粗暴,有教养且愿意送客返乡的费埃克斯人;助人为乐的友好主人(如赐奥德修斯风袋的风王艾奥洛斯),吃人的生番巨人族莱斯特律戈涅斯人;让人遗忘过去的洛托法戈伊人,歌声迷人却异常危险的女妖塞壬;善用药草的魔力会把人变成猪猡的魔女基尔克,清纯可爱的少女瑙西卡亚和亲切感性的神女卡吕普索,等等。经过这些经历的磨砺,奥德修斯成为一个阅历丰富,理解一切事物的人(Whitman 1958.175)。荷马让奥德修斯的旅程和返乡成为人生战场,其残酷激烈丝毫不亚于血肉搏杀的真实战场,其诡谲奇幻又非真实战场可比。 和奥德修斯同住了七年的神女卡吕普索(Calypso)曾经问他,为什么不要神女的眷爱,不享受她给的长生不死,这些都是凡人艳羡追逐的东西,奥德修斯的回答是他“怀念故土,渴望返回家园”(《奥》5.219-20)。对奥德修斯的话不能只作字面的理解。表面上看,奥德修斯的旅程一直在追寻(quest),旅程的方向是返乡(home-coming)。奥德修斯舍弃神女和仙岛,选择了返乡,实质上意味着他选择的是他的过去,他的记忆。故乡家园对奥德修斯的人生而言并非实义,而是一种象征(须知奥德修斯到家后不到一个月就再次离开),象征着他来自一个有着亲密关系和社会脉络的城邦,象征着他二十多年的记忆,奥德修斯的人生由这些记忆构成。归乡途中他遇到的险阻、诱惑实则就是遗忘,或是对他是否还能保存对过去记忆的考验。 奥德修斯的人生姿态表现为追寻。追寻不同于阿基琉斯的顿悟,顿悟是瞬间的心领神会,是阿基琉斯个人心灵的感悟,而奥德修斯的追寻在广阔的人际关系中展开,他大幅度拓展生命的视野,不像阿基琉斯的顿悟是在封闭式自我的内心转折中完成。入冥之行特别以隐喻的方式呈现出另一种眼界,奥德修斯的经验已经能够超越现实世界的局限,进入另一个经验层。怪不得魔女基尔克也不得不佩服“大胆的家伙,活着去到哈得斯的居所,将两度经历死亡,其他人只死亡一次。”(《奥》12.21-22) 2、奥德修斯的谎言和智慧 构成奥德修斯本性的东西有:谎言、坚忍。荷马曾借女神雅典娜之口给奥德修斯准确地定位。当他对幻化成牧羊少年的雅典娜撒谎时,雅典娜嗔怪道: 一个人必须无比诡诈狡狯,才堪与你比试各种阴谋,即使神明也一样……你我俩人都善施计谋,你在凡人中最善谋略,最善词令,我在所有天神中间也以睿智善谋著称。(《奥》13.291ff.) 细细琢磨,雅典娜的欣赏多于责备,她并未过多责备奥德修斯居然对神撒谎(这是奥德修斯归家后第一个谎言),因为人间的奥德修斯最像她——多谋善断。 阿基琉斯不会说谎,而且憎恨说谎和说谎的人[6];但说谎是奥德修斯的生存方式。奥德修斯对所有人(包括神明)纷纷撒谎,这说明他对别人极不信任,任何人都无法轻易通过他的忠贞考验。而且,奥德修斯说谎有如真话,听者必须细心分辨,才有可能从他的谎言中探究他的真实本性。荷马曾透过他人的口,赞美奥德修斯的言辞。还不识主人身份的牧猪奴欧迈奥斯(Eumaeus)曾向佩涅洛佩说,那个外乡人[即奥德修斯]讲故事有如歌人吟唱“把我迷住”(《奥》17.521)。奥德修斯训斥出言不逊的费埃克斯人欧律阿诺斯时,也曾说过言词优美胜于外表。 奥德修斯以“足智多谋”著称,智谋主要就体现在他的言词。《奥德赛》里,奥德修斯表演的言辞主要是他对不同的人“讲故事”,故事是真是假,取决于面对的人和身处的环境如何。四处漫游时,奥德修斯说谎多半为了求生(典型的如欺骗独目巨人一节),以归返故里。归乡后,奥德修斯的重任是用计谋杀死求婚人,重建伊塔卡的秩序,为此他必须掩藏自己的身份。对求婚人,他乔装乞丐瞒过众人眼目,最后时刻现身杀之;对家人,生性多疑的他要“探察”家中的奴仆,甚至妻子,是否对他仍忠心。《奥德赛》后半段,奥德修斯几次高水平的“说谎”,几乎都是面对家人(对妻子、老父),唯一没有撒谎的例外是对儿子特勒马科斯,奥德修斯的复仇计划中唯一的天然同盟者只有儿子。当他面对二十年不见的妻子考验其忠贞时,“他说了许多谎言,说得如真事一般。(《奥》19.203)”他的谎言把妻子感动得“泪水流,沾湿了美丽的面颊”,奥德修斯虽然“心中也悲伤,怜惜自己的妻子,可他的眼睛有如牛角雕成或铁铸,在睫毛下停滞不动,狡狯的把泪水藏住。”(《奥》19.208-12) 3、奥德修斯的隐忍 与阿基琉斯的冲动、阿伽门农的蛮横相比,坚忍的奥德修斯显得更加谨慎沉稳。忍耐(themosyne)不仅是奥德修斯的品质,也是在战争后的新世界里存活的法则,他因此宁可暂时屈就卑微的角色:奥德修斯做过女神羁留的伴侣,巨人的阶下囚,“外乡乞援人”,“乞丐”,这些角色都很难和英雄扯上关系。但奥德修斯却靠着他的智慧和隐忍成为另一种类型的英雄。 杀求婚人是奥德修斯最大的一个计谋,他和特勒马科斯,加上最后时刻招募的牧猪奴和牧羊奴(《奥》21.189ff),四人协力在“家中展开阿瑞斯式的猛烈较量”(《奥》16.269),杀死了伊塔卡116个青年显贵和侍从(《奥》16.247,后只有一传令官和歌人被赦免)。这个复仇大计的成功当然归功于奥德修斯的智慧和雅典娜的襄助,但他的忍耐仍是复仇计划中重要的一环。奥德修斯离开故土二十载,回到家宅后却只能以一名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的身份进自己的家门,受到求婚人、其他乞丐、家中奴仆的种种侮辱,被人扔凳子,扔牛蹄,拳打脚踢,却一直隐忍未泄漏真实身份。他甚至叮嘱儿子,看到求婚人侮辱乔装的父亲时要忍耐,“要是他们在我们的家众对我不尊重,你要竭力忍耐,尽可眼见我受欺凌,即使他们抓住我脚跟,把我拖出门,或者投掷枪矢,你见了也须得强忍”(《奥》16.274-77)。奥德修斯对涉世不深的儿子的这番忍耐教诲,是他日后在伊塔卡为王者必须具备的品格。入夜后,奥德修斯看到家中众女仆和求婚人鬼混,他被激怒了,他对自己说 心啊,忍耐吧,你忍耐过种种恶行,肆无忌惮的库克洛普斯曾经吞噬了你的勇敢的伴侣,你当时竭力忍耐,智慧让你逃出了被认为必死的洞穴。(《奥》20.18-21)[7] 如果不是以一颗坚忍的心强忍愤怒,奥德修斯杀死众求婚人的计谋此时就功亏一篑了。奥德修斯虽名为“愤怒”[8],他不止一次的暴怒使整个《奥德赛》染上更血腥的气息,但综观他的人生轨迹,其愤懑情绪总是适时地克制,服从大局和理智,不像阿基琉斯的忿怒,除了神明的遏制没有办法可以消解。如此也不难理解,当复仇大计终告成功时奥德修斯会像冷血动物般杀戮,而且杀人后遏制住老奶妈欧律克勒娅过于兴奋的欢呼(《奥》22.407ff)。荷马把奥德修斯一分为二,把他的愤怒和理智一分为二。 《奥德赛》总体上呈现出两种奥德修斯的形象,“漫游者”奥德修斯和“复仇者”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的漫游是一种追寻,是对过去记忆的追寻,也是对知识和全知的追寻——当奥德修斯对波吕斐摩斯撒谎说他名叫“无人”时,他不自觉说出了“心灵的无名性”(伯纳德特2003.93),这正是后世的希腊哲人“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路线。奥德修斯的复仇表面看是为了搭救妻儿,更深层的目的则是要剪除不义,恢复神的正义,恢复理性和秩序。如宙斯在《奥德赛》开篇所指出的,凡人“自己丧失理智,超越命限遭不幸(《奥》1.34)”不能再归咎于神,奥德修斯的复仇就笼罩在神义论的框架中,求婚人被杀是神明对人行为不检的惩罚,“神明的意志和他们的恶行惩罚了他们……他们为自己的罪恶得到了悲惨的结果。(《奥》22.414, 416)” 三、两类英雄:“力量”与“智谋”的较量 奥德修斯的故事和生命轨迹呈现出异于阿基琉斯的另一类英雄。荣耀不是奥德修斯生命追逐的至高点,从他的追寻、智慧和忍耐,可以看出,奥德修斯式的英雄心灵更为成熟,更懂得认知自我和世界。[9]他认识的现实就与阿基琉斯不同:“奥德修斯把现实看作他面前出现的情境或问题;阿基琉斯则视现实为他自身内的某种东西,问题就在于通过行动把他自己彻底等同于现实。(Whitman 1958.175)”奥德修斯理解客观的现实和世界,而阿基琉斯的关注点始终不曾脱离他自己。所以,奥德修斯的心灵和行为较少受盲目的情绪支配,而是用理性规导,为此他运用智谋,谨慎行事,承受屈辱。奥德修斯不求光辉夺目的短暂荣耀,但求平淡朴实的长久存活,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英雄被日常化,或日常被英雄化。[10] 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通过塑造两种不同特质的英雄以及他们暗藏机锋的对峙,对照了两种英雄价值:阿基琉斯式的英雄,其标志性价值是“力量”(bíē),奥德修斯的则是“智谋”(mētis)。奥德修斯曾直言不讳对阿基琉斯说:“佩琉斯之子,阿开奥斯人的杰出战士,你比我强大,枪战技术也远远超过我,但我在判断力方面也许比你强得多,因为我比你年长,见识也比你多广,因而但愿你能耐心地听我的规劝。(《伊》19.216-20)”[11]阿基琉斯善战,希望马上投入战斗为友复仇,奥德修斯凭借判断力,以为该暂时休养疲累的军队,埋葬死者——关键时刻需要做决断时,两种英雄的价值及其观念就发生了冲突。正因为两种英雄价值互相抵牾,《奥德赛》回溯特洛亚战争时才强调“奥德修斯和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争吵”是“阿开奥斯人中的杰出英雄起纷争”(《奥》8.75,78),纷争的焦点是取特洛亚城究竟靠的是阿基琉斯的力量,还是奥德修斯的计谋(Nagy1999.45)。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的对峙是明面上的,突出的是英雄的“力量”与王权的冲突;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的对峙则反映的是另一个传统的史诗主题:“力量”和“智谋”两种英雄价值的较量。 仅从史诗文本来看,似乎《伊利亚特》以“力量”为重,故而尊崇阿基琉斯,史诗有大半篇幅表现希腊联军失去了他的“力量”蒙受了无数的苦难;而《奥德赛》通篇围绕“智谋”展开,奥德修斯并非没有勇力,但若光靠蛮力,不施计谋,他就干不成大事。如果说“《伊利亚特》属于阿基琉斯。伊利亚特的传统赋予阿基琉斯永远不朽的名声(kléos, Nagy1999.29)”,那么《奥德赛》自然属于奥德修斯。阿基琉斯在(而且只在)战场上获得了短暂而光辉夺目的荣誉,他的生命曲线在那一刻达到光辉的顶点。奥德修斯饱受苦难和磨炼,但从战场结局和人生结局来看,他胜出一筹的是,不仅在战争中赢得了不朽的名声(特洛亚城最终不是靠阿基琉斯的“力量”,而是靠奥德修斯的“木马计”被攻破),而且平安返家(nóstos)——这正是阿基琉斯的命运不允许他二者兼得的。 当诗人荷尔德林说阿基琉斯是“理想的英雄”时,他已经划定了阿基琉斯与荷马史诗中所有其他英雄人物的区别。他们(不惟奥德修斯)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理想的英雄”阿基琉斯形成对照,从而建立起史诗的全景(Whitman1958.174)。可以说,阿基琉斯的英雄主义代表的是早期希腊英雄品德的最高境地,凭靠力量和英勇争取属于自己的荣耀,死不足惜;奥德修斯的英雄主义则突出智慧和计谋,纳入了多元的关怀:对名声、自我认知、正义和王权秩序的追求。但无论如何,荷马的英雄都面对着生命的苦难。阿基琉斯以昂然的人生姿态坦然直视之,将苦难掩映在耀眼夺目的荣誉下;奥德修斯则明白他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艰难困苦,众多而艰辛,我必须把它们一一历尽(《奥》23.249-50),他承受的姿态不像阿基琉斯那样傲岸,历经磨难的奥德修斯要卑微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奥德赛》把英雄主义的魅力还原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英雄只有接受了人之为人的卑微是不可避免的,人不可僭越神明,不可忘乎所以,才可能成功(Clarke2004.89)。而这一智识,也是荷马史诗的世界观的核心,英雄的经验、苦难和荣誉成为后人理解世界现实的依托之一。 希腊人世世代代吟诵荷马史诗,对两种品质各异、旨归不同的英雄主义同样推崇。不管有多大的分野,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都属于希腊式的英雄,他们代表的英雄主义就是希腊人追求的英雄品德。 本文原载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注释: [1]hērōs一词,据Erwin Rohde的研究,是传统希腊宗教的一个古老概念,与英雄崇拜有关(英雄崇拜由祖先崇拜发展变形而来)。恰巧在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出现之时,在城邦(polis)的社会环境下,英雄崇拜的仪式渐入高潮。(Nagy1999.114-115)参《伊利亚特》(以下两部史诗分别简称为《伊》和《奥》,标注卷数和行数)23卷帕特洛克罗斯葬礼上的仪式。 [2]这个希腊词含义丰富,大约可译为“卓越”。英文常见的对译词是virtue; excellence。 [3]《伊利亚特》中,mēnis唯一没有用于神明,而用在英雄身上的,就是此处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彼此发“怒”。唯一的例外是埃涅阿斯对普里阿摩斯的mēnis(《伊》13.460),那涉及到另一个以埃涅阿斯为主要英雄的史诗传统。(Nagy1999.73) [4]尽管阿基琉斯承认他“从心里喜爱”布里塞伊斯(《伊》9.343),但争夺布里塞伊斯绝非(像我们现代人想像的那样)单纯出于爱情。布里塞伊斯被带离后,阿基琉斯马上有了另外的床伴。而且最后与阿伽门农讲和时,阿基琉斯懊悔“为了一个女子心中积郁了那么深的恼人怨气”,他甚至“愿当初攻破吕尔涅索斯挑选战利品时,阿尔特弥斯便用箭把她射死在船边。”(《伊》19.56-57, 59-60)倒不是英雄不爱美人,不过爱情在古希腊关乎风俗礼仪。说到底,布里塞伊斯还是阿基琉斯的“荣誉礼物”,是被阿基琉斯杀死了丈夫抢过来的女俘(《伊》19.295)。另外据考证,她的名字Briseis只表明她是Brisa的少女,尽管后来荷马对她也有所着墨(《伊》19:282ff),但她只是诗人的一个影子和虚构(Murray1934.204-205)。 [5]不过在社会思想史家沃格林看来,阿基琉斯的愤怒则反映出,荷马的社会是一个受制于激情(而非理性)的社会,因而整部《伊利亚特》无异于是对英雄的种种反常行为(pathology)的研究。阿基琉斯的愤怒(和帕里斯的情欲一样)是社会秩序之外一个大裂缝,一种无法控制的黑暗力量通过这个裂缝从上倾泻而下,造成社会的无序。(Voegelin1987.65-68) [6]阿基琉斯曾言“有人把事情藏心里,嘴里说另一件事情,在我看来像冥王的大门那样可恨”(《伊》9.312-313)据纳吉的考证,他此处的说辞暗指奥德修斯(Nagy1999.52)。 [7]奥德修斯似乎是荷马笔下少数几个对自己心灵讲话的人(也参《伊》11.403ff.)。赫克托尔的独白虽然也是内心心声的吐露,但主要是对外部发生事件的反应,而非把自己的心灵直接当作倾吐对象。荷马的英雄人物中,奥德修斯的自我认识能力明显高于他人,故而更能控制自己的心灵和行为,达到目的。 [8]此名为奥德修斯的外祖父所取,他说:“因为我前来这片人烟稠密的国土时,曾经对许多男男女女怒不可遏,因为我们就给他取名奥德修斯。(《奥》19.407-09)” [9]从奥德修斯的叙述角度也可察觉他的认知和理解水平。奥德修斯对费埃克斯人讲了9个故事,但这些故事不是经验本身,而是奥德修斯对经验的理解。(伯纳德特2003.75) [10]对日常的英雄化(heroization of the domestic)首先在于奥德修斯展现的是如何做一个存活者,另外,奥德修斯对胃腹需求的坚持,对财富拥有的追求,显得与常人接近。故此有论者提出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代表着两种英雄主义:荣耀之英雄主义和存活之英雄主义(翁嘉声2000)。相似的说法还有:奥德修斯以适应(adjustment)求生存,不管是自我调适还是巧妙利用处境,其目的是存活(Whitman1958.175)。 [11]两人暗藏玄机的对峙还体现在:《伊》9卷奥德修斯带领的劝说团劝说阿基琉斯无效,《奥》11卷冥府之行中奥德修斯与阿基琉斯亡灵的对话。
参考文献: Clarke, Michael,2004, “Manhood and Hero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omer, Robert Fowler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Gilbert, 1934, 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fourth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gy, Gregory, 1999, 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Concepts of the Hero in Archaic Greek Poetry,revised edition,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oegelin, Eric, 1987, “Order and Disorder”,Kenneth Atchity (ed),Critical Essays on Homer, Boston: G. K. Hall &Co. Whitman,Cedric, 1958, Homer and the Heroic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伯纳德特2003,《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程志敏译,华夏出版社 荷尔德林1999,《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 基托1998,《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翁嘉声2000,“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序言》,台北:猫头鹰 本期编辑 谢云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