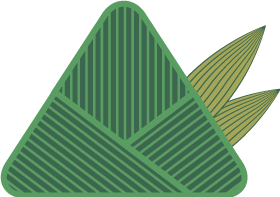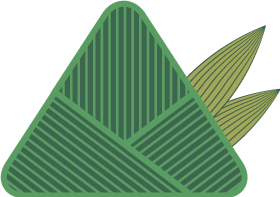|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缓和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里吗 ›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缓和 |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缓和
|
关 键 词:《民法总则》第123条;知识产权定义;知识产权类型;法定主义;规制缓和
一、立法沿革 知识产权是一种兼具人身性质和财产性质的私权,也是人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47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宪法上的原则性规范,旨在表明国家促进科技、文艺等事业发展,促进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但如何进行鼓励和帮助,需要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 1986年《民法通则》在我国立法中首次使用“知识产权”的概念,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加以概括,并进行了系统性规定。知识产权具体的权利类型,1982年《商标法》和1984年《专利法》先后制定。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和施行之后,随着1990年《著作权法》、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1997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颁布和施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规范与保护体系。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于2002年审议的《民法(草案)》中,保留《民法通则》设专章规定民事权利的做法,在其中设知识产权专门条文(第89条)进行规范。专门条文对知识产权进行规范的模式,分两款进行:第1款规定,“自然人、法人依法享有知识产权。”该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知识产权,是指就下列内容所享有的权利:(一)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及其传播;(二)专利;(三)商标及其他有关商业标识;(四)企业名称;(五)原产地标记;(六)商业秘密;(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八)植物新品种;(九)发现、发明以及其他科技成果;(十)传统知识;(十一)生物多样化;(十二)法律规定的其他智力成果。” 从2014年启动的本轮民法典编纂活动,确立了制定民法典总则编。总则编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基本上沿袭2002年《民法(草案)》第一编《总则》专门条文加以规范的做法;同时,专门条文又分两款加以具体规定,即第1款宣示性规定和第2款对知识产权定义的规定。 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稿中,第108条第1款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该条第2款规定,“知识产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所享有的权利:(一)作品;(二)专利;(三)商标;(四)地理标记;(五)商业秘密;(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数据信息;(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2002年《民法总则(草案)》关于知识产权宣示性规定,将民事主体进行“自然人”与“法人”两分,但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关于知识产权宣示性规定,则笼统地规定权利主体为“民事主体”。这种做法,采取抽象概念的方式,回避了备受争议的民事主体两分法的分类模式之分歧,也为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多元化打开了一条通道。此后,《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和三审稿关于知识产权专门条文之第1款宣示性规定,都一直采取了这一规范模式。 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稿有两个变化之处。第一个变化是,初审稿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客体”的概念,改变了2002年《民法(草案)》第一编《总则》中模糊性的“内容”的提法;第二个变化是,初审稿缩小了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从12项“内容”的具体列举,改为9项“客体”的具体列举,但又扩张了最后兜底性列项的规定,这一兜底性列项,在原有其他“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列项虽然缩小,但却留下了行政法规规定的立法空间。不过,这一兜底性列项,依然保留了模糊性概念“内容”的提法;但此后的二审稿和三审稿,均已更正为其他“客体”这一范畴。 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稿之后,关于知识产权专门条文第2款的第一个变化即明确提出“知识产权客体”范畴,关于第2款的第二个变化,即对具体权利客体的列举,存在较大的分歧。 2016年8月《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中,将是否能够作为知识产权客体存在争议的“数据信息”拆分出去,替代该项的,是“科学发现”这一权利客体。同时,对较为笼统的“专利”项,进一步分述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以符合国内关于专利权的具体权利类型及其客体。另外,关于兜底性列项中,又去掉了“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项,仅保留了“法律”规定的其它项,坚持了较为彻底的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但是,就本次立法中是否确立“科学发现”这一权利客体,后续审查中出现了分歧。二审稿加入了“科学发现”这一客体,但后来有些法律委员会委员在审议中提出,“科学发现”规定比较含糊,不宜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如果国家需要鼓励,则可以按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予以奖励。因此,2016年12月《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中,干脆去掉了“科学发现”这一项权利客体。 另外,《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条文对知识产权定义时,加上了“专属的和支配的”修辞,强调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具有绝对性。 2017年2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对《民法总则(草案)》进行最后审议,审议中,关于知识产权定义的表述,依然是权利人对知识产权客体享有的“专属的和支配的”的权利。直至3月15日审议通过的《民法总则》第123条,将修辞语改为“专有的”一词,即知识产权是指权利人对知识产权客体享有的专有权利。我们从《民法通则》将商标权表述为“商标专用权”(第96条)的用语中,能够感受到《民法总则》之“专有”对《民法通则》之“专用”在语意上的继承性。
二、规范内涵 (一)条文含义 该条将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主要类型,纳入《民法总则》之《民事权利》专章(第5章)中规定。该条两款规定,第1款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是一种宣示性规范;第2款对知识产权进行定义,并列举了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目的在于明确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和具体权利类型。《民法总则》中对知识产权进行概括性规定,带有定义性质,能够对知识产权加以概括性定义与列举,就已经完成其立法使命了。 该条还明确了其具有“专有性”,这一专有性的权利,符合大陆法系对权利规范的基本方式:一是静态意义的一般权利,即一种“对世权利”;一是动态意义上的特殊权利,即一种“对人权利”。前者为绝对权,后者为相对权。对知识产权范畴进行概括性定义,是从静态意义上进行的,其“专有性”强调了知识产权是一种“对世权”、“绝对权”的权利属性。从种属关系来讲,民事权利(私权)是属概念即上位概念,知识产权是种概念即下位概念。该条文第1款将知识产权纳入民事权利,意味着知识产权领域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规则、学说等,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 知识产权是一类权利的集合。从种属关系上讲,知识产权是属概念,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是种概念。该条文第2款规定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权利形态,并在第2款最后一项(第8项)设立兜底性规定,从立法上为这些具体的权利类型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 事实上,每一种具体类型的知识产权都是某一类权利的集合(权利束)。例如,对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兼具人身权与财产权双重性质.该条文第2款第8项“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一说,包含了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和内容实行严格的法定原则。这一规定表明,除上列7种客体之外,其他客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必须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规定,才能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如前所述,这种规定将已然存在的行政性立法确权模式都排斥在外(如《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所确立的植物新品种权),实则是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法定主义规制模式。 (二)规范路径 《民法总则》中对知识产权进行概括性定义,可以采取三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是概括现有权利类型,进行高度抽象性的定义;二是对现有的权利种类进行列举式规定;三是从权利对象或者权利客体角度进行定义。毫无疑问,该条选择的概括性定义方式是第三种模式,而且是从权利客体角度加以定义的。这一路径选择是否恰当,值得深思。特别是,权利对象与权利客体的分歧本身就已存在,而且“知识产权”之“产权”一词,本身来自一个法律规范性不明确的经济学术语,导致与识产权领域的这一分歧进一步加大。 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权”对应的对象就是“智慧财产”;日本“知的财产权”对应的对象就是“知的财产”。而权利所对应的客体,我们一般认为是由权利人(主体)对“权利对象”的权利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世纪之初的那场关于“是制定‘物权法’还是制定‘财产法’”的讨论,论战双方都承认民法所调整的并非只是“人与物的关系”,其本质表现为其背后的社会关系。 刘春田认为,“权利客体是指法律设定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基于对知识产权的对象的控制、利用和支配行为而产生的利益关系或称社会关系,它是法律所包含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春田认为,“知识产权的对象就是‘知识’本身。”而吴汉东则认为客体与对象属于同一范畴,将知识产权客体或称对象定义为“知识产品”。 无论如何,定义模式的选择,导致立法深深地介入这种看似纯粹的学理或者学术性争论——本文不希望引起意识形态的讨论,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隐含着导致法律带有不确定性的极大风险。 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学习前苏联法律理论,通常用“智力成果权”一词。1986年《民法通则》正式使用“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之后,“知识产权”一词开始取代“智力成果权”。同时,《民法通则》第97条第2款出现了“其他科技成果”的说法,“科技成果权”或者“技术成果权”等词汇,从不同的角度指代某些类型的知识产权。 (三)规范目的 在知识财产领域确认或者赋予知识创造者的产权,一方面是承认知识创造者的专有的权利,另一方面是通过产权激励机制,鼓励民事主体从事知识创造,以促进社会福祉、人类文明与进步。诚然,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客体及其具体的权利类型设计,有着不同的具体的规范目的。按照学理上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邻接权)、外观设计专利权等,旨在保护文艺创作;第二种,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旨在保护科技创新;第三种,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等,旨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三、知识产权的法定类型 1967 年斯德哥尔摩《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 2 条第 9 项规定,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以下权利:(一)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二)表演艺术家、录音和广播节目有关的权利;(三)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中的发明有关的权利;(四)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五)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六)商标、服务标记及商号名称和标志有关的权利;(七)反不正当竞争;(八)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者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其他权利。WIP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定义笼统,权利类型比较宽泛,特别是最后第(八)项兜底条款,几乎可以囊括一切知识财产领域的权利。 相对而言,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狭窄一些,但相对明确和具体。WTO框架下的1994年《TRIPS协定》规定,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以下权利:(一)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即邻接权);(二)商标权;(三)地理标志权;(四)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五)专利权;(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七)未公开的信息(商业秘密);(八)对许可合同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缘何《TRIPS协定》所定义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相对狭窄呢?顾名思义,其所定义者,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诸如科学发现权(或称发现权),因为缺乏可交易性,便不在其定义范围之内。
《民法总则》规定的知识产权客体与WIPO、TRIPS规定的权利类型对比表 WIPO TRIPS 民法总则 备注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有关的权利 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 作品 《民法总则》未区分著作权与邻接权 表演艺术家、录音和广播节目有关的权利 同上(著作权相关权利) 同上 WIPO和TRIPS将邻接权单列出来 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中的发明有关的权利 专利权 发明、实用新型 《民法总则》草案曾以“专利”概括,后分列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客体 工艺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 工艺品外观设计权 外观设计 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 《民法总则》草案曾拟“科学发现”,后删除 商标、服务标记及商号名称和标志有关的权利 商标权 商标 WIPO对商业标志(权)进行概括性规定 地理标志权 地理标志 TRIPS和《民法总则》单列地理标志(权) 未公开信息的保护 商业秘密 WIPO中没有规定,但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所保护的法益中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 反不正当竞争 对许可合同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 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者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其他权利 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民法总则》草案中曾在“法律”之后,增加“行政法规”,后删除我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规范中关于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一)专利权;(二)著作权(包括计算机软件);(三)商标权、厂商名称权、产品标记或者原产地名称权;(四)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五)植物新品种权;(六)发现权;(七)发明权;(八)反不正当竞争中的法益(包括商业秘密);(九)其他科技成果权。从《民法总则》该条的规范来看,基本上遵循国际条约与惯例,也吸收了我国现有的立法经验(如将商业秘密保护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独立出来,确认为独立的知识产权客体),确立了我国知识产权的基本权利体系。 我国在工商业标志的相关权利方面,《商标法》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商标法》采取的却是注册商标制度。2013年修改《商标法》虽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有所强化,但对商号、企业名称及其他标志的保护,没有纳入统一的商业标志保护模式。而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商标法》有所涉及的,仅仅是与注册商标相关的部分(第10条、第16条)。 同时存在的另外两种保护方式,在国务院部门规章中建立了具体的申请与注册制度:一是质检部门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二是农业部门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有上位法《农业法》(第23条、第49条)的立法依据。这种由工商、质检和农业三部门形成的“三足鼎立”式的地理标志保护模式,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权利冲突,特别是同属工商业标志的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之间的冲突尤为突出。立法过程中对此客体是否列入虽有存废之论,但立法者最终因《TRIPS协定》单列而列入。 本文认为,“三足鼎立”的管理与保护模式,加上实践中的权利冲突,是促成该条立法将“地理标志”单列的根本性因素,而这,也许是相对保守的《民法总则》立法中出现的些许亮点之一。 不过,该条文最终没有将“科学发现”这一客体纳入知识产权权利客体,对应的“发现权”(或称“科学发现权”)没有在《民法总则》中确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更加重视《TRIPS协定》,具有较为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特别是,除了《民法通则》对此有规定之外(第97条),《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也列举了“发现权”,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之下否定“科学发现”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难以想象的。 据张新宝介绍,《民法总则》起草初期曾将“科学发现”列入,但在讨论中有些委员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科学发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或者这样的立法规定过于含糊。自草案第三次审议稿开始,不再将“科学发现”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而对于有重大科学发现成果的,可以依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予以行政性质的奖励。另外,由于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成果与司法经验缺乏总结,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如第5条规定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权利保护)没有在这次立法中直接体现。 四、法定主义的缓和方式(代结语) 《民法总则》第123条规定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是一个“7+N”模式,该条文第2款第8项兜底条款,还是为后续立法或者法律修订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事实上,该条文实行了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排除了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司法判例等创设知识产权新的权利类型的可能性。因此,下一步如何对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加以缓和,以适应技术变迁和知识社会的突飞猛进,是立法留下的重大议题。 本文认为,《民法总则》对知识产权的规范是结构性的,除了第123条规定概括性定义之外,其他规定同样可以适用。这是知识产权权利扩张之立法论和解释论的基础,也是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进行规定的根本意义之所在。例如,《民法总则》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稿中也曾将“数据信息”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但因争议较大,且“数据信息”过于宽泛和模糊,后来从知识产权的客体中删除。最后对此加以原则性规定,“ 一方面,确立了依法保护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原则。另一方面,鉴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存在争议,需要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进一步总结理论和司法实践的经验,为以后立法提供坚实基础。”与之相适应,《著作权法》通过汇编作品对数据库的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保护、《民法总则》第113条关于财产权利平等保护等,都可能成为扩张解释的基础;而《民法总则》第127条授权立法的模式,更是为未来立法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 同样,如前面知识产权客体与WIPO、TRIPS规定的权利类型对比表中所列,第123条规定的客体中并未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或者“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之类的表述。但相关的内容和权利,在《民法总则》第132条对权利不得滥用的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这一规定,与《民法总则》第7条诚信条款相协调、相一致。事实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经历了从抗辩事由到一般原则的转化,与诚信条款相得益彰,正反而合,从正题和反题两个角度规制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这种规定,对应的就是WIPO和《TRIPS协定》中禁止他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利。 另外,《民法总则》第10条处理民事纠纷中确立了习惯的法源地位,可能是一道打开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方便之门。该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即便第123条在绝对性权利之取得方面缺乏明确的法律确认机制,但商业习惯、科研伦理、善良风俗等在解决两造纠纷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间接承认该条第2款前7项之外的其他权利。 因此,正如本人曾经指出的,“民事制度中的相关学说、理论与规则,可以克服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与类型化之不足的局限。对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救济体系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这只是一种解释论的发展路径,对司法实践的意义更大一些,即通过司法适用中强化知识产权私权观,利用现有的民事法律关系保护知识创造者的权利。而从根本上讲,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透过法律的废、改、立,完善知识产权权利体系。 在民法典与知识产权立法选择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改造和整合知识产权领域各单行法,将知识产权法整体纳入民法典单独成编;第二种观点,知识产权法的一般规定单独一编在民法典中体现,而大量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则游离于民法典之外;第三种观点,知识产权领域各单行法性质迥异,务使诸法林立,以尽显特色。 客观地讲,从现有民法典编纂组织形式和立法能力来看,按照民法典立法规划,在剩下1年有余的时间之内,全国人大法工委似乎只能够对现有的《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各单行法加以整合或者修订,以此形成民法典分编,再与《民法总则》汇编成典。 更何况,知识产权法独立成编的设想和立法探索,即尝试及其失败——2002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民法草案》并没有将知识产权法整合成单独的一编,还深深地印刻在立法者的脑海里。即便民法典最终未能将知识产权法作为独立的一编纳入,但《民法总则》第123条第2款第(八)项之“法律”的立法要求(包括授权立法的第127条),对后续知识产权权利生长及确定模式,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从1982年《商标法》制定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主要以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单独立法形式(或出自全国人大立法,或出自行政性立法)出现,有些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以附属性立法形式存在,如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中,又如《农业法》规定“符合规定产地及生产规范要求的农产品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第23条第3款)。 国务院行政法规对知识产权保护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们是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单行法施行的配套性规范;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创设新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的作用.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之后,那些创设新型知识产权的行政法规(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如何处理,是作为《民法总则》配套性的行政法规看待,还是需要将这些行政法规上升到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层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关于地理标志的“三足鼎立”式保护模式,具体的地理标志权的认定只是国家质检部门和农业部门分别对“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从产品质量认证的角度制定了各自相应的部门规章,缺乏系统、协调的法律规范,包括国务院行政立法层面也没有系统性规定——事实上,如《农业法》(第23条第3款)那样,地理标志的申请、授权或者认定是具有明确的立法要求的。 本文认为,规制缓和方式的第一阶段或者说第一步,还是尽快将已有的国务院行政法规上升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相应的权利,完善各类型的知识产权单行法;同时,制定统一的《地理标志法》(或称《地理标志保护法》),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单行法的规范法律体系。就地理标志、特有的包装或者装潢等标志保护而言,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是,将商标法进行彻底改造,摒弃注册商标立法模式,使之成为能够涵盖各种工商业标志的单行法。 当然,如果条件成熟或者立法者下定决心,在民法典编纂活动中及时制定知识产权分编,可以最大限度地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权利体系,并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全面融入现有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如其不然,尽快制定单独的知识产权法典,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统一的法律规范,也是可以期待的方式。 (由西南政法大学法律(法学)专业2016级研究生周厚燕整理、编辑) 版权声明 作品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无意中侵犯了您的版权,请来信告知,本站将在2个工作日内删除。 西南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共同体 官方网站:www.xinanipr.com 赐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新浪微博:@西南知识产权 作者易继明的文章《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缓和 ——兼对第123条条文的分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