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世纪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空间的初始解释和理由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欧洲入侵美洲的时间 › 16世纪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空间的初始解释和理由 |
16世纪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空间的初始解释和理由
 下文摘自《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9辑)》,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 16世纪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空间的初始解释和理由 〔委内瑞拉〕卡洛斯·阿方索·弗朗哥·希尔 著 姜玉妍 译 15世纪末,欧洲探险家代表卡斯蒂利亚王国来到后来被称为美洲的领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彻底改变了全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关系、观念和动态。然而,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即通常在史学上被确定为“征服”的阶段,在不同的领域内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个对于欧洲人来说全新的地理空间和与其人类学概念相对立的一些居民,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理解和认知方式。 如果单纯地从文化情境出发,探险和定居的过程是围绕着以前伊比利亚人在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和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探险经历而展开的,构成了1492年事件前后的背景,如1479年的《阿尔卡索瓦斯—托莱多和约》(Alcaçovas-Toledo),该和约促成了法律和宗教条约的建立,为16世纪的征服合法化奠定了基础。通过对这些过程和讨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因素,使我们更接近美洲历史在上述阶段发展起来的其他标准。 一 将美洲征服作为文化问题 随着1492年欧洲人抵达并逐步定居在后来被称为美洲的领土上[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ldsmuller)在1507年出版的地图上首次绘制了“美洲”],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时代,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并揭示了有关事件的复杂性。因此,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处理历史分析的层次;其中之一是对文化问题的解读,这些问题已经逐渐交织在大陆空间的动态现状中。 考虑到这一点,以下方法从文化形貌“碰撞”的角度来解读16世纪的美洲征服问题,这些文化形貌在有关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具体来说,我们将把重点放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伊比利亚主体上,这将使我们首先从国家限定词(西班牙和葡萄牙)中,打破对这些主体的同质化概念束缚,理解半岛王国的异质性特征是文化形貌的一个基本要素,构成了与其他“海外领土”(plus ultra mare)形貌的互动框架。同时,我们将更加接近于对人类和领土的解释范式,以及从形成的想象中为征服所开启的历史进程提供法律依据。 在进入深度叙述和分析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些概念标准,用以处理这篇文章。首先,我们确定,在我们的解释兴趣下,“文化”这个术语超越了一些科学定义,这些定义将概念局限于人类所创造的东西上,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产生了一个对立的标准。我们将专注于概念化,使文化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认知关系,与构成社会物质生活的强制性关系共同形成支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 文化包含了一套抽象化的社会过程,或者更复杂地说,文化包含了一整套抽象化的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 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利尼(Néstor García Canclini)指出,文化研究领域正在向社会历史领域过渡,这迫使我们深入理解社会现象中可认知到的解释框架,它们已经或可能具有历史性。 考虑到这一定义,我们分析的主要目的不是伊比利亚人在16世纪的美洲做了什么的问题,而是伊比利亚人作为一个文化主体,如何利用一系列诸如宇宙学、象征性、意识形态和宗教之类的文化负载,去解释超出自我认知体系外的人类、社会和地理状况,从构成的地方进行解释。这一因素将逐步把伊比利亚文化形貌的转变作为初始框架,并引入一种更复杂的新文化形貌:美洲文化形貌。简而言之,这一框架让我们看到埃德孟多·奥戈尔曼(Edmundo O’Gorman)所命名的“美洲的创造”的更深层面。 同样,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所说的“文化形貌”的概念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在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中被破坏的。我们可以将“文化形貌”视为文化互动的范畴,它以文化行动者和文化集体的异质性为基础,通过四个构成要素联系在一起,正如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Alejandro Grimson)在他的文章《文化的界限:身份认同理论的批判》中指出的那样,这些要素是可能性领域、各方互动的逻辑、共同的象征性情节和共享要素。 “可能性领域”涉及定义社会生活选项的多种解释、象征和代表,尽管它们是异质的,但它们是对文化形貌定义的边界,从而从部分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从一个集合体形成一个整体。例如,我们可以在16世纪的美洲案例中看到,伊比利亚人的表现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一名塞维利亚人与一名里斯本人并不相同),从异质性中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形貌。他们有拒绝人类牺牲的共同意识,决定了其与同一领域中前西班牙美洲文化代表的界限,在那里献祭是一种常见的仪式行为。 这个可能性的框架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其中有一种逻辑使其在思想意识的基础上变得合理,尽管行动者具有异质性,但他们构建了社会生活并使得这种互动变得合乎逻辑。这是由一个共同的象征性情节所补充的,在这种情节中,尽管事物的意义可能不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位于同种框架下,使概念的补充和对立都可以被理解。 最后,文化形貌的参与者有着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发出时可能是分散的,但最终会将上述系统合并在一起。考虑到上述构成要素,我们可以认为“伊比利亚人”是“伊比利亚”文化形貌的轴心主体,从1492年开始,它与其他文化形貌接触,它们中大部分没有联系,但都同为新互动的参与者,在随后的时代中将被定义为新的文化形态。 二 中世纪的人 文化背景是使1492年10月12日后的历史进程变得活跃的基础,以参与随后事件的社会行动者的异质性表达为特点。虽然在后来被称为美洲的整个领土上的原始民族确实是极其多样化的,但逐步入侵新领土的欧洲人也以这种特殊性为特点,扩大了16世纪关于这块大陆上的地理学和人种学知识,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大陆是相连的实体。因此,首先要指出我们此刻指的是哪种欧洲人,这将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定在征服进程中,影响欧洲人日常生活和法律程序的文化要素。 在史学中,特别是在具有学术特征的著作中,人们常常认为是西班牙人领导了最初对美洲的探索和入侵,与仅限于在“新世界”东南海岸探索的葡萄牙人一样。这一观点建立在一系列模棱两可且笼统的基础上,扭曲了15世纪欧洲历史背景下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然而,这种过于简化的立场表明了一个事实:在大陆定居的第一阶段是由伊比利亚王国领导的。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在教皇所代表的政治宗教权威的支持下,伊比利亚王国在这项事业中获得了排他性,这个因素我们将在随后的文中讨论。 现在,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文本中谈论“西班牙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一身份既没有得到巩固,也没有在具体的文化遗产中被提出;它以1492年10月12日前后的两个事件为基础,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两个事件为1469年著名的天主教双王联姻(1479年卡斯蒂利亚继承战争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强强联合)以及1492年1月2日格拉纳达的收复失地运动。西班牙哲学家胡利安·马里亚斯(Julián Marías)在概述西班牙思想的原始历史基础时提出了这个因素。 ……入侵被认为是西班牙的损失,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永远无法接受的;西班牙决定成为基督教王国,这意味着它成为欧洲的,西方的。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起源,对于收复失地运动,或对于什么?对于失去的西班牙,因此是不真实的,但在其视野中存在,作为一个理想,一个目标。这是西班牙的计划。 考虑到这一点,在15世纪末的时局中西班牙主体并不存在明确的身份认同,因此,大部分进入新世界的个人和集体并没有对这一坚定的国家计划做出具体的回应。尽管必须指出,在西班牙身份统一的想法与该国各地的多样化差别相去甚远,但这同时也是耸人听闻的独裁计划的结果,它与佛朗哥主义一起标志着西班牙20世纪的一部分。 在葡萄牙同胞中,这些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并未被深刻地表现出来,特别是由于葡萄牙人的想象力集中固定在非洲海岸的探险经历上,这夸大了诸如航海家唐·恩里克王子(Dom Henrique)这样的民族人物,同时也巩固了天主教的统治。这些因素中的一部分为巴西社会学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所认知的“葡萄牙国家出现的早熟”奠定了基础。然而,重要的是考察进入巴西的葡萄牙人都是哪类人,因为这暗示着复杂且根深蒂固的文化结构。 因此,基本因素之一是将伊比利亚主体理解为15世纪在美洲进行探险并定居的欧洲人中的主要行动者。我们提出的一个默认因素是宗教决定因素,即葡萄牙人、卡斯蒂利亚人和阿拉贡人围绕着天主教转,这个因素巩固了半岛拥有欧洲文化的地位,并制约了两个基本进程:其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即罗马教皇等级制度承认伊比利亚王国是天主教的堡垒;其二是在逐渐被吞并的美洲空间里,围绕基督教信仰及其实践对社会主体进行限制。哥伦比亚历史学家赫尔曼·阿西涅加斯(Germán Arciniegas)指出,16世纪的美洲是“平民的黄金世纪”,他认为社会、政治和宗教进程是由进入该大陆的平民所推动的,他对这些人进行了这样描述和形容: 前来征服的人民是野蛮的、危险的、血腥的、卑劣的,同时也是无知的……16世纪在美洲的军队是一个混乱的群体,其中不仅有战士,还有许多其他职业的人,比如木匠、铁匠、绳匠、泥瓦匠、制革师、军械师、冶炼师、火药商等。有时,部队中的人是农民,他们在必要时变成了工匠……做出地理发现的农民、士兵、修士和工匠人群……是西班牙平民一部分,对于贵族而言则是一堆垃圾…… 这一描述具体说明了在占领的初始阶段执行西班牙计划的部分主体,为了对地区间多样的特殊性进行更深刻的探索,必须对这一主体进行分析,尽管对他们的分析会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但它是后来从文化混合和融合的角度理解混血种族的一个重要因素。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同样致力于另一个复杂的层面,描绘从1500年起到达巴西的普通葡萄牙人的面貌: 来到巴西的大多数葡萄牙人是流亡者。他们如此之多,以至于把这片土地都变成了罪犯的巢穴,不仅耶稣会士这样认为,这些人自己也这样认为……就巴西而言……应该指出,累计犯有三次罪行的犯人会被送往这片土地。流放到巴西被认为比到非洲或亚洲还要糟糕得多……因此这些人是葡萄牙派遣到巴西大陆,用以繁衍后代并征服大陆的。这些人,被强行安置到这里……这些强壮而丑陋的人被迫成为我们的开国元勋,成为那些事实上强行开办海外企业并孕育我们的人。 我们注意到,这里提到了一个作为平民群众的文化主体,作为16世纪在美洲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行为者,其所承载的宇宙观与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紧密相连,同时也是文化存在的构成基础。现在,我们可以将伊比利亚主体框定为在半岛特殊性下中世纪晚期的一种表达;然而,抵达美洲意味着对已形成的观念和表现的冲击,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关于文化碰撞的一章里指出了这一设想,即在欧洲的种族和地理背景遭到挑战的情况下,中世纪的人群开始用其想象力来解释征服。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宇宙观的基础是天主教,但作为一个世俗的主体,同样存在一些教义外的其他构想,这也是有关想象力的基本组成部分: 哥伦布不仅相信基督教教义:他还相信(在那个时代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独眼巨人和美人鱼,相信亚马孙人和长着尾巴的人,而他的信仰竟和圣彼得一样如此强烈,正是这种信仰使他最终发现了美洲。 尽管哥伦布本身并不属于伊比利亚主体,但他的逻辑和伊比利亚主体一样都处于相同的框架下,即欧洲的框架,因此认为他属于伊比利亚文化形貌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可以说,这种碰撞促使从中世纪伊比利亚主体过渡到现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主体,这是胡利安·马里亚斯再次总结的言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进取精神使西班牙与葡萄牙一起远渡重洋。美洲的发现……使勉强统一的西班牙超越了自己,也就是说,把它的计划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从而产生了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嫁接,其结果是天主教君主国的诞生……其另一个名字是西班牙王国,最初的西班牙只是现在王国中的一部分。 三 新世界 最初强调的几个方面主要涉及从1492年开始,那些美洲殖民者在文化和宇宙观方面的基础,1492年前后的那些时刻以同样的方式逐步挑战着想象中的固有准则。在我们看来,美洲的发现与欧洲人的想象这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解释和整合的多重节奏,对16世纪初的伊比利亚人(尤其是到达美洲的普通伊比利亚主体)而言,这是对自然和人的重大发现。 这种互动是围绕着一系列具有文化形貌的主观先决条件所展开的,在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作品《美洲的征服:他者的问题》中,按价值论、实践论和认识论的顺序确定了现阶段大陆历史差异性问题的核心。这种方法受到个人主观行为的制约:新事物是好是坏(我想要或不想要),我对新事物感觉有多亲近(我把自己同化为新事物,或者我把新事物同化为自己),以及我对新事物了解多少(我是否忽略了他者的身份,以及我对自己的身份了解多少)。 因此,考虑到上述问题,我们从一个场景出发,在主体内部并未形成具有当代一致性特征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民族性仍在构建中,内部蕴含丰富的多样性,这将使得对人和自然的看法因人而异。 基于上述情况,美洲的大自然挑战着15世纪末美洲殖民者的认知。这是一个面积与他们的世界无可比拟的领土:河流、丛林、山川和平原,其面积、颜色和气味都对这一主体的认知构成挑战。这是一种未知的东西,所以在理解它的最初时刻,他们是结合自己的信仰来理解的;如果考虑到我们谈论的欧洲主体来自中世纪的最后阶段,那么关于这一领域的最初价值判断(认识论层面的互动)指出他们已经到达了《圣经》中的天堂也就不奇怪了。哥伦布在1492年的信中的论断暗示了这一点: ……这些是证明这里是人间天堂的重要迹象,因为这个地点符合那些神学家的想象;此外,这些迹象也是非常一致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多的淡水这样流淌着,与海相邻。 这种对地理环境理解的进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对其探险的不断深入,这一要素也在动态中被重新解释。然而,将美洲理解为天堂是一种被长期坚持的看法;已经发现17世纪中期的一些著作仍然这样描述美洲领土。这可以从1663年西芒·德·巴斯孔塞洛斯(Simao de Vasconcelos)撰写的《关于过去巴西事物的重要奇闻》中看出: 许多严肃的作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都认为上帝将人间的天堂创立在赤道以下至热带地区中部,在它下面,或在它旁边,或从它向南……,他们认为,在赤道以下至热带地区中部,上帝创造了人间天堂,因为这是整个宇宙中最温和、最宜人和最令人愉快的部分…… 同样,巴西作家塞尔希奥·布阿尔克·德·霍兰达(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在其作品《天堂的愿景》中认为,导致中世纪伊比利亚人前往新大陆的部分动机与“伊甸园”有关,其指的是在美洲领土上发现了《圣经》中的天堂,除了宗教因素外,还是在他们的文化框架下一个符合逻辑的想法: 事实上,经文中说,伊甸园在亚当后来居住的土地的东部,根据最初的表象这种迹象是值得怀疑的。但对安东尼奥·莱昂·皮内罗(Antonio Léon Pinelo)则不然。很明显,圣书的意思是,就可居住的范围而言,伊甸园所在的区域位于特殊的位置,远离东方,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远离已知的土地,这只能意味着这片区域在美洲。他很快就克服了另一个困难,他将天堂的四条河流即普拉塔河、亚马孙河、马格达莱纳河和奥里诺科河分别与比逊河、基训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相互对应。另外,导致亚当和夏娃厄运的水果肯定不是只在其他纬度地区自然生长的苹果……知善恶树的果实只能是西班牙印第安地区的西番莲果(maracujá、pasionaria、gradilla),它的香气和味道能够激起夏娃的食欲,其神秘的花朵明显带有主受难的标志。 这种观念不仅停留在浪漫的、田园式的或理想的范围内,而且还拥有具体的金融投资潜力,西班牙历史学家德梅特里奥·拉莫斯·佩雷斯(Demetrio Ramos Pérez)在其1987年的作品《金色神话:起源和过程》中评论了这种做法。他指出,德国在这块大陆上的投资是以“金色”作为理由的,它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可以承担金融风险的现实。 以上是对领土位置方面的理解,此外还存在一个方面,即这一地理如何成为(或并未成为)“我所认知的世界的一部分,以及我如何将它整合到这一认知中”,涉及人类行为学的层次。当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Arturo Úslar Pietri)在他的文章《哥特人、暴动者和幻想家》[发表在《新世界,新世界》(Nuevo Mundo,Nuevo Mundo)中]中谈到对三个意大利人[哥伦布(Colón),发现者;佩德罗·马尔蒂·德·安格莱利亚(Pedro Mártir de Anglería),解释者;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érico Vespucci),命名者]的构想时,这种动态很容易将其综合起来并加以说明。 因此,有必要考虑在1492年的时候,欧洲的各个知识界对世界持有什么样的想法,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主要与公元2世纪的特洛梅克(Tlomejco)地图有关,在该地图中,世界由三块组成——欧洲、亚洲和非洲,领土被陆地之间的海洋(地中海)分割。 在这一层面的解释中,探险家们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将这些领土融入他们所知道的世界中,这一做法的代表是哥伦布,他宣称,根据克劳迪奥·特洛梅奥(Claudio Tlomeo)确定的空间划分,新的领域是“印度群岛”,已知世界的最东端。这种最初的认识导致了西印度群岛这一常见叫法的产生,用以确定美洲领土。佩德罗·马尔蒂·德·安格莱利亚在后来的时间里,将这种融合的方法用于当时的人文发展,使用了“新世界”(Nuevo Mundo)这个词来形容这些领土,尽管它们仍然与既定的观念有关,但远非印度的一部分。最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不仅与新大陆被命名为美洲有关,他还是成功将大陆视野和固定领土视野带到这些领土上的人,他将这一因素与已知的整合理念相对照,即新的板块必须被整合进整体板块之中。这样一来,在全球地理学的发展中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美洲作为一块领土,逐渐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反过来又改变了后者内部和外部的文化观。 四 新人类 16世纪在对征服进程的解释中,对“人类”的研究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因为欧洲人对美洲人的理解受欧洲自身文化的限制。这种复杂性最初始于对他人的无知和对自我的认知。 ……在16世纪初,美洲的印第安人确实存在,但我们忽略了关于他们的一切。然而,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我们将关于其他遥远种族的图像和想法放到最近新发现的物种上。如果殖民者真的使用“相遇”一词,那么这场“相遇”将永远不会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16世纪将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 在上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中,欧洲人开始与美洲接触。出于启发式的原因,我们今天关于征服进程的分析更多地参考了伊比利亚人,而不是印第安人,因为尽管提到了对原始群体的描述,但这种描述是从传播者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因此它可以成为欧洲人用来理解土著人的认知网络工具,用以处理对前者来说完全陌生的人类学现实。 因此,对于将印第安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人们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一问题在哥伦布的信件中得到了证明,信中对未知事物的描述是占上风的,特别是与作者日常社会结构相悖的因素。信中重点叙述了土著人的裸体,以及对贵金属分级的无知。这一框架对于理解相互之间的价值秩序和尺度是奏效的,不同的框架是无法被相互理解的。简而言之,两种文化形貌间是相互隔绝的。我们可以参考茨维坦·托多罗夫的价值秩序框架,它使我们看到伊比利亚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解释。 在价值论层面上,我们经常会发现判断的立场游走于善恶两端,尽管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天主教纲领之外的任何做法都是违反教义的;但在最初与美洲人的接触中,欧洲人并没有试图对他们进行解释,而是通过占卜对他们直接作出论断: ……祭司们亲自为欧洲天主教信徒预言未来的事情,以及他们在工作中所期待的结果,引导并使他们远离战争……占卜是上帝唯一的恩赐,因此,滥用占卜的人应该被看成骗子而受到惩罚。 尽管伊比利亚主体在信仰实践中可能具有内在的灵活性或形式,但宗教教义是特定互动中的基本依据,这导致了严重的主观性立场。 在人类行为学方面,这种方法也是围绕着欧洲主体所进行的,在这方面更常见的是将土著人相关的事务与欧洲世界所知道的事务进行比较,从而在主观解释中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主体将未知的事务限定到文化形貌的认知网络中,以便将其汇编成可以理解的事务。 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瓦卡(Álvar Núñez Cabeza de Vaca)是卡斯蒂利亚的一名先遣官,他在日记中叙述了16世纪他在加勒比海被土著人俘虏的经历,并详细地讲道:“他们都是战斗者,就像在意大利持续的战斗中长大的一样,在防御敌人方面相当狡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把理解带到了他所知道的东西中,关于战争的概念,关于战斗民族的概念。总之,带到了他理解的框架中。 在认识论方面,有一种困惑甚至使欧洲人与美洲人无法一起生活。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土著人的做法不在伊比利亚人所理解的框架和认知之内。这可以从罗德里戈·德·基罗加(Rodrigo de Quiroga)总督在1579年发表的评论中看出,他在智利说道: ……他们是一个全身赤裸的民族,缺乏司法秩序和政治生活,因为在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司法秩序,他们也不守真理,没有任何羞耻心,不知道什么是忠告,他们以酗酒为荣,兽性很大,而且有非常淫荡的恶习,是一群非常懒惰、卑鄙、爱撒谎且贫穷的家伙,不置办或拥有任何财产,不种庄稼,甚至无法养活自己,毫无理智可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判断基于一种文化框架,它定义了面向制度性的司法概念和实践以及法律的应用,但对上述土著人的生存形态、政治形态和司法形态却一无所知。印第安人在当时伊比利亚形貌的文化解释框架之外,因此伊比利亚主体对美洲形貌转变和融合的预测十分有限。 这几句话概括了这些人对那些为他们服务了近40年的人的看法。其中混杂了对印第安人拒绝播种的岁月的记忆和对印第安社会的扭曲看法,在这种看法中他们只承认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而群居生活中的任何其他特性都被排斥在上述讨论之外。 五 来自经验的法律体系 征服的法律体系基础源自两个要素:欧洲中世纪末的习惯法以及15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征服和殖民之前的经历。此外,还有另一个要素是从人性的角度思考1492年之前定居在美洲的土著人。 首先,支持征服的最重要的文件是由天主教会通过一系列“教皇训谕”发布的。其中第一个对美洲进程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教皇尼古拉五世(Nicolás V)于1454年发布的罗马教皇训谕,根据达西·里贝罗的说法,该训谕“使欧洲扩张合法化和神圣化”。其中指出: ……我们授予阿方索国王充分和自由的权力,其中包括入侵、征服、降服任何萨拉逊人(sarracenos,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和异教徒的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基督徒的敌人,应使所有的人都沦为奴隶,并将一切用于自己和后代的利益…… 这是一份在1492年10月12日里程碑事件之前的文件,对理解欧洲在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进程至关重要,尤其因为它是证明殖民前的经验为后来的形态提供条件的框架基础。 与尼古拉五世发布的教皇训谕一起,1492年之前的另一份基础文件是1479年葡萄牙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室之间的《阿尔卡索瓦斯——托莱多和约》,该和约是一份和平协议,其为每个王国都划定了事实上的海上航行区。这最初有利于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的沿海航行,同时推动卡斯蒂利亚人在加那利群岛以外的地方进行探险,并将这些岛屿的主权授予卡斯蒂利亚人。 在加那利群岛的权利方面,卡斯蒂利亚王国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与葡萄牙人在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岛上的情况不同,它们是无人居住的岛屿,所以适用无主财产(Rex Nullius)的法律准则,但加那利群岛上有土著人:关切人。对于这一因素,诉讼依据的立场是基于1454年教皇训谕中所规定的主要准则,用理查德·孔内茨克(Richard Konetzke)的话来说: ……符合当时一种普遍的法律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将新发现的属于非基督教王室的地域据为己有是合法的。中世纪人的法律意识是受宗教启发的。作为基督徒,他认为自己应比异教徒享有更好的占有权。 关于征服关切人的描述和摆脱异教徒的态度一样,即在征服者身上除文明之外,同时还有一种与信仰密切相关的因素,它产生了一种二元论,维持了一种对土著人的贬低态度,甚至在征服者最初剥夺加那利群岛的土著人权利之前就已经有这种态度。 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在最初征服这群人性仍然存疑的人类群体时,美洲的征服并不是一个让卡斯蒂利亚人措手不及的事件。 现在,为了我们的分析兴趣,必须指出上述对道德和宗教的讨论同样是在既定的文化框架下进行的,因为对土著人人性的理解主要基于经院哲学的思想,而这种思想认为异教国王有权根据《自然法》(Derecho Natural)拥有财产和王国,这使伊比利亚人的入侵行为失去合法性。辩论的重点在于“亚历山大训谕”(Bulas Alejandrinas)的合法性(这些教皇训谕在1493年确立了在美洲的探险分界线),尽管一些经院法学家这样认为: ……在这一点上,托马斯·德·阿基诺(Tomás de Aquino)认为,基督并不希望成为一个人间的王子。由此他推断……教皇也没有世俗的权威,异教徒更是完全缺乏权威。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等人是这一立场的广泛支持者。与之前的观点相反,这种观点认为,教皇的计划是根据传达者的准则,努力将信仰带给信仰缺失者,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将谈论殖民为美洲所带来的福音,而不是征服,16世纪西班牙社会在美洲的定居进程中,始终坚持为美洲带来福音的说法。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辩证的理想主义中,其结果是形成了万民法(Jus Gestium)这一综合法,只要不侵犯土著人的权利,便赋予欧洲人在美洲定居以及发展经济、政治和开展社会活动的权利。现在,如果土著人不尊重他人的权利或伊比利亚人“仁慈的”告诫,后者就可以自由地训斥和制服他们。在没有对话者和法官的情况下,这些暴行只会以纯粹的主观秩序为基础。 这一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被16世纪的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发生的人口混合所削弱,这强化了委托监护制的引进和黑人的输入,在当时的伊比利亚人的心智中这些黑人毫无疑问是“非人类”的。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法规看到,在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定义的心智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下,中世纪主体的法律、想象的转变和文化表现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例中逐步构建起来的,这一进程随着文化和人种融合进程的节奏而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行动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美洲人,成为新计划在我们的大陆上稳固的标志。 结论:从征服和权力讨论的角度解读史学问题 关于16世纪对美洲领土的征服,再次陷入一系列以两个症结为特征的讨论,我们认为这削弱了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潜力。 第一个是指围绕着诸如“发现、两个世界的交汇、印第安人的抵抗或西班牙日”等使用范畴的价值判断,从而引发了一场围绕政治秩序——意识形态的辩论,结果通过一个实用的推断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有问题的方法失效。 第二个问题涉及欧洲人在伊比利亚美洲殖民统治下建立话语权力的解决,这对该大陆的史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也简化了一个历史现实,这一历史现实交织在一个变量框架中,后者使1492年以来的进程更加丰富和复杂。 其中一个适用的变量将我们引向文化史,我们将其作为分析准则,以此将征服作为一个由不同层面组成的复杂历史问题来对待。我们在整个研究中使用的因素使我们能够看到所构建的文化想象是如何在最初成为理解伊比利亚主体的桥梁。在日常所获得的认知关系中,这些主体是一个不同世界文化形貌的一部分,与自然和人类等领域相互作用。对世界的认知是受条件限制的,人类学家艾曼纽·阿莫迪奥(Emmanuel Amodio)以今天委内瑞拉东部特定空间为例证明了这个问题。 因此,库马纳(Cumaná)开始了它作为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边陲小镇史: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住在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和最近到达的西班牙人。也许正是这种领土和文化上的边界条件,从根本上说明了在西班牙人存在的三个世纪里,委内瑞拉东部居民的演变和特征。 这个过程逐渐导致了某些意义的转变,正如为了使新人种进入不久前所建立的人种框架,法律逐步进行了调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征服,接触的文化形貌开始了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转变过程,由于这些形貌是动态的,加之文化的适应、再认识和转化,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文化融合的过程导致了新主体形成,其在异质性中塑造了17世纪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社会的辉煌,殖民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伊比利亚人对局外事物的解释构成,直到逐渐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 书籍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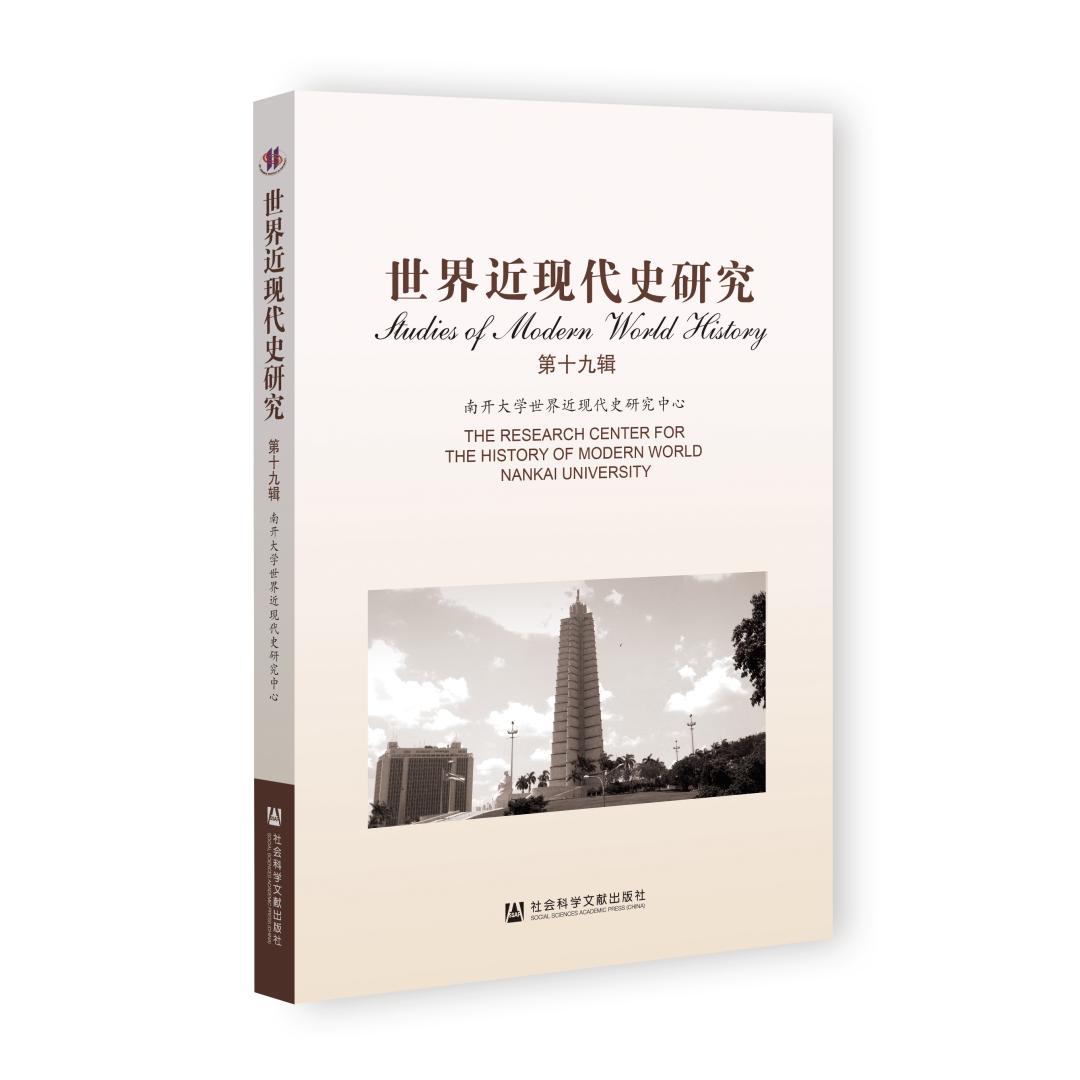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9辑)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编 2023年3月出版/98.00元 978-7-5228-1466-7 内容简介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年刊,面向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促进和推动国内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而提供的一个学术交流的园地,辟有史学理论研究、全球史研究、国际关系史、地区国别史、博士生论坛、争鸣、书评、史学资料、研究综述等栏目,对于推动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为第十九辑,收入17篇文章,分为“第一届跨国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选登、拉丁美洲史专论、地区国别史、史学史料、博士生论坛、书评六个栏目。 书籍目录 “第一届跨国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选登 费边社会主义与查尔斯·比尔德经济史观的形成 宋晓东 “南北朝正闰问题”与近代日本“皇国史观”的构建 瞿亮 晚清女学堂中的日本女教员——以服部繁子为中心 殷乐 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的对华调查活动 郭循春 跨国史视域下的1920年中日法互动与《四库全书》 刘兆轩 拉丁美洲史专论 16世纪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空间的初始解释和理由 〔委内瑞拉〕卡洛斯·阿方索·弗朗哥·希尔,姜玉妍 译 墨西哥国家历史中的前哥伦布过去和殖民地遗产 〔墨西哥〕宝拉·洛佩兹·卡瓦列罗,刘颢 译 资本家与政治家:墨西哥革命中的索诺拉领导人 〔美国〕尤尔根·布切诺,王盼 译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寻求传记的人 〔墨西哥〕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刘豪 译 拉美学界关于马克思对玻利瓦尔评价观点的辩论 韩琦 刘颢 地区国别史 肯尼迪政府、美国国内政治与核禁试问题 赵学功 党程程 二战前后日本社会的思想“转向” ——“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转向》述论 杨栋梁 史学史料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馆藏查询例解 姚百慧 博士生论坛 美国西北地区印第安战争的英国因素探析(1783~1795) 刘永浩 墨西哥实证主义教育的确立及其特点(1867~1876) 王译 书评 1910年革命前夜的墨西哥 ——读安德烈斯·莫里纳·恩里克斯《国家重大问题》 宋媛 殖民地遗产、寻求独立与新殖民主义 ——读本杰明·吉恩、凯斯·海恩斯的《拉丁美洲史》 邹扬 Abstracts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稿约 想了解更多书籍详情及购买 请保存下图,打开淘宝  策划:张思莹 原标题:《16世纪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空间的初始解释和理由》 阅读原文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