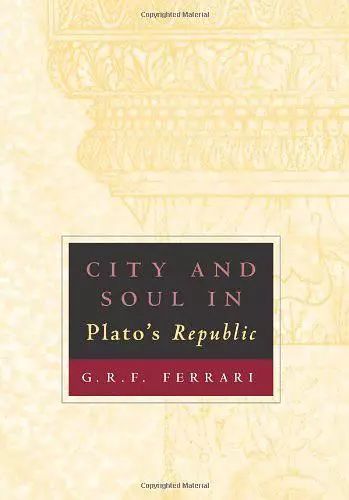| 黄俊松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柏拉图的兄弟 › 黄俊松 |
黄俊松
|
因而其次要注意苏格拉底所针对的三种男人:一是他的谈话对象,即勇敢的、颇有政治野心的雅典贵族青年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二是与那“整个城邦”相类似的那“一个男人”;三是那“整个城邦”中的成员,尤其是护卫者阶层或统治阶层中的成员,因为这是苏格拉底后面所讨论的重点。 再次,苏格拉底虽然说的是“一个男人”与“整个城邦”之间的类比,但他并没有说那“一个男人”是或不是那“整个城邦”中的一员,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提到那“一个男人”与那“整个城邦”之间有或没有因果性的、建构性的关联,因此最好首先将二者隔开,将它们并置对观。 最后,在卷二开头两兄弟的发言中,他们都倾向于将自己与大多数人、与城邦对立起来(cf.358c, 367a),但苏格拉底随即就针对他们提出了“一个男人”与“整个城邦”之间的类比,这点并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对,可见,那兄弟俩并没有只关注自己的灵魂而完全无视城邦。苏格拉底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再次将两兄弟带入城邦、带入政治,而且可以充分满足他们统治的欲望:在卷一中,色拉旭马霍斯用僭主来诱惑他们,在这里,苏格拉底马上就会用比僭主还要更荣耀的城邦缔造者来吸引他们,因为他要和他们在言辞中缔造城邦。(cf.Bloom, 1991:343) 二、含意类比与整体-部分原则: 个人与邦民 在缔造完净化的城邦后,在卷四434d—435c处,苏格拉底第二次集中阐述了类比原则,他提议将他们在城邦中所看到的正义应用到单个男人身上(434e)。至于类比是否成立的问题,他虽然表达了一阵疑惑(434e—435b),但是紧接着就颇为肯定地断言,“就正义这一形式(eidos)本身而言,正义的男人就不会与正义的城邦有任何不同,而是会与它类似”(435b)。 由于前面已经划分出城邦的三阶层及四美德,于是城邦与个人之间的类比便相应地扩展为二者之间在结构上的类比,苏格拉底说:“当城邦中三个自然阶层的成员各自关注自己的事情时,城邦就显得是正义的,而且,由于那些阶层的其它某些情感和习惯,城邦就会显得是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单个男人——其灵魂里有着那些相同的形式——由于那些与城邦里的情感相同的情感,就可以正当地要求拥有那些相同的名称”(435b—c)。 在最初引入类比时,苏格拉底并没有说类比的两端具有因果性的关联,这里的引文也是这样。但是接下来在划分灵魂三部分之前,苏格拉底却说:“除了来自城邦中的男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那些品质的”(435e),这似乎是在说,城邦与个人之间的类似是由于相互之间的因果关联,这便与最初的说法不大一样。 威廉姆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对柏拉图以及类比进行了猛烈批判。在他看来,368d以及435b处的说法其理由在于“dikaios[正义的]同时适用于城邦与人”,他将此命名为“含意类比”(analogy of meaning),而435e处的说法实际上是另一种原则,即“整体—部分原则”(the whole-part rule)。他将“整体—部分原则”和“含意类比”概括如下: (a)当且仅当城邦的人是F时,城邦才是F; (b)对城邦是F的解释,与对人是F的解释,是同一个解释(F-ness这同一个eidos[形式]适用于二者)。 (Williams,1997:51) 在他看来,这两种原则不但不能相互支撑而且还会相互冲突,如果将它们混用在一起,就会导致论证上的无意义、荒谬和后退,还会导致种种悖论。(cf. Williams,1997: 50) 比如,根据 (b),城邦的正义与人的正义一样,在于三阶层——理性的、激情的、欲望的——各自关注自己的事情,但 (a) 也同样适用于三阶层,因为那些阶层毕竟由人组成,于是便会得出,当且仅当城邦中的人是理性的、具有激情的、具有欲望的时,城邦的阶层才会是理性的、具有激情的、具有欲望的,因而,城邦中必须有欲望的人们,而且柏拉图也说这部分人占大多数,但是,一个欲望的人又的确不是正义的人,如果他不是,那么城邦的大多数人就不是正义的,这显然与前面对于城邦正义的说法相矛盾。(cf. Williams,1997: 52) 威廉姆斯的批判看似深刻,但要注意,首先,苏格拉底在435e处提及的城邦与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的“形式和品质”主要涉及到的是激情、热爱学习和热爱钱这三种,而并没有涉及到正义这种形式,可见,(a)和 (b)所适用的对象并不一样,所以柏拉图并没有混用两个原则,因而威廉姆斯所说的那种悖论就不会出现。 除了上述两种原则外,威廉姆斯还提出了一项弱于“整体-部分原则”的“主导部分原则”(the predominant section rule): (g)当且仅当主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或是占主导地位的邦民们是F时,一个城邦才是F。 (Williams,1997:53) 威廉姆斯认为,在讨论堕落的城邦形式时,柏拉图所诉诸的正是这一原则,这种原则与整体—部分原则一样,也意在强调城邦与个人之间的因果关联,而这种观点似乎也体现在苏格拉底对类比原则的最后一次阐述中。 在卷八开头,经由格劳孔的回顾,苏格拉底打算回到卷四末被打断的计划,然后说:“你知道情况必定是这样吗:有多少种形式的政制,就会有多少种形式的人之性格?还是你会认为,政制‘来自于橡树和岩石’,而不是来自于城邦中的男人们的品质?……因此,如果城邦的安排有五种,那么单个男人们的灵魂也就有五种”(544d—e)。在这里,苏格拉底似乎明确指出城邦与个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而且似乎将这种关联当成了类比的根基:政制来自于城邦中的男人们的品质,因此,有五种政制,就应有五种个人灵魂。 威廉姆斯以民主制为例再一次批判了柏拉图的荒谬。在他看来,按照主导部分原则,民主制城邦的品质应该来自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邦民的品质,因而民主制城邦就必须拥有大多数“民主型”品质的人物,但民主型品质毕竟只是一种特殊品质,而这就与柏拉图说民主制城邦拥有所有种类的品质不大协调。(cf. Williams,1997: 54—55) 不过这里依然要注意,首先,苏格拉底虽然说有五种形式的政制就应有五种形式的个人,但他并没有说某种城邦政制就一定来自于与那种城邦相对应的个人,他只是说某种城邦政制来自于那种城邦中的男人们即邦民,所以这里依然要分清两种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威廉姆斯的上述说法其实是又一次混淆了邦民与个人,因为,与民主制城邦相类似的民主型人物并不一定是民主制城邦中的邦民,与此类似,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发现:哲人并不一定在美好城邦中(cf.496b—c),僭主型人物也并不一定在僭主制城邦中(cf.575b),因而他的上述批判并不成立。 其次,要注意苏格拉底那种因果性的说法其实并没有错。因为,城邦毕竟由邦民组成,所以确实可以说政制来自于邦民的品质,而如果城邦有五种政制,那么也确实可以推出邦民也有五种;既然有五种邦民和五种城邦,那么某种邦民相对于他并不所属的城邦而言就可以称作为个人;而既然有五种邦民,那么也就可以说有五种个人。综上所述,有五种城邦就有五种个人这种说法在上述意义上能够成立,但要注意,这种说法并不是城邦-灵魂类比意义上的那种——对应的五种城邦与五种个人的说法。 Bernard Williams
三、内化与外化:邦民与城邦 上述的威廉姆斯的批判性论文影响了整整一代哲学家,不过,也有人试图将柏拉图从他的批判中拯救出来,比如李尔。李尔主要是从心理学的内化(internalization)与外化(externalization)理论出发,将类比当成是这一理论的一个附带现象,从而再次建立起了类比两端之间的关联。 在他看来,所谓内化,简单来说就是指社会给人的灵魂带进各种文化影响,那些文化影响会积淀到人的灵魂中,从而对人的心理结构产生极大的影响,柏拉图在谈到诗歌教育时所说的摹仿正是内化的一种典型手段。而所谓外化,则是指一种偿还的过程,即人会将内化于自己的文化影响又外推到社会,哲人王的例子便是外化的典型例证,因为他会按照先前内化了的神圣模型来塑造城邦,此外,诗歌等等摹仿技术的产品也都是外化的表现。(cf. Lear,1997: 63—68) 通过内化与外化理论,李尔在城邦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因果的-心理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表现为它们相互之间动态的心理交易,据此,他重新审视了城邦-灵魂类比。他认为,威廉姆斯的原则(a)仅仅只是指城邦与邦民之间的一种形式关系,这种形式关系只有通过因果的-心理的交流才能够保持,因此,“柏拉图在435e处的要点并不是说,一个激情的城邦是激情的仅仅是由于拥有激情的邦民们,而是在于拥有按照自己的想象成功塑造了城邦的激情的邦民们……,他是在说,从邦民到城邦,存在着一种外化的心理关系”(Lear,1997:69)。原则(b)与原则(a)一样,它们都“并没有给予柏拉图认为城邦与灵魂之间存在着异质同构的理由,那种异质同构依赖于柏拉图所认为的内与外之间所保持住的心理关系”(Lear,1997: 70),因而,如果将城邦与灵魂间的异质同构看作是内化与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柏拉图对类比的承诺就不会像威廉姆斯所认为的那样,会“迫使他在政治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都走向荒谬”(Lear,1997: 72)。 看得出来,李尔的策略是力图去寻求类比背后的心理学根基,通过将类比当成是其背后更深一层的内化与外化理论的一项副产品,从而避免了威廉姆斯所指出的那种荒谬。但是,他依然混淆了人的两种身份即邦民与个人。作为邦民,他当然与他所属的城邦之间有内化与外化之动态关联,但作为与城邦相类似的那个男人,柏拉图并没有说他一定属于他与之相类似的那个城邦,因而他的灵魂与那个城邦就仅仅只是类似,而无关于相互之间的内化或外化。因此,李尔虽然是在为柏拉图辩护,但是他并没有把握到柏拉图的关注所在。正如费拉里指出的,李尔的外化理论实际上只是威廉姆斯“主导部分原则”的“李尔因果版”(Ferrari, 2005:51)。 四、类比的机制与运用 通过考察苏格拉底对于类比原则的阐述,以及通过澄清威廉姆斯和李尔对于类比原则的误解,我们目前倾向的结论主要是:在类比问题上,关键是要区分出人的两种身份,即邦民与个人;在邦民与城邦的关系上,无论威廉姆斯的整体-部分原则或主导部分原则,还是李尔的内化和外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依然适用;但是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上,他们的理论则并不适用,因为在柏拉图的描述中,类比的两端并没有塑造与被塑造的关联。 既然类比的两端并没有建构性的、因果性的关联,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它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联?对此,笔者将借助费拉里对于类比问题的论述来阐明类比的机制以及苏格拉底使用类比的修辞目的。 费拉里并没有像威廉姆斯那样诉诸于单纯的语义原则来寻找柏拉图的悖谬之处,也没有像李尔那样诉诸于某种心理学理论来为柏拉图辩护,而是追溯到古代的修辞理论。他主要是运用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说法,认为那种类比式对应的核心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称作的“比例性的隐喻”,这种隐喻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可以转换的”,也就是具有可逆性。比如,我们可以将青年比作城邦的春天,但也可以将春天比作一年中的青年,(cf. Ferrari,2005: 61)用在城邦—灵魂的例子上,那么自然就可以得出,如果说理性是灵魂的统治者,那么也可以说统治者是城邦的理性。 费拉里将这种作为比例性隐喻的类比的特征概括为:“他探究的形式不是初次看上去的那样:不仅X(一个人),而且Y (社会),都可能被描述为Z(正义的),……更确切地说,它变成了A:B::C:D,A和B是社会的成分,C和D是个人灵魂的成分,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正义,那么我们必须要审查的就是那一比例本身;此外,社会中A之于B以及灵魂中C之于D的这种关系,结果将会是等级制的。”(Ferrari, 2005:40) 藉此可以发现:第一,虽然类比的两端并无因果性的关联,但是通过比例性隐喻的可互换性或可逆性,类比的两端之间依然可以建立起某种修辞性的关联;第二,类比的重心在于城邦各阶层之等级结构与灵魂各部分之等级结构之间的对应,也就是在于城邦政制与灵魂政制之间的对应,政制(politeia)是类比对应的核心,而它也正是《理想国》(Politeia)的标题;第三,那种等级制结构自然会带出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那兄弟俩的情结所在。 费拉里有力论证了类比的性质与特征,指出了类比起作用的机制,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指明了苏格拉底在对那种比例性类比的使用上存在着一种不对称,而那种不对称的使用恰是苏格拉底故意为之,其目的是为了引导那兄弟俩。 他指出,虽然那种比例性的类比具有可互换性,即,可以说理性是灵魂的统治者,也可以说统治者是城邦的理性,但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城邦的统治阶层从不被称作是城邦的理性,而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则常常被称作是灵魂的统治者。(cf. Ferrari,2005: 86)费拉里认为,从这种偏向可以看出,柏拉图更为关注灵魂政治,也就是更为关注个人,通过这种不对称的使用,柏拉图将类比的隐喻性力量完全集中到了个人灵魂上(cf. Ferrari,2005: 88—90),而这,也恰恰针对着那兄弟俩对于灵魂的关注。 本文参考文献:Ferrari,G. R. F.,2005,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书影
五、类比之外:哲人王与僭主 以上借助费拉里的论述澄清了类比的机制与作用,并且指出了柏拉图 (苏格拉底)对于类比的使用有其针对性的修辞特征或引导特征,但同时要注意,虽然城邦与灵魂之间的对应确实是类比性的,但这并没有否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因果性的,因而当类比性的城邦与灵魂之关系和因果性的城邦与灵魂之关系合二为一时,就得尤为小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情况。 如果通观“城邦—灵魂类比”,那么可以看出,按照诸成分之结构的不同,这一类比主要涉及到了五种对应:美好城邦——哲人、荣誉制城邦——荣誉型人物、寡头制城邦——寡头型人物、民主制城邦——民主型人物、僭主制城邦——僭主型人物。柏拉图对各种城邦的描述当然会涉及到各种城邦中的统治阶层,它们依次是:哲人王、荣誉制城邦中的统治阶层、寡头制城邦中的统治阶层、民主制城邦中的统治阶层、僭主。在这五种统治者中,中间三个包含有不止一人,即使柏拉图描述的是那三种统治阶层中的个人,他也是在强调以那个人为代表的整个阶层的品味(cf. Ferrari,2005: 65—75),因而我们比较容易地就能将那三种城邦中的统治者与那三种城邦所对应的个人区别开来。 但是到了哲人王与成为了实际僭主的僭主型人物的例子上(为行文方便,下面将“成为了实际僭主的僭主型人物”简称为“僭主”),情况则比较复杂:作为城邦中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单个人,其身份是邦民;但由于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哲人王也是哲人,僭主也是僭主型人物,因而他们也可以作为与他们所统治的城邦相对应的那种人,其身份是个人;如此一来,哲人王与僭主就集邦民与个人这双重身份于一身,因而上文所区分的个人与城邦之间的类比关系和邦民与城邦之间的因果关系就难解难分,而且很容易就会让人认为类比性来源于因果性,而这就又回到了威廉姆斯的主导部分原则和李尔的外化原则。 不过依然要注意,在哲人王与僭主的例子上,苏格拉底着重的依然是个人与城邦之间的类比性关系,他对二者之间的因果性关系其实有所保留,而且如果细查文本,就会发现因果性关系仅仅只是个特例(cf. Ferrari,2005: 85),它不但不是类比性关系的根基,而且通过类比性关系,恰恰可以发现苏格拉底为何对因果性关系有所保留。 先来看看哲人王的情况。首先,由于哲人王是哲人,作为哲人,也就是作为与美好城邦相对应的那种人,他的身份是个人,在这种意义上,他和美好城邦的关系就和其它四种类型之人与相应的四种城邦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类比性的关系。又由于在柏拉图的描述中,除了美好城邦中的哲人王之外,在其它劣于美好城邦的城邦中,哲人也依旧存在(496b—e),这也就是说,哲人不一定都是美好城邦中的一员,因而当然也就更不一定是美好城邦中的统治者,而这种哲人要成为统治者,就得端赖于“政治权力与哲学巧合一致”的那种运气或偶然(473c—d)。因此,作为个人的哲人王与哲人一样,他们二者与美好城邦的类比性关系并不是由于他们与美好城邦之间的因果性关系。 其次,由于哲人王也是美好城邦中的统治者,作为统治者,他的身份是邦民,在这种意义上,他与美好城邦的关系就是因果性的。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威廉姆斯的主导部分原则确实可以适用,但李尔的外化原则却并不适用(cf. Ferrari,2005: 100),因为哲人王是按照天上的、神圣的模型来塑造自己与城邦(cf.484c, 500d, 501b),而不是将美好城邦的文化内化后再外推到城邦。 最后要注意,作为邦民,哲人王的正义在于“关注他自己的事情”(cf.434c),也就是统治城邦;但作为个人,他的正义却在于他的灵魂政制应该类似于他所统治的城邦的政制,如果按照上文所论述的那种作为比例性隐喻之类比的可转换性,那么其关键就在于他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应该是他灵魂的统治者。但是,哲人 (王) 灵魂中的理性(phronēsis),⑤其最高的目的却不是统治,而是超越了统治,指向了神圣的、永恒的事物(518e, 590d)。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好城邦是最正义的城邦,但是哲人(王)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却使得他向往着神圣的沉思生活或哲学生活,使得他蔑视政治官职和统治权力(521b),使得他在活着时就已住进福岛(540b),而且这会给他带来“最真实的快乐”(586d)。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哲人王的例子上,虽然主导部分原则在起作用,但那不是因为哲人王完全心甘情愿,他只是迫于某种必然,是城邦的律法迫使他挑起统治的重担,统治城邦对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520e),因为他是由城邦所培养,接受统治任务是为了报答城邦的养育、教育之恩(520b—c),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正义就是欠债还债(331e),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卷二开头“大多数人的意见”所认为的苦差(357d—358a)。 因此,对于哲人 (王) 而言,最好的生活是哲学生活,而非统治城邦。统治城邦要么是由于偶然的巧合,要么是迫于律法上的必然,而并非他自身的“内圣”所自然带来,因此,他的“内圣”并不必然开出“外王”,他的“内圣”要高于“外王”。对于哲人 (王) 而言,“外王”与其说是对他的“内圣”的一种奖赏或报酬,倒还不如说是对它的一种惩罚(对照卷一中对最好之人的报酬是惩罚那一说法,cf.347a ff.)。 再来看看僭主的例子。与哲人王的情况一样,僭主也是集邦民与个人这双重身份于一身。作为个人,他是僭主型人物,在这种意义上,他和僭主制城邦的关系就和其它四种类型之人与相应的四种城邦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类比性的关系。又由于在柏拉图的描述中,除了僭主制城邦中的僭主之外,在其它种类的城邦中,僭主型人物也依然存在(575b),这也就是说,僭主型人物不一定都是僭主制城邦中的一员,因而当然也就更不一定是僭主制城邦中的统治者,而这种僭主型人物要成为统治者,就得端赖于某种偶然或运气 (cf.579c),“运气迫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僭主”,“迫使”表明他或许与哲人王一样,是迫于某种必然而掌权)。因此,作为个人的僭主与僭主型人物一样,他们二者与僭主制城邦的类比性关系并不是由于他们与僭主制城邦之间的因果性关系。 其次,由于僭主也是僭主制城邦中的统治者,作为统治者,他的身份是邦民,在这种意义上,他与僭主制城邦的关系就是因果性的、建构性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李尔的外化原则并不适用于哲人王,但却适用于僭主,因为僭主作为僭主型人物是一个自然的外化者(cf.Ferrari, 2005:96)。 这里让我们稍微对照一下哲人王与僭主。⑦表面看来,二者具有某些类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生活都与战争有关(cf.543a, 567a),他们都有违背律法习俗的危险性(cf.537e—538c, 569b—c, 575d),他们都是充满爱欲之人(cf.499c, 573a—e)……。但是由于二者在“灵魂转向的技术”(cf.518d)方面的巨大差别,于是一个转到了最好的方面,另一个则转到了最坏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哲人王对哲学充满的爱欲激情将他带到了超越于整个人类事务之上的神圣境地(cf.490b, 517c, 519c),而僭主的爱欲则使得他不断的超出自身而侵入到整个城邦世界(cf.573d—575a),他会将自己的灵魂政制外化到他所统治的城邦上。 最后要注意,在僭主的例子上,虽说个人与城邦之间的类比性与因果性并无关联,但正是通过类比性,即僭主型人物的灵魂政制与僭主制城邦的政制之间的类似,可以发现,成为了实际僭主的僭主型人物其外化的野心实际上也在作用于其自身,外表上看他是在奴役城邦,但通过类比,就会看到他的灵魂如同城邦一样被奴役着,处在一种最悲惨的境地(cf.579d—e),因而他所施行的外化其实是一种最糟糕的外化。 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
六、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城邦与个人的五种对应上,单纯类比性的机制一直存在,但在五种对应的两端即哲人王和僭主的例子上,苏格拉底又加上了类比机制之外的因果机制。不过,那两种因果机制在类比机制的反观下却昭示了政治权力或统治生活的不完美:在僭主的例子上,可以看到,灵魂政制很糟糕的人如果运气让他获得权力,其后果是害己害城邦;在哲人王的例子上,可以看到,灵魂政制很完美的人如果由于某种偶然或迫于某种必然而获得权力,其后果对城邦来说虽然很好,但对他个人来说却并不好(对照卷一中所说“有识之士”认为统治是麻烦事,不利于自己利益, cf.347d),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牺牲哲学生活。 因此,在这两个例子上,都显示出了“外王”的局限,都展示出了“内圣”的优先性,而这对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两兄弟来说,一方面与他们在卷二中对于灵魂正义的欲求相符,因为这里强调了个人灵魂,但另一方面又与他们统治城邦的欲求不符,因为这里从根本上就贬低了统治。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哲人王的例子,在卷二开头,那兄弟俩依然与城邦保持着对抗,但在这里,哲学与王权又结合了起来,而哲学又高于王权,因此,这种既调和又超越的安排就足以治愈他们的政治野心并将他们引向哲学生活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柏拉图,1986,《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2]Adam,J.,1938,The Republic of Plato,2 v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Bloom,A.,1991,The Republic of Plato,BasicBooks. [4]Blössner,N.,2007,“The City-Soul Analogy”,in G. R. F. Ferrar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Ferrari,G. R. F.,2005,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Lear,J.,1997,“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public”,in Richard Kraut,ed.,Plato's Republic: Critical Essay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7]Strauss,L.,1964,The City and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Williams,B.,1997,“The Analogy of 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in Richard Kraut,ed.,Plato's Republic: Critical Essay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注释 ①参见368d-369a;434d-435c;544d-e, 另参见445c-d以及543c-544a;其它提及的地方有:441c, 498e, 576c, 580d。本文的《理想国》引文均系笔者所译, 引用时注明斯蒂芬页码, 希腊文原文参照亚当的编本 (Adam, 1938) , 英译本参考布鲁姆译本 (Bloom, 1991) , 中译本参考郭斌和、张竹明译本 (柏拉图, 1986) 。 ②在本文中, 笔者并不打算探讨类比问题的所有层面, 而只集中在类比的机制与作用这一问题上, 有关类比问题较为全面的概括, 可参见布略斯那的研究。 (cf.Blössner, 2007:345-384) ③在卷二开头两兄弟的发言中, 表面上看来, 他们只关注灵魂正义的问题 (cf.358b, 366e, 367e) , 但是如果结合《理想国》开场背景以及对话过程中两兄弟的表现来看, 就会发现统治城邦依然是他们的关切所在, 参见施特劳斯和费拉里的研究。 (cf.Strauss, 1964:62-65;Ferrari, 2005:11-15) ④虽然苏格拉底在卷五中描述了女护卫者, 但是那里的女人是指城邦中的女人, 苏格拉底从没有说过一个女人和整个城邦之间的类比。 ⑤这里的“理性” (phronēsis, 或译“明智”) 不同于卷四灵魂三分中的“理性” (logistikon, 或译“算计”) , “logistikon”仅仅负责照管灵魂整体 (441e) , 它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欲求对象, 而这里的“phronēsis”则指向神圣的事物。 ⑥在这个意义上, 个人正义就要多于城邦正义, 而并不像苏格拉底起初所说的“或许在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 (368e) 。 ⑦鉴于他们的双重身份, 因而苏格拉底对哲人与僭主型人物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他们。 编辑排版:刘曼婷 审核发布:董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