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凯歌《妖猫传》:文化多元下的盛世想象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极乐之宴是否存在于历史 › 陈凯歌《妖猫传》:文化多元下的盛世想象 |
陈凯歌《妖猫传》:文化多元下的盛世想象
|
演员的选择让这部电影染上强烈的外部观察视角 然而,在想象、虚构和补充过程之中,其本身超过了历史剧的界限,又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戏说性质。尽管《妖猫传》的电影基于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演绎,然而其故事的演绎却远远溢出了历史剧之外,奇幻/侦探因素的引入使得影片增添了一份戏说的意味。这同电影所改变的文学文本相关,电影改编自和陈凯歌年岁相仿的日本奇幻小说家梦枕貘的同名小说。
日本作家梦枕貘此前作品《阴阳师》及其游戏改编是国内读者最为熟悉的 事实上,《妖猫传》的原著在日本文学传统中属于“怪谈”系列。作为日本传统社会的文艺形态,怪谈之中存在异态与常态之间转化、切换的方法和认识。原著《猫妖传》之中展现的是日本作者对中国曾经唐朝盛世的想象,表达的是日本文化之中的唐朝情结与中国情结。唐朝作为中日历史关系想象的“蜜月期”,中日之间交往非常频繁,然而,“怪谈”这一类型所携带的“奇幻”使得这样的想象充满了某种对盛唐时期的中国的“异化”。
空海与白居易组成了唐朝版的“福尔摩斯” 对陈凯歌而言,这个日本故事给他提供了想象唐朝的空间。在一次采访中,陈凯歌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健康的一个时代,文化昌盛,天真浪漫,而且非常包容。这个电影从设计上讲有很多幻想的、甚至是狂想的美。”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选择原本漏洞百出的原著:这种奇幻而残缺不全的故事给他的表达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编剧王慧玲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诸多手术,方才为陈凯歌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故事框架。不同原著的地方是,电影叙事中将空海的队友全删减了,只是和白乐天组成“国际化”的“侦探搭档”。这种中日“侦探搭档”本身构成了一种叙事的“奇观”:空海是精通鬼怪幻术的“技术专家”,尽管故事之中是行动的主体但充其量只是保镖与密码的解码者;而担任起居郎的白乐天,尽管在面对幻术时在行动层面是无力,然而才情与对真相的执着才是真正文明的象征与代表。
极乐之宴的华丽场景对于熟悉陈凯歌电影的观众并不陌生 在《妖猫传》之中,陈凯歌证明他对盛世的奇观呈现能力,同时怪谈本身的奇幻性质使得他能够放开身手来表现大唐盛世的“极乐之宴”。“极乐之宴”中,阿部仲麻吕敬仰大唐的文明,也目睹了放荡形骸的李白让高力士脱靴撰写《清平乐》,见到了唐玄宗向世人大度展现的杨贵妃以及自己披头散发狂癫击鼓。正是这样的文明,容纳了万邦来朝。
诗人李白在电影中的狂放不羁,也在时代缩影 作为重要的叙事线索阿部仲麻吕,虽为日本人,然而在唐朝任高官,见证了唐朝的繁盛与开放。他曾两度意欲向杨贵妃表白,然而第一次未曾说出口,唐玄宗就强行挽着杨贵妃,强调:“贵妃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大唐盛世的象征与皇帝的拥有物;第二次则是一度提议将杨贵妃护送到日本,然而遭拒后依然未能说出。这些是通过来自日本的“他者”阿部仲麻吕的日记展现的。连同后来通过曾经“白鹤少年”的幻术见证曾经的“大唐盛世”的空海,均是一个反身关照大唐盛世的“他者”。相对于阿部仲麻吕的内化的“他者”观照,空海则提供的是另外的一种“外在性”的观照,更为冷静与超然。在这种一切皆空幻之中,陈凯歌以历史剧与戏说之间暧昧言说的方式来借用日本人的“他者”想象表达了他对大唐盛世的想象。
演员阿部宽总是自带一种落寞中年人的气质 问题在于,借助怪谈本身的奇幻性质使得陈凯歌能够放开身手来表现大唐盛世的“极乐之宴”的奇观,但同时浓郁的日本文化底色使得真正的中国故事无法展开:中国电影叙事工业还没有达到好莱坞那种能够将异域故事转变成为美国梦故事的能力。被显现的大唐盛世依然只是“他者”的,而不是中国自己的。
爱情残酷物语中的大唐 《妖猫传》讲述的故事并不新鲜。如果剥掉电影之中文本套层结构、奇幻叙事部分,那么电影《妖猫传》表达的正是某种独特的爱情残酷物语。这种爱情残酷物语,本身是根植在今天的“青春电影”与对青春的想象之中的。只不过,陈凯歌使用的是“陌生化”与历史化的方式,安置在唐朝来讲述特殊的帝妃之恋罢了。片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也并不是垂暮之年老态龙钟,而是与大唐盛世相匹配的芳华正茂的形象。
中法混血的演员饰演杨贵妃,呈现唐文化的多元混杂性 《猫妖传》将质询的目光放在李隆基与杨贵妃帝妃的旷世之爱上。陈凯歌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帝妃的倾世之恋的“元故事”,提供的是流传至今的白居易《长恨歌》与正史之外的版本。故事随着白乐天与空海两位中唐的“侦探”介入到妖猫事件调查的深入,所谓“真相”在剥洋葱过程中一层层被打开。这种侦探加奇幻的文本结构,本身是一种后现代阐释的狂欢。妖猫在叙事中发挥着串联故事情节的作用。
尽管电影中,仰慕大唐风采的空海是妖猫密码的不断破解者,然而陈凯歌却将情感放置在白乐天身上,并试图通过白乐天来寄托某种文明的思考。帝妃的旷世之恋的真相,对白乐天而言其重要性在于他花费了多年心血写作,生活在深重的“文本之恋”中:他多年在宫中担任皇帝的起居郎,为的是寻找盛唐的真实感与触碰历史的可能;他关心李隆基与杨贵妃之恋,生活在一个墙上贴满杨贵妃画像的空间之中亦癫亦狂;他能够为了寻找到秘密,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犯禁。
这种“文本之恋”,使得他能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电影之中以极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雪中单衣萧瑟表现出来。正是这种“文本之恋”,使得帝妃之恋的真相对白乐天有格外重要意义,也是妖猫要将他带进来的原因所在。当真相大白后,空海继续寻道,而白乐天则在“一字不改”之后获得了超脱。在白乐天这个形象上能看出《霸王别姬》(1993)之中程蝶衣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影子。或许,这其中也有近年来陈凯歌不断遭到质疑后的夫子自道意味。
但在阿部仲麻吕的视角中,杨贵妃只是唐玄宗的“物”,只是大唐盛世的装点,因而当盛世转入危机,面临安禄山作乱有抢走杨贵妃的危机之际,杨贵妃只能死,而且必须死。幻术大师提供假死脱身的“尸解大法”,只不过是提供一个合理赐死杨贵妃的方式,让唐玄宗从负疚感之中解脱出来。在这种骨感的“真相”面前,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白乐天最后没有修改最初的《长恨歌》。这种对真相追寻到最后功亏一篑的犬儒姿态,充满了某种历史终结论的论调。 以幻术来理解唐朝盛衰 当陈凯歌将日本的怪谈小说《妖猫传》作为他讲述大唐盛世的框架结构的时候,他可能没意识到,他客观上完成了一部具有“元电影”意味的作品。幻术本身具备某种电影的性质:其创造一种情境,让人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这种幻术的特征和电影“造梦”特点不谋而合。正是这种幻术与电影“造梦”之间的这种同构性,使得曾经扑朔迷离的历史有了讲述空间。
白鹤少年身上的幻术场景令人惊叹 影片中,幻术是妖猫的能力,也是黄鹤师徒的能力,更是最后造成葬送杨贵妃的关键。相对于原著怪谈式对于杨贵妃的结局安排,恰恰是陈凯歌电影的处理,更能体现一种盛世的失落与悲剧所在:盛世之际,李隆基打造极尽奢华的极乐之宴,就是要让世人看到大唐盛世的繁华,看到杨贵妃的美,并不惜亲自披头散发狂癫击鼓同安禄山虚与委蛇;一旦盛极而衰之际,又不得不将曾经盛世象征的杨贵妃作为替罪羊。
长安繁华梦 如果历史真实中的杨贵妃之死是扑朔迷离的话,那么作为“奇幻”类型的《妖猫传》,与影片中的猫本身就构成了这一段历史真相的悬置。所以说,影片结局中的“猫”必须死,因为只有“猫”死才能达到历史中的真实。这正是《妖猫传》试图达到的:它与好莱坞叙事套路之中妖猫不能死形成了截然对立。这也是最后陈凯歌毅然在电影之中“杀”掉它的原因所在:只有将这种异质的幽灵消除掉,才能更好言说大唐盛世;白居易才能一字不改《长恨歌》;空海才能求经遇到已经化身为得道高僧的丹龙。问题在于,一旦这种异质性的幽灵真正消灭掉了,历史就顺理成章了吗?陈凯歌没回答,答案在风中飘荡。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
【本文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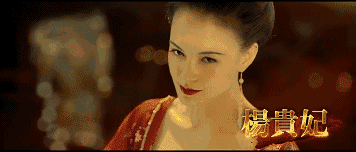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