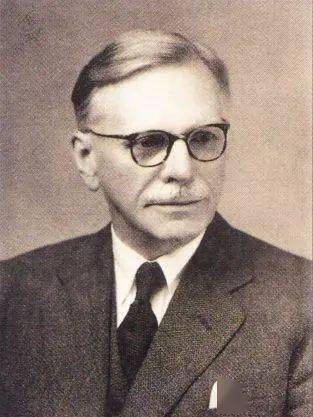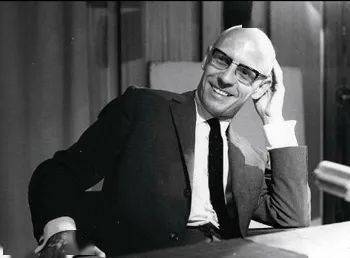| 话语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政治的各种定义 › 话语 |
话语
|
索绪尔 但对索绪尔来说,对于发展一个关于话语的语言学理论之可能性来说,存在着诸种严格的限制。从一个索绪尔主义的观点来看,话语是任何比句子更为扩展的语言序列。现在,在一个索绪尔主义的观点中,一种关于话语的语言学是不可能的,因为由多个句子组成的序列,仅仅是受说话者一时的想法所控制,并未呈现出任何为一种一般理论所能掌握的结构性的规律。伴随着这一笛卡尔主义的关于主体之全能性的论断,一种关于话语的语言学理论之可能性便被排除出去了。此外,索绪尔主义的符号理论最终并不协调一致,因为如果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如果在能指的秩序与所指的秩序之间存在着一个严格的对应性,那么(从一个形式的观点来看),这两个秩序是不能区分彼此的,语言学符号的二元性也便无法保持了。这样,索绪尔不得不悄悄地再次引入关于声音性实体与概念性实体之间的区分,其结果便是使结构分析更紧密地同语言学符号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含糊地宣布了一门符号学的可能性——作为在社会中的一门关于各种符号的一般科学,但他对于各种语言实体的依赖,使得这一对诸种结构性原则的各应用领域的扩展,变得相当困难。 只有通过哥本哈根的语符学学派(glossematic school),索绪尔主义的这些内部不一致才得到了妥当处理。其结果便是关于结构语言学的第二种模型的一个表述;这第二种模型明显地在一个不断增长中的形式主义的方向上前进。通过把能指的秩序与所指的秩序再划分成比符号更小的单位,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打破了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关系的对应性观念[2]: 音素学家们……已经发现诸种比符号更小的语言单位:各种音素(phonemes)……(符号calf[小牛]由三个音素k/ae/ 和f/ 组成)。适用于内容(content)的同一方法,使得在同一符号中可以区分出至少三个元素……或语素(semes)……牛的/公的/年轻的。因此现在,各种语义的和语音的单位显然可以从形式的观点加以区分:有关一个语言的各种音素的诸种组合法则,和那些适用于各种语素的诸种组合法则,无法被表明为是一一对应的……[3] 若是考虑到一种关于话语的理论,这个朝向形式主义迈进的趋势的诸种后果,乃是意义深远。那些主要的后果如下: # 1 如果那控制各元素之间的组合与替代的诸种形式规则的抽象系统,不再必然同任何特定的实体相连,那么社会中的任何符号指向系统(signifying system)——比如,食物代码、家具、时尚,等等——都可以用这个系统来进行描述。这是符号学自1960年代以降的发展方向,其始自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诸种先驱性研究。[4]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话语”并不是指一系列特定的对象,而是指一个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重新描述社会生活的总体是可能的。 # 2 如果形式主义严格适用,这意味着,语言的(the linguistic)与非语言的(the non-linguistic)之间的诸种实质性差异,也必须被抛弃。换句话说,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区分成为了在关于各种有意义的总体(meaningful totalities)的更广阔的范畴中的一个次要区分。拉克劳和穆芙(Mouffe)特别强调了这点。[5]它使得了话语理论接近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后期研究所得出的诸种结论,比方说以下这个概念:各种“语言游戏”同时包含了语言与各种行动,语言交织在各种行动中。[6] # 3 最后,严格的形式主义还使得克服另一个障碍——它妨碍了一种关于话语的语言学理论的表述——成为可能:当所有的区分不得不被认为仅仅是差异性的——比如,内在于结构——那么主体就不能再被认为是意义的来源,而只是一个有意义的总体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主体之死”,曾是古典的结构主义的战斗口号之一。说话者将多个句子组织在一起的方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主体的各种一时想法的表达,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制度被结构化的方式,取决于在一些语境下什么是“可说的”,等等。对古典的结构主义来说,话语分析的任务乃是揭示这些在社会生活中控制意义生产的基本规律。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个规划乃是通过把不同学科的各种贡献放在一起而贯彻落实的。这些学科包括:论证理论(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阐述理论(the theory of enunciation)、言语-行动理论(speech-act theory)、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等。 近年来,结构主义传统在各种不同的面向上经历了一系列的重新表述,从而迎来了一个可以被称作是后结构主义的时刻。这些修正的共同特征便是,质疑了作为古典结构主义之基石的关于封闭的总体(closed totality)的概念。(如果各种认同是一个话语系统中的唯一差异,那么没有一种认同可以被完全地构建,除非该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从构建一个封闭系统之逻辑不可能性上,可以得出一种关于各话语性认同(discursive identities)的颠覆逻辑(logic of subversion)。后结构主义思潮正是将这种颠覆逻辑付诸实验。这一思潮中的主要潮流如下: # 1 对罗兰•巴特后期作品中的关于意义的逻辑(logic of meaning)的再表述。[7]尽管在其早期的诸种符号学作品中,巴特相信在外延的意义和内涵的意义之间的一种严格差异,但他后来意识到,无法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任何一种严格的差异。这便引出了关于一个多元文本(plural text)的概念:多元文本的各种能指不能永恒地同各种特定的所指相连。 # 2 能指与所指之关系的相似的松动,出现在受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启发的精神分析的潮流中。[8]通过对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之过程(凝缩与置换)——它介入了所有心理构型(psychical formations)之构建——的强调,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已表明,通过能指与所指间的严格的相互关联来固定意义,乃是不可能的。这个趋势被拉康主义理论——通过那被称作为能指的逻辑(logic of the signifier),即在能指之下的所指的永恒的滑动(能指正变成为稳定的元素)——而被激进化了。 # 3 最后,始自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运动[9],试图(用与哥德尔[Gdel]定律并无不同的方式)表明在所有结构性的安排中,均可以发现各种极端的不可确定性(undecidability)的元素,以及如何任何一种符号指向的结构(structure of signification),均不能够在自身中找到关于它自己的封闭(closure)的原则。因而,它的封闭需要某一向度的力量来进行操作,这一力量必须是来自于结构的外部。
福柯 在米歇尔•福柯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一种全然不同的路径,其通向一种被他称为关于各类“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s)的理论。尽管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始于符号的逻辑以及——一旦不能获得关于总体性封闭的各种条件/状况——它的颠覆,福柯的起步点却是一种第二层级的现象学(second-level phenomenology),试图将各种总体(totalities)——任何关于意义的生产正是在这些总体中发生——隔离开来。通过将各种陈述与任何外在现实的参照括置起来的方式,古典的现象学专注于各种陈述的意义。通过表明意义本身预先假设了各种生产的条件/状况(这些意义的生产条件/状况本身不能简化为意义),福柯继续进行了一种第二层的括置(second bracketing)。这一“准先验的”举动,在现象界中隔离出了一个被福柯称作为话语的层面。在福柯的分析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要确定什么构建了一个话语构型的统一性、以及什么构建了它的连贯性原则。对福柯来说,任何话语的最小单位,乃是陈述(énoncé)。一个陈述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命题(proposition),因为同一个命题能够包含有两种不同的陈述(我和一个医生都能说某人得了癌症,但只有后者的命题能够被认为是一个医疗性的陈述)。它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个言说(utterance),因为不同的言说能够包含相同的陈述。最后,各种陈述不能被认为是各种言语-行动,因为前者被福柯局限为他所说的“严肃的言语-行为”——那些不平凡的、非日常的言语-行动,但却是通过一个权威性的或自主性的活动所构建(如医疗话语)。不过,这只是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论述同一个问题:什么构建了一个特殊的话语场域或话语构型的统一性的原则?福柯一度想在他所说的一种认识型(episteme)中,来寻找这个统一性原则。认识型是将在某一时代内的思想生产统合起来的一个基本的轮廓。“我们用认识型来指……把在一个给定时期内的各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整合起来的各种关系的一个总体性的集合。这些话语实践引发了各种认识论的观点、各种科学、以及可能被形式化的各种系统。”[10]在这个意义上,他试图将各个时代的各种基本的认识型隔离开来;对于这些被隔离开来的不同时代的认识型,他曾分别称之为(大写的)文艺复兴、古典时代与现代性。[11]揭示这些基本的话语策略的思想操作,就是他所说的考古学(archeology)。但他思想的主要趋向使他越来越意识到,一个话语构型的异质性不能被简化为这样一种简单的统一性原则。因此他总结道,在对于同一对象的参照中、或在诸种陈述的生产中的一种共同风格中、或在各种概念的恒定性中、或在对于一个共同主题的参照中,一个话语构型的统一性原则是无法被找到的;而只有在他所称之为的“弥散中的规律”(regularity in dispersion)中,一个话语构型的统一性原则才能被找到。这种弥散中的规律,乃是指在各元素(这些元素并不遵守与支持结构化的本质原则)之间的各种外部关系中的恒定性。然而,如果弥散中的规律是一个话语构型唯一的统一性原则,那么仍有待解决的是各种话语构型间的各类界线的问题。在这个阶段,福柯对这个问题不能够提供任何精确的解答。 02 话语理论和政治 迄今为止,话语理论对政治领域的各种主要贡献,都同权力的概念化联系在一起。先前所指出的同一种广泛区分(即指分别以广义的后结构主义与福柯为代表的两种路径——译者注),也适用于此处:一方面,我们拥有着在理论上扎根于后结构主义之符号理论的分析师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拥有着那些主要同福柯后期作品相联系的分析师们,他们致力于对福柯的思想方案进行重新表述。
拉克劳、穆芙 前一趋向在拉克劳与穆芙的作品中尤其可见。[12]在他们关于一种以领导权(hegemony)之范畴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的路径之表述中,后结构主义传统的两个方面十分重要。第一个是这样一种关于“话语”的概念:“话语”作为超越语言的和语言之外的(the extra-linguistic)这一区分的一个有意义的总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封闭的总体之不可能性,切断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中充斥着各种“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政治性的竞争可被视为各种对立的政治力量把那些能指,部分性地固定到诸种特殊的符号指向的构造(signifying configurations)的各种努力。例如,关于固定一个能指(如“民主”)之意义的各种方式的诸种话语斗争(discursive struggles),对解释我们当代政治世界的政治语义学来说至关重要。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的部分性的固定,就是这些作品中所说的“领导权”。后结构主义贡献给一个关于领导权的理论的第二个方面,乃和第一个方面紧密相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解构(deconstruction)显示了,在结构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各种各样可能的关联,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确定的。不过,由于一个构造而不是另一些可能的构造已经被确实化,因此:(1)这个实际存在着的构造,本质上是偶然的;(2)它不能被结构本身所解释,但可以被一个必须是部分性地外在于结构的力量所解释。这是一个领导权的力量(hegemonic force)所扮演的角色。“领导权”是一个关于在某一不可确定的地带中作出各种决定的理论。结论是,正如解构所显示的,由于不可确定性在社会的基层进行操作,客观性和权力变得彼此不可区分了。正是根据这些论述,已有人指出道:权力是在结构之内的偶然性的痕迹。[13]拉克劳和穆芙描述了一个从第二国际到葛兰西(Gramsci)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为对各种社会系链(social links)的偶然性特征的一个逐步的认可,这种偶然性特征先前被认为是根植于(大写的)历史的诸种法则中。这些已经取得的扩展,总是进一步地深化了各种领导权系链(hegemonic links)的操作性的领域。
齐泽克 最近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努力,那是由斯拉沃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作出的。[14]通过结合拉康主义的精神分析、黑格尔主义哲学、以及在分析哲学中的一些思潮,尤其是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反描述主义,齐泽克把话语理论扩展到政治分析的领域。齐泽克的路径的核心方面,便是他在不带有任何本质主义的含义下,再次引入主体的范畴的努力。他的“主体”不是现代性的哲学传统中的实质性的我思(cogito),但也不是结构主义所假定的各种主体位置(subjective positions)的弥散,而是——追随拉康——一个属于缺乏(the lack)的地方,是各种各样认同化(identification)的努力所试图填补的一个空白的地方。齐泽克表明了在任何认同化(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复杂性,并尝试在这个基础上解释各种政治认同的构建。 福柯后期的作品[15],是为处理他关于各种话语构型的分析所引致的诸种困难而作出的一个努力。福柯把话语的王国定义为仅仅是在众多对象中间的一个。同陈述相关联的、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话语,明显地同其它的分析对象区分了开来:各种话语规律并未横跨语言的与非语言的之间的诸种界线。结果便是,某些话语构造的在场,对于他来说,必须用语言之外的术语来解释。这便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路径,他将其称之为谱系学(genealogy)。当考古学预先假定了一个话语场域的统一性(其不能诉诸于任何更深的统一化的原则),谱系学则试图把各种参与一个话语构造的元素在一个非连续的历史框构中进行定位。这一非连续的历史中的各种元素,并没有任何关于目的论的统一性的原则。在各种元素的谱系学的弥散(genealogical dispersion)背后,各种统一化的力量的外部特征是以福柯主义的权力观念为基础的: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各种元素是非连续的。我们无法从这些元素本身出发,去解释它们的互相关联。因此,虽然后结构主义和谱系学均处理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的问题、以及处理非连续性从各种未缝合的认同中的产生,但它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非连续性的:前者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话语的范畴扩展到这样一个点上,在该点上,话语将包含它的激进他者(radical other)。换言之,问题是这样的:如何来显示出一种差异的逻辑(logic of difference)所起着的作用,这种差异的逻辑横跨了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之间的任何区分。而后者则是要去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各种语言的规律是如何依赖于被放置在一起的各种元素,这些元素只有用各种非话语的术语才能被思考。 - 注 释 - [1] F.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C. Bailey and A. Sechehay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2] L. 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 F. A. Whitefie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Hjelmslev,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rans. F. A. Whitefie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3] O. Ducrot and T. Todorov,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ag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2. [4] R.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 A. Laves and C. Smith (New York: Hill and Wong, 1968); Barthes, Mythologies, trans. A. Laves (London: Cape, 1972); Barthes, The Fation System, trans. M. Ward and R.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ong, 1983). 也可参见J. Kristeva, Semeiotik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9). [5] 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6] 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d: Blackwell, 1983), p.5. [7] Barthes, S/Z,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4). [8] J.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1977). [9] J.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 C. Spivak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R. Gasché, The Tain of the Mirro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1972), p.191. [11]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1973). [12]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1990). [13]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14] S.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L Verso, 1989). [15]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Vintage, 1979);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1980. (图片来自网络) 新浪微博账号: 实践与文本 欢迎搜索并关注 实践与文本 编辑:潘玥 ↓↓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实践与文本”新浪微博主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