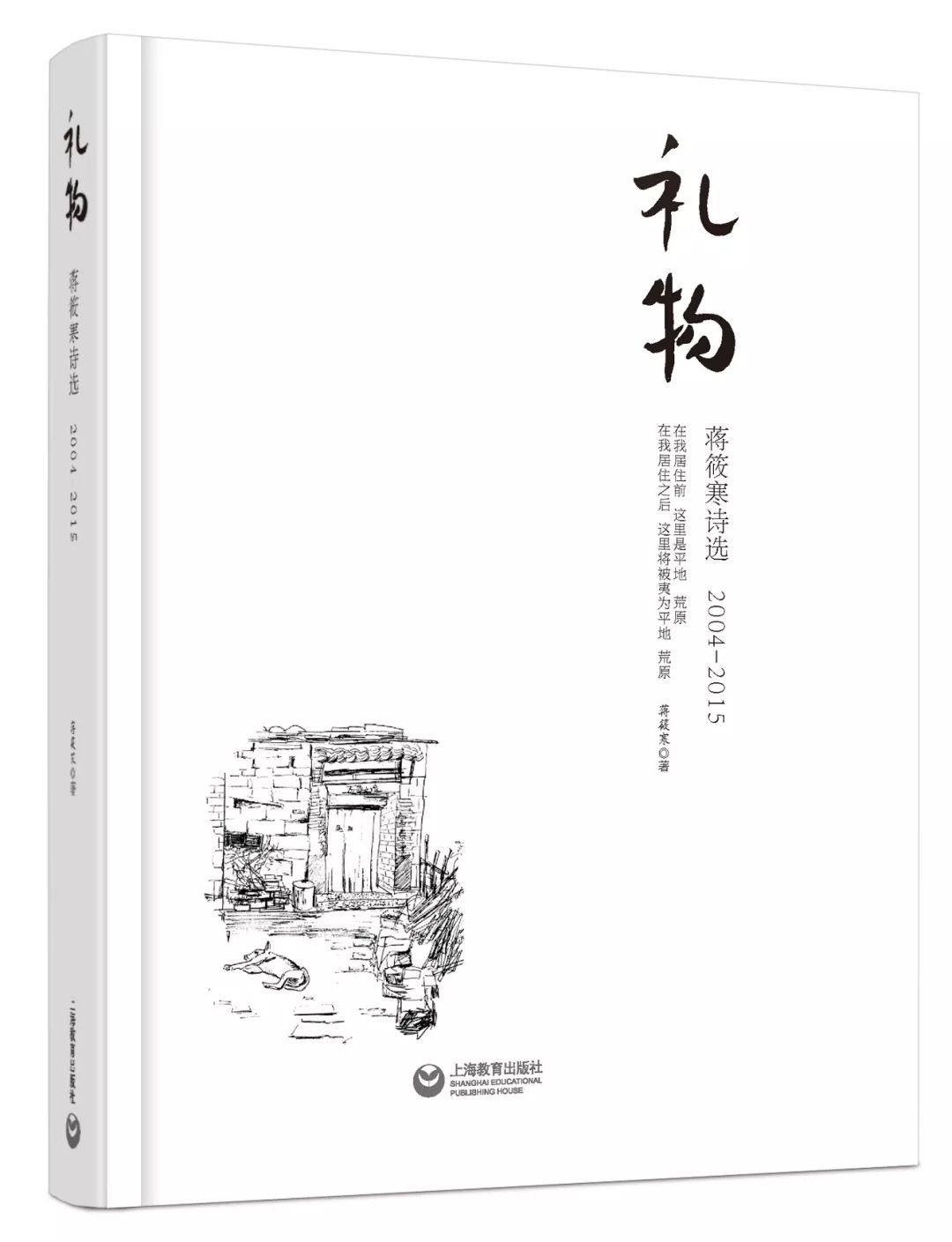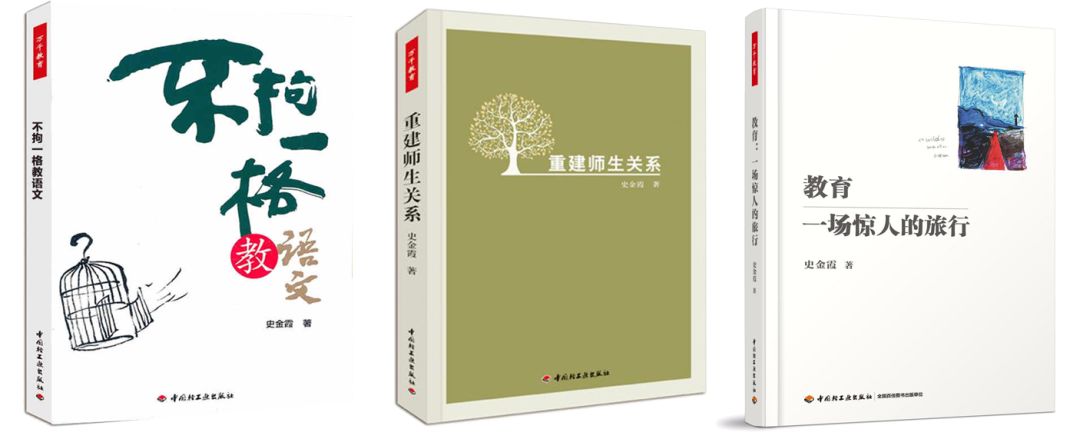| “我手里拿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一一纪念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我手里拿着一个人 › “我手里拿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一一纪念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
“我手里拿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一一纪念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
译丨杨春 我愉快地走进这个大厅。在我之前来到这里的人们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们真是一队使人感到敬畏和亲近的桂冠诗人。名单上这一长串的名字的拥有者创作的作品使我感受到了整个世界。他们那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特征的艺术,以无穷的勇气和清澈的想像穿透了我的心灵;他们那令人惊叹的光辉的艺术才华激励和哺育了我。我在他们面前感到愧疚。对于瑞典文学院挑选了我来加入这个杰出的集体,我同样深感不安。 早在10月份,一位艺术家朋友在留言机里给我留下了一个口信。我把它保留了好几周,常常放来听听,只是想重温她声音中那颤抖的喜悦和言语里的信任。“我亲爱的姐妹,”她说.“你的奖也就是我们的奖,这个奖再没有比放在我们手里更合适的了。”她的留言的内在精神和那种坚定的乐观主义,以及高尚的信赖使我将那一天铭记在心里。 我将会离开这个大厅。然而,我会带着比进来时更新、更愉快的思绪:那就是未来的桂冠诗人们。就是那些——甚至在我说话的此时此刻,不断地挖掘、筛选和磨砺我们从未梦想过的闪亮的语言的人们。可是,无论他们中的任何人是否可以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中占据一席,这些作家都是不容忽视的,并且他们仍在不断上升。他们的声音表现着逝去的和未来的文明,他们用想像力凝视的悬崖也将会吸引着我们;他们不会置之不理.更不会掉头放弃。 因此,满怀着先行者的恩赐和姐妹们的祝福,喜悦地期待着未来的作家们,我接受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荣誉,也请你们一起来分享我此刻的荣耀。 “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的眼睛虽然瞎了,但头脑充满智慧。”或者是一个老头儿?也许是位长老,也或许是个哄劝淘气孩子的歌舞艺人。我曾经听过这个故事,或是类似的故事,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这样的传说。 “从前,有一个老太婆,瞎了,但很有智慧。” 在我知道的版本中,这个老太婆是奴隶的女儿。她是黑皮肤的美国人,孤独地住在城外的小屋里。她智慧的名声是无可比拟的,而且是毋庸置疑的。在她的人民中间,她既是法律,又是对法律的超越。她受到的尊崇以及她唤起的敬畏影响远及遥远的地方,一直传到了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乡下预言家的智慧则变得滑稽可笑了。 一天,三个年轻人来造访这个老太婆。他们似乎决心要驳斥她有非凡洞察力的说法,并向她表明他们认为她只是个冒牌货。他们的计划很简单:他们走进她的房间,问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仅仅取决于她和他们之间的一点差异。他们认为这个差异是一种严重的残疾,那就是她的失明。他们站在她面前,其中一人说道:“老太婆,我手里拿着一只小鸟。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没有回答,问题又重复了一遍。“我手里拿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还是没有回答。她瞎了,甚至看不见她的拜访者,更别提他们手里的东西了。她不知道他们的肤色、性别或者家乡。她只知道他们的动机。 老妇人沉默得太久了。年轻人抑制不住他们的笑声。 最后,她开口了,她的声音柔和而严峻。“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拿的鸟是死是活,但我确实知道它就在你手里。它在你手里。” 她的回答可以这样理解:如果鸟是死的,你或者是找了只死鸟,或者是杀了它。如果鸟是活的,你仍然可以杀了它。鸟是否可以活着,这出于你的决定。不管出现哪种情形,这都是你的责任。 因为夸耀他们自己的力量和老妇人的无助,这些年轻的来访者受到了惩罚,他们被告知不但要为这种嘲弄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要为那个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牺牲的小小生命负责。这个瞎眼的妇人转移了注意力,从对权力的判定转移到了行使权力的手段和工具。 思考“手中的鸟”意味着什么(除了它那脆弱的躯体以外),一直对我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现在,当我因为曾经做过的工作而进入了这个光荣的行列时。所以我选择将鸟读解为语言,老妇人就是有经验的作家。她担心她梦想中的、与生俱来的语言,是怎么被操纵,怎么为人运用,甚至因为某些恶毒的原因她怎么被拒斥。作为一个作家,她认为语言部分是一个体系,部分是一个受人控制的有生命的东西,但更像是一种媒介——如同一种带来后果的行为。所以那个孩子们向她提的问题“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并不是不现实的,因为她认为语言很容易死去,被删除。当然,语言被损害或被救助都是出于人们的意愿。她相信来访者手中的鸟如果死了,它的看管人会对它的尸体负责。对她来说,死的语言不仅指人们不再说或写的语言,它还是一种满足于崇拜自已的瘫痪状态的不屈服的语言。就像统计员的语言,被人审查,同时又审查别人。在履行它的职责时毫不留情,除了保有它陷于迷醉的自恋情结、排他主义以及权势的自由领地以外,它没有任何别的追求与目标。虽然已经垂死,但它并非毫无效力,它尽力地阻碍理智,阻塞良知,压制人类的潜能。由于对疑问毫无感知,它不可能形成或容忍新的观点,不能建构新的思想,不能讲述别的故事,或填补令人窒息的静默。官方语言被锻造出来支持无知和保持特权。这是一套被擦拭得闪闪发光的铠甲,骑士早已离它而去,留下了这副空壳:毫无光彩的、掠夺性的、感伤的。它在孩子们心中激起敬畏,为暴君提供庇护,在公众中唤起虚假的关于稳定和和谐的记忆。 她确信,如果语言死去,是由于疏忽、滥用、冷漠和缺乏尊重,或是被命令扼杀,那时不仅仅是她,所有语言的使用者和创造者都对语言的夭折负有责任。在她的国家里,孩子们咬掉自己的舌头,用子弹来重述那种无语的声音,残废的和致人残废的语言的声音——一种成年人已经共同抛弃了的、作为与意义缠结的提供指导或者表达爱意的手段的语言。但她知道,咬舌失语并非只是孩子们的选择。在那些领土和权力的交易者幼稚的脑袋中,这是很常见的。他们那被抽空的语言没有留给他们任何机会去接近他们仅存的人类本能,因为他们只对那些服从他们的人说话,或者只为了强迫别人服从而说话。 对语言有系统的洗劫,可以从这种趋势中看出来:语言的使用者们摒弃了它那精细、复杂、催生新生命的特征,使本身成为威胁和征服的语言。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仅代表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也不仅仅代表知识的局限,它直接限制知识。无论是让人迷惑的官方语言,还是没头脑的新闻媒介的人造语言;无论是学院派的骄傲但僵化的语言,还是利益驱动的科学语言;无论是缺乏道德标准的法律的恶意语言,还是为疏远少数族裔而创造的语言。在它文学的嘴脸后隐藏着种族主义者的掠夺行径——都必须受到拒绝、改变和揭露。这是一种吸血的语言,它掩盖了弱点,在可敬的爱国主义的裙衣下蜷曲着法西斯主义者的根须。它无情地朝着最低处的思想移动着。性别主义者的语言,种族主义者的语言,有神论者的语言,都是典型的统治的控制性语言。它们不能,也不会容忍新的知识,或鼓励观念的相互交流。 老妇人清醒地知道,没有一个雇佣的知识分子、贪得无厌的独裁者,或被收买的政客及社会活动家,也没有一个冒牌的新闻工作者,会被她的观点说服。也许有或将会有煽动性的语言,让公众武装自己也武装别人,或在商业中心、法院、邮局、运动场、卧室和林阴道上,被人屠杀并屠杀别人;还会有蛊惑人心的纪念的语言来掩饰无谓的死亡的浪费和可悲;还会有更多的外交辞令纵容强奸、折磨和暗杀;也许有或将会有更多诱惑性的变种的语言被设计出来扼杀妇女,用强硬的侵略性的语言,像填鸭一般堵塞她们的喉咙;还将会有更多监视的语言伪装成学术研究;将会有更多政治和历史的语言被计算出来补偿千百万沉默民众的苦痛;将会有更多迷惑人心的语言挑动不满的受剥夺的人们去袭击他们的邻人;将会有更多自以为是的伪经验主义语言被巧制出来,把有创造性的人们禁锢在卑微和绝望的牢笼之中。 在滔滔不绝的雄辩、炫目的光彩和学者式的联盟下,虽然仍有煽动性和诱惑力,这类语言的心脏正在逐渐衰弱,或者也许根本不再跳动——如果小鸟已经死了的话。 她思索任何一种流派的知识如果没有被坚持或被强迫成为对时间和生命的浪费的话,那么它的历史会是什么样的?那是统治的合理化和统治的陈述所要求的——一种致命的隔绝的话语,它阻塞了隔绝者和被隔绝者通往认知的道路。 巴别塔故事中的传统智慧认为,塔的倒塌是一种不幸,是繁多语言的散乱和重量加速了塔的建筑的失败。而一种坚如磐石般的单一语言将会促进塔的建成,并且天堂也就触手可及了。是谁的天堂?她在想。是哪一种天堂?如果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别的语言、别的观点、别的叙事阶段的话,也许这乐园的建成有点儿操之过急,有点儿太匆忙了。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梦想的天堂可能早就在他们脚下被发现了。这似乎有点儿复杂,有点儿苛求于人,确实如此,但这是真实生活中的天堂景象,而不是身后才能享有的天堂。 她不愿留给她的年轻来访者这种印象:应该迫使语言为了活着而活着。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能生动地描绘说话者、读者和作者的真实的、想像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有时它的平衡在于置换经验,但它并非经验的替代品。它俯着身朝向意义可能存在的地方。当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在思虑他的国家已快成为一个大墓园时,他说:“世界几乎不会注意或长久地记住我们在这儿说了些什么,但它永远不会忘记人们在这儿做了些什么。”他的简单话语充满了对生活信念的支持,是振奋人心的。因为他的话拒绝忽略在一场杀人竞赛的战争中牺牲60万人的现实,拒绝树碑立传,蔑视“结束语”和精确的“总数”,承认他们“没有权力增加或减损”。他的话表明了话语和它所哀悼的不可把握的生活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触动了她,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生活,语言也永远不应当等同于生活。语言永远不能阻止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也不应当有向往获得这种能力的自负。语言的力量和巧妙存在于它向不可言说的事物的努力接近中。 无论是洪亮的还是微弱的,是躲躲闪闪的还是攻击性的,或是拒绝崇拜神明的;也无论它是放声大笑还是无字的哭泣,精选的词语和有选择的沉默以及未受干扰的语言都汹涌着奔向知识,而不是毁灭。但是,谁不知道文学因为提出疑问而被禁止,因为批评而被诋毁,因为提供不同的选择而被删除。又有多少人被自我劫持的语言的想法所激怒? 文学工作是神圣的,她想,因为它是生产性的。它创造意义——确保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作为人类而具有的差异——我们与其他生命不同的表现方式。 我们死了。这可能是生命的含义。但我们“做出”了语言。这可能是为了衡量我们的生命。 “从前……”来访者向一个老妇人提了一个问题。这些孩子们是谁?在那次相遇中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从“小鸟在你们手里”这句最后的话里听出了什么?这句话是表明可能性的一个手势还是指锁上了门闩?也许孩子们听到的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我老了,是个女人,黑皮肤,又瞎了眼。我现在具有的智慧就是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们。语言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他们站在那儿。设想一下他们手里空无一物,设想一下这次拜访只是一个诡计,是为了让别人对他们说话,让别人认真地对待他们,而这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或许这是一个机会——去插话,去侵犯成年人的世界及其话语的魅力?他们的急切的疑问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包括他们问的“我们拿的这只鸟是死的还是活的?”这个问题也许意味着“能否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死亡?”根本没有诡计,也没有愚蠢。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引起一个智者的关注。如果一个老人,一个经历过生活并面对过死亡的年老的智者仍不能描述生死,那还有谁能做到呢? 但她没有这么做。她保守了她的秘密、她的好建议、她的小矮神般的见解,以及她的不许诺的艺术。她保持并强化了她与别人的距离,又重新退缩回孤独的隔绝中去,回到她那深谙世故的、享有特权的天地中。 什么也没说,在她的转移了声明之后再没有一句话。那种沉默是深刻的,比她说的话中可能包含的意义更深刻。这沉默颤动着,而迷惑不解的孩子们用刚刚创造出的语言充满了它。 “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他们问她,“你难道没有一句话可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冲破失败的记录?冲破你刚刚给予我们的根本不是教育的教育?冲破你在年龄和智慧之间竖立的这道屏障? “我们的手里根本没有小鸟,无论死的还是活的。我们只有你和我们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手中空无一物的事实包含了一点儿你无法去沉思,甚至无法去猜想的东西?你难道不记得当你年轻时,语言没有意义却充满魔力?为什么你说出的话有时却无法表达意义?为什么有时想像力驱使你去寻找的东西却看不见?寻求答案的疑问和要求猛烈地燃烧着,而你为什么却由于无法回答而愤怒地颤抖?” “难道我们不得不以一场像你那样的英雄们曾经参加并失败过的战斗来作为理智的开端,留下我们两手空空,除了你想像中那儿有的东西以外空无一物?你的回答非常有技巧,但这种技巧使我们尴尬,也应该让你自己感到尴尬。你的回答因其自我庆贺的表现而显得粗鄙。如果我们手中空无一物,那么为电视而炮制的发言将毫无意义。 “为什么你不伸出手来,用你柔软的手指触摸我们,暂且缓一缓你严厉的攻击和你的训诫,直到你弄清我们到底是谁?难道你如此蔑视我们的小花招,我们的做法,以至于看不出我们正为如何得到你的关注而倍感困惑?我们很年轻,还不成熟。我们已经听取了我们必须对之负责的年轻短暂的生活。但是日渐演变成的这场大灾难又能说明什么呢?这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没有东西可被暴露,因为它们已经很露骨’。我们获得的遗产就是蓄意冒犯。你指望我们拥有和你一样老迈、空虚的眼睛,只看见残酷和平庸。你以为我们竟愚蠢到如此地步,会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为国家民族的虚幻构想作伪证?当我们浸没在你的过去的毒素中,你还敢对我们谈起责任?” “你使我们显得琐碎平庸,也使我们手中不存在的小鸟显得琐碎平庸。难道我们的生活没有上下左右的联系?难道就没有歌,没有文字,没有富含维生素的诗,没有与经验相连的历史,而只有你可以帮助我们变得强壮?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是老人,是有智慧的人,别再考虑保全自己的面子了。请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你特有的世界。你编一个故事,叙事是最根本的,它会在自己被创造出来的一瞬间创造我们。我们不会责怪你,如果你的努力超出了你的把握;如果爱点燃了你的话语,使它们在火焰中坍塌,只留下烫伤的痕迹;或者,如果以外科医生的双手的严谨,你的话语仅仅缝合了鲜血喷涌的地方。你知道你永远不可能正确地做到这一切——永远不可能。只有激情或只有技巧都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试一试吧,以我们的名义和你的名义,忘掉你远播的名声。别告诉我们去信仰什么,去惧怕什么。给我们展示信仰的宽大的衬衣,拆开恐惧的发网的针脚。你,一位老妇人,因为失明而受到祝福——能说那一种语言——可以告诉我们只有语言能做到的事:如何见无像之物。只有语言能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面对无名之物的恐惧。语言就是沉思。 “告诉我们做女人是怎样的,我们才会知道做男人是怎样的;告诉我们什么在边缘移动,在这个地方,没有家是怎样的,离开你熟悉的家四处漂游又是怎样的;告诉我们生活在城镇的边沿,无法忍受你的陪伴又是怎样的。 “告诉我们关于复活节时从海岸边驶离的船只,离开了田野的源头;告诉我们关于满满一马车奴隶,关于他们轻声的吟唱,在飘落的雪花下不可辨别的呼吸,关于他们从邻近的肩膀上预感到下一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站。男人和女人的手都在祈祷,他们想着热量,更想到了太阳。他们抬起脸来,仿佛太阳就在那儿,可以亲近;他们转动着身体,仿佛太阳就在那儿,触手可及。他们在一个小旅店门前停了下来。赶车的人和他的伙伴拿着灯走进门去,留下他们在黑暗中低声嘟嚷着。马蹄下的白雪喷出的蒸汽,以及积雪融化的嘶嘶声都使冰冷的奴隶们羡慕。 “小旅店的门开了:一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从屋里的灯光中走出来。他们爬上了马车的铺位。这个男孩儿在三年之后将会拿着一支枪,但现在他提着一盏灯和一壶温暖的苹果酒。壶从一个人嘴边传到另一个人嘴边。那个女孩儿在分发面包、一块块的肉以及一些别的:对每个接受食物的人眼睛飞快地一瞥。每个男人给一份,每个女人给两份。女孩儿看他们一眼,他们也回看她。下一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但不是这一站。这一站已经变暖和了。” 孩子们说完之后,又安静下来,直到那位老妇人打破了沉默。 “最后,”她说,“我信任你们了。我相信小鸟并不在你们手中,因为你们确实抓住了它。看,它多可爱啊,我们共同完成的这一切。”
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 1931年2月18日-2019年8月5日 托妮·莫里森是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一位获得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小说家、编辑和教授。她的小说以史诗的主题,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细致的非裔美国人角色而著称,这些人物对他们的叙事至关重要。她最著名的小说有《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爵士》《爱》。莫里森2012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还获得了书坛的诸多赞誉和荣誉学位。 1931年2月18日出生在俄亥俄州洛雷恩市一个非洲裔家庭,在四兄弟姐妹是排行第二。其父亲主要从事焊工,同时也做过好几份工作来养家。母亲是一名家政工。莫里森后来说,她的父母给她灌输了对阅读、音乐和民间文学的热爱,以及清晰和有洞察力的观念。 莫里森生活在一个综合的社区里,直到十几岁的时候,她才完全意识到种族的分歧。“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没有人认为我低人一等。我是班里唯一的黑人,也是唯一会读书的孩子。”她后来告诉《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莫里森在学校里学习拉丁文,读了许多欧洲文学名著。她于1949年以优异成绩从罗兰高中毕业后入读霍华德大学,继续追求她对文学的热爱;她主修英语,修选了古典名著。1953年从霍华德大学毕业后,莫里森继续在康奈尔大学深造。她写的论文是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威廉·福克纳的作品,并于1955年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之后她搬到了德州,在德克萨斯南方大学任教。 1957年,莫里森回到霍华德大学教英语。在那里,她遇到了哈罗德·莫里森,一位来自牙买加的建筑师。她们于1958年结婚,1961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哈罗德。她的儿子出生后,莫里森加入了一个作家小组。她开始为这个小组写她的第一部小说,最初是一个短篇故事。 莫里森于1963年决定离开霍华德。她和家人在欧洲旅行了一个夏天后,带着儿子回到了美国。但是,她的丈夫已决定搬回牙买加。那时,莫里森怀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1964年,在儿子斯莱德出生之前,她搬回了家乡,和她的家人住在俄亥俄州。第二年,她随儿子搬到了纽约的锡拉库扎,在一家教科书出版社任高级编辑。莫里森其后去了兰登书屋,在那里她编辑了托尼·卡德·班巴拉和盖尔·琼斯的作品,他们以文学小说而闻名。 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出版于1970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的非洲裔美国女孩佩科拉的爱情故事,佩科拉相信只要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那苦难生活就会变得更好。这部有争议的作品卖得不好,莫里森在1994年的一个后记中说,对这本书的接受程度与她的主要角色在世界上受到的待遇是一样的:“被解雇,被轻视,被误读。 尽管如此,莫里森继续探索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她的第二部小说《秀拉》(1973)通过两个在俄亥俄州一起长大的女人的友谊来探索善与恶。《秀拉》被提名为美国图书奖候选人。 《所罗门之歌》是托妮·莫里森1977年的作品。小说以“黑人会飞”这则古老的民间传说为故事主线和象征核心,通过北方城市一个富裕黑人家庭的小儿子奶娃南行故土寻找金子,从而意外找到家族之根,文化之源的人生经历,展现出一幅绚烂壮阔的黑人生存画卷,揭示出新老两代、男女两性、贫富两极间的种种冲突,提出了在物质生活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才能解决精神生活贫乏、文化无根的这一严峻社会问题。小说融合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以极具想象力又颇具口语化风格的语言,运用民间色彩浓厚的神话故事,阐释了一个深刻的人类命题。莫里森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许多赞誉。 莫里森做为一位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1980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委员。次年出版了《柏油娃》。这部以加勒比海为基地的小说从民间故事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并受到了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然而,她的下一部作品《宠儿》被证明是她最伟大的杰作之一,这是托妮·莫里森最震撼人心、最成熟的代表作,现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小说完成于1987年,1988年即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2006年《纽约时报》召集125位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及文坛泰斗等选出自己心目中“25年来最佳美国小说”,《宠儿》得票最高,名列第一。《宠儿》讲述女黑奴塞丝怀着身孕只身从肯塔基的奴隶庄园逃到俄亥俄,奴隶主循踪追至;为了使儿女不再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毅然杀死了自己刚刚会爬的幼女宠儿……十八年后宠儿还魂重返人间,和塞丝、塞丝的女儿丹芙以及塞丝的情人保罗•D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她不但加倍地向母亲索取着爱,甚至纠缠和引诱保罗•D,不择手段地扰乱和摧毁母亲刚刚回暖的生活……全书充满苦涩的诗意和紧张的悬念。 莫里森于1989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并继续创作伟大的作品,包括文学《黑暗中的游戏:白色与文学想像》(1992)。为了表彰她在文学创作上的贡献,她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莫里森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裔美国女性。第二年,她出版了小说《爵士乐》,这部小说探讨了20世纪哈莱姆的婚姻爱情和背叛。 在普林斯顿,莫里森于1994年为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坊,叫做普林斯顿工作室。该计划旨在帮助学生在各种艺术领域创作原创作品。 除了她的学术工作,莫里森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她的小说《天堂》(1998)以一个虚构的非裔美国人小镇为主题,赢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1999年,莫里森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儿童文学。她和她的艺术家儿子斯莱德一起写《大盒子》(1999)、《贱人之书》(2002)、《蚂蚁还是蚱蜢》(2003)和《小云和风女士》(2010).她还探索了其他流派,写了剧本《做梦》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埃米特和作曲家安德烈·普雷平在1994年的《四首歌》的歌词,以及1997年与作曲家理查德·丹尼尔波的《甜言蜜语》。而在2000年,最初销量不大的《最蓝的眼睛》在被选为奥普拉图书俱乐部的选秀节目时,就成了一部文学巨著,卖出了数十万册。 创作于2003年的《爱》大胆探索爱的本质——它的疯狂、它的占有、它的恐惧、它的绝望!文字背后,藏着一颗深切的、令人无法拂逆的真心。那些流血、煎熬、痛苦、死亡,即使是你闻所未闻的,也一样能让你产生共鸣,感受到切肤之痛。《出版者周刊》的一位评论家称赞了这本书说:“莫里森创作了一部华丽、庄严的小说,它的神秘之处逐渐被发掘出来。” 2006年,莫里森宣布她将从普林斯顿的岗位上退休。那年,《纽约时报书评》将《宠儿》评为过去25年中最好的小说。她继续探索新的艺术形式。 2008年,莫里森的新小说《恩惠》出版。一个即是奴隶又是母亲的妇女必须对她的孩子做出可怕的选择。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评论家评价说这部小说是“神秘、历史和渴望的融合”,《纽约时报》评选此书为“年度十大好书”。 除了她的许多小说,莫里森还创作了非小说。她出版了自己的散文、评论和演讲集。
● 第六期 第六期 讲 ◉
史金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