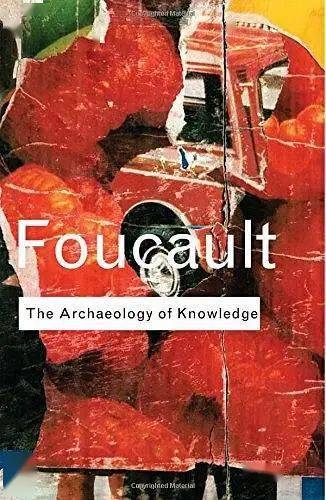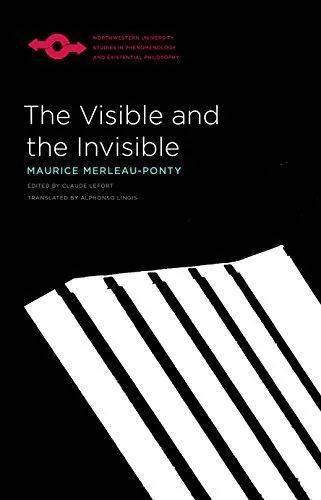| 朱迪斯·巴特勒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巴特勒对抗力量 › 朱迪斯·巴特勒 |
朱迪斯·巴特勒
|
让我们跟随尼采(Nietzsche)的名言前进:“轰隆隆……正午的十二个节拍”的钟声让自我反省的人感到惊愕,在这之后,他只是揉揉耳朵,“惊讶和不安”地问道,“我们刚刚经历的到底是什么?”这也许就是迟到,被弗洛伊德(Freud)称为“事后之思”(Nachtraglichkeit),是此类探究不可避免的特征,这种探究使叙事沾染了现在的历史视角。尽管如此,可否试着为受感染的过程提供一个叙事顺序,提供一个可能反思并转述尚未存在的生命的感受性及其转换的阈界,并对那个我的出现做出部分说明? 某些文学小说依赖于这类不可能的情景。想一想《大卫·科波菲尔》奇妙绝伦的开头,其中的叙述者以非凡的洞察力讲述了自己出生前的日常生活细节。他顺带提到,有人跟他讲述他的出生故事,他也相信别人告诉他的,但随着叙事的开展,他不再转述这个故事,好像这个故事是由别人写的;他从出生开始,就把自己当作一个知情的叙述者,也许是为了摆脱曾经是一个婴儿,不能像成年作者那样说话、反省或思考的困难。某种对婴儿期的否认,影响了他越来越具权威的讲述,包括自己何时哭泣,那时他人在想什么、做什么。 叙述的权威并不要求在现场。只要一个人能从不在场的位置,以一种可信的方式重构现场,或者,某种难以置信的叙事因叙述者自身的原因而令人信服。当他在讲述时,这个故事有些意味深长,因为我们正在被他相当出色的自我理解引入其中。他所讲述的内容可能并不真实,但这不重要,一旦我们明白他所完成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创作野心与欲望,那显然,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对抗并取代婴儿的被动性和原动力控制的缺乏,或许还需要抵抗被交付给他不可能选择的人,而这些人最后都或多或少地照顾着他。 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中发生的这类事情,在主体形成理论中是相似的。相反,我想说的是,像这样的叙事姿态在几乎所有的主体形成理论中都有一席之地。主体形成理论的叙事维度是否不可能?但这个维度又是必要的,只是不可避免地迟到了,特别是当我们得去辨别感染主体的东西最初如何激活了主体,以及这些转化过程如何在后来被激活的生命中重申。如果我们想讨论这些问题,必须要接受居于一个不可能的位置,这个位置也许重复了我们试图描述的条件的不可能性。 说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意味着不能做到,而只是说,我们无法完全摆脱成年生活的束缚,除非自问那些最初的转变如何与我们同在,它们如何一次次重现。在我说自己受到感染之前,我就已经成为了“我”,这是通过使用尚未投入使用的代词来传递消息,混淆了这个时间性与那个时间性。我,就个人而言,不能回到那个地方,我也不能以非人称的方式做到。然而,我们似乎仍有许多话可以说。例如,让我们想一想,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主体的出现或形成。
在理论的脉络中,我们大致可以跟随福柯主义的线索,简单地说,主体是通过规范或更普遍的话语生产出来的。如果我们慢下来,问一问“生产”是什么意思,这种被动的动词形式属于什么样的生产观,我们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被生产”与“被形成”是否相同?我们使用哪种措辞是否重要?我们总是有可能把规范称为一种单一的东西,但是请记住,规范往往成簇地出现,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有空间和时间维度,这与它们是什么、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形成它们所作用的东西密不可分。 规范或许先于我们存在,在接触我们之前,它就已经在世界上流转了。当它突然出现时,它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规范使我们感受到它的重要性,而这种感受打开了一个情感寄存器。规范形成了我们,但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它们留下的感受有某种接近的、非自愿的关系;它们需要我们的感受能力,并加强了这种能力。规范从各个方面作用于我们,也就是说,以多重的、时而矛盾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们在作用于感性的同时,也形成了感性;它们引导我们以某种方式去感受,而这些感受甚至可以进入我们的思考,因为我们最终很可能会思考它们。它们制约了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作为有思想、会说话的存在出现,它们就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相反,它们继续按照一种重复的逻辑行事,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只有在生命结束时这种逻辑才会结束,尽管规范的生命(更普遍的说法是话语的生命)会以一种与我们的有限性完全不同的韧性继续下去。福柯对此了然于心,他表明:“话语不是生命:它的时间不是你们的时间。” 当我们试图解释主体的形成时,往往会犯一个错误,我们会误以为单一规范充当了某种“原因”,然后把“主体”想象成随着这套规范的运作而形成的东西。也许我们所要描述的并不完全是一个因果序列。我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脱离一套规范,这套规范在等着我,已经安排好我的性别、种族和地位,甚至作为一种纯粹的潜能,在我第一声啼哭前就对我发挥了作用。因此,在我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在有一个时常认为自己就是自身行动的来源的“我”之前,规范、惯例、权力的体制形式就已经在运作中了。有时我们把自己理解为自身行动的来源,我并不是想嘲弄这样的时刻。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能动的,就必须这样去理解。我们的任务是把“受动”和“行动”看作同时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序列。也许这是一个反复发生的困境:一个人被交付给形成了他的世界,即使这个人采取行动或是试图将新的东西带入存在。尽管存在主义会欢欣鼓舞地抗议,但行动并不能使我们任何人从自己的形成中解放出来。我们的形成不会在某些中断或破裂之后突然消失;对于我们所讲述的自己的故事或其他自我理解的模式来说,中断和破裂变得很重要。我打破的那段历史仍然存在,正是那种断裂将我安置在此时此地。因此,如果没有这样的形成过程,我就无法真正思考。同时,没有任何东西事先决定了我,我不是一次就能明确形成的,而是持续或反复地形成的。当我在此时此地形塑自己时,我仍然在形成过程中。并且,我的自我形成活动——有人称之为“自我塑造”——成为这个持续的形成过程的一部分。我从来不是简单地形塑而成,也不完全是自我形成。这也许是另一种说法,即我们生活在历史性的时间中,或者说,时间作为人类生物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历史性,存活在我们身上。
最后,如果我不谈谈伦理关系的轮廓如何从主体形成的持续悖论中出现,我的论点就不会完整。我不仅受到某个他者或一系列他者的感染,而且受到一个世界的感染,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机构以及有机和无机过程都使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我从一开始就是易受感染的,以极不自愿的方式受到感染。我被剥削的可能性条件预示着我是一个需要支撑的人,我具有从属性,我为了采取行动而被交付给一个构造了基础的世界,我的生存需要一个情感的基础构造。在我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工作之前,我不仅已经受到别人的控制,我还在机构、话语和环境,包括技术和生命过程的“手中”,被一个超越人类的有机和无机的客体领域所操纵。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非人类的东西,“我”就无处可去、一无是处。 这种从属的非自愿的特性本身并不是剥削,但正如我们所知,它是一个向剥削敞开的从属领域。此外,感受性并不等同于征服,尽管当感受性被利用时,它显然会导致征服(就像我们探讨孩童受剥削时通常发生的情况,这取决于对孩童的从属性的剥削,以及相对不加批判的信任维度)。感受性本身并不能解释热情的依恋或坠入爱河,不能解释背叛或抛弃的感觉。然而,所有这些感觉的方式都能随之而来,这取决于那些打动我们、感染我们的人,以及易受我们感染的人发生了什么(甚至容易受到我们的感受性的感染,这个循环说明了某些形式的情感强度和性强度)。在每一种情况下,与其说是一个因果序列,不如说是在划定一系列关系时起作用的转折形式中;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或者,并不总是说,谁先感动了谁,或者,什么是被感动的时刻,什么是感动的时刻。这是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讲述“交织”时的重要见解。当他认为,在马勒伯朗仕(Malebranche)那里,被感动首先激活了知觉的主体,感动就与他更普遍的描述相关,即我们究竟如何感知事物。 …… 相关文章 巴特勒 | 非暴力主张 巴特勒|无限期羁押(一) 巴特勒|无限期羁押(二) 巴特勒 | 心灵的诞生:忧郁、矛盾、愤怒 巴特勒|汉娜·阿伦特宣判的死刑 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 朱迪斯·巴特勒 |暴力、哀悼、政治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