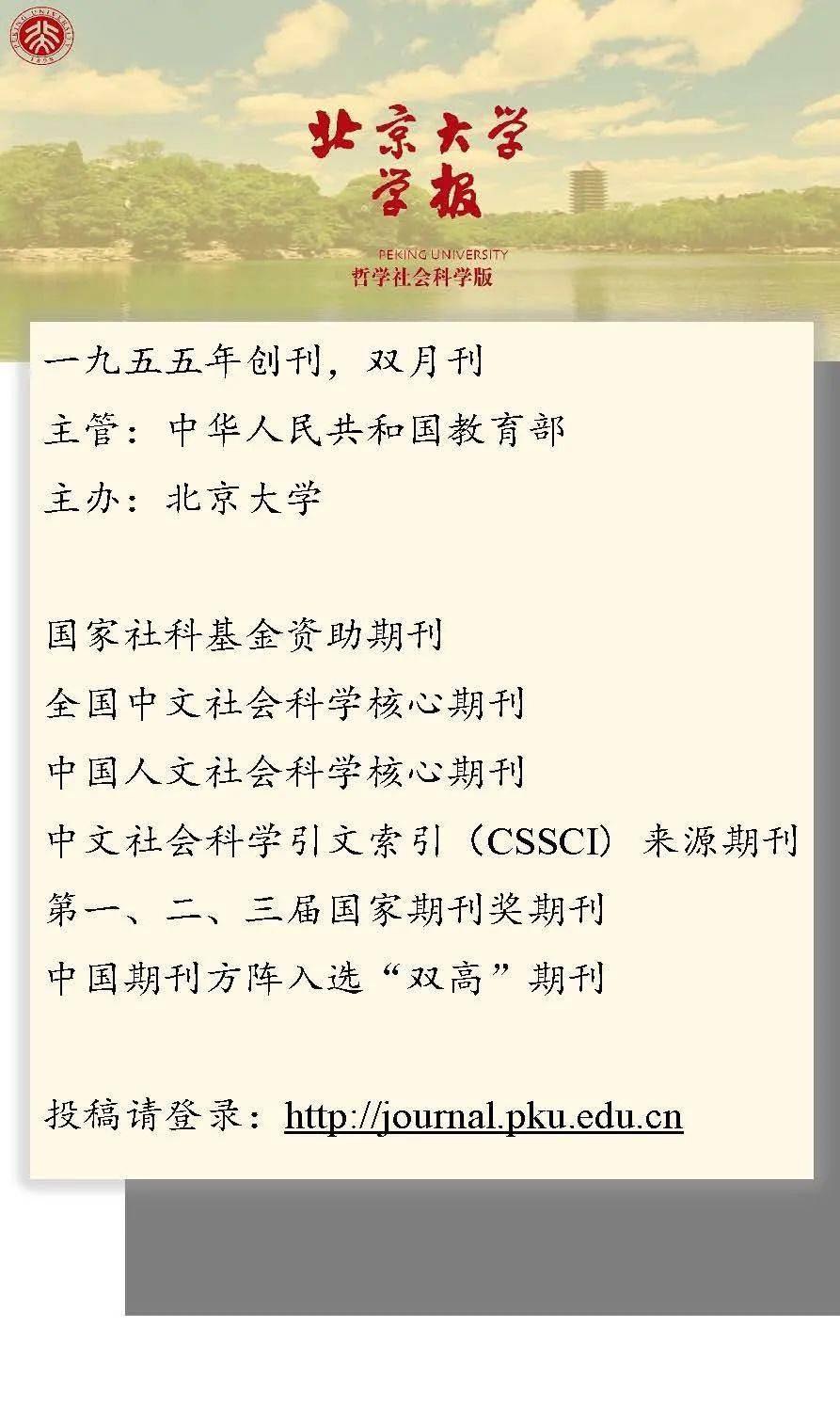| 诸子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山东济宁名人的故事和介绍 › 诸子 |
诸子
|
关键词: 逻辑性反思;物观;辩者之学 阅读导引 一、几何意义的物 二、礼序与物观 三、非乐、节葬、辩者的谱系 《墨辩》之称最早见于《晋书·鲁胜传》,指《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谭戒甫以为可增《大取》《小取》两篇,将墨家辩学的经典文献统称为《墨辩》。因战国末年墨家即已衰绝,加上历代儒者的批判,《墨子》一书,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晚清以来对《墨子》的关注,显然有西学东渐、救亡图强的背景。 对于《墨辩》中的逻辑学或辩学,已经有很多深入的研究。本文着眼于《墨辩》中的物的观念,并尝 试探究这种“纯客观”的物观念何以能在先秦时期出现,以及这样的观念何以只产生于墨家的思想传统。 一、几何意义的物 《墨辩》中的逻辑学与古希腊以降的西方逻辑学有明显不同。将《墨辩》中与逻辑有关的知识和思想定性为逻辑性反思,也许更为恰当。《墨辩》中虽然不乏关于说理方式的形式化思考,但大都与具体的论辩或义理宗旨有关。换言之,对思维形式的反思总是与思想内容结合在一起的。比如,《经上》第四十一条“穷,或有前不容尺也”,是关于有穷、无穷的论断。这一论断与“兼爱”思想的论证有关。《经下》第七十五条说:“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又如《经下》第七十一条:“‘以言为尽誖’誖。说在其言。”这一条应该是针对老、庄思想而发的。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中,没有脱离思维内容单纯考察思维形式的路向。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哲学的缺陷。思维的纯形式的规定,并不能赋予真理性探索以具体的内涵和形态。就仿佛力学的基本原理无法决定建筑物的功能,更不能规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悲欢一样。《墨经》批评“以言为尽誖”的主张,揭示出了庄子“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的思想的逻辑困境:说“言尽誖”之言,也是言说。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庄子的根本洞见:究竟实在是不可言说的。要说不可言说者,所以有沉默的至德者与言说的闻道者的区别。而且,即使是闻道者的也仅仅是“尝言之”或“妄言之”。《墨辩》反映出战国时期哲学理性的普遍状况:所有的哲学家,无论是否参与同时代的论辩,都要在逻辑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可被质疑、检验和辩护的思想。 墨家的经验主义,是哲学史的通识。这一点,在《墨辩》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当然,墨家的认识论 并不完全局限于感官知识。《经下》第四十六条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梁启超认为这里的“久”指时间:“吾人之得有时间观念,全不恃五官之感受,与以目见火不相当。”虽然我们不能说时间观念与感官经验无关,但却不是任何感官经验所能把握的。 在先秦哲学中,重视感性经验的并不只有墨家。《荀子》《韩非子》都有对感性知识的强调。《韩非 子·解老》解释《老子》的“前识”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也。”这里“无缘”的“缘”,与《荀子》“缘天官”的思想有关。强调的是心的“征知”作用要以感官的“当簿其类”为基础。陈奇猷说:“无缘而忘意度,谓无所因而妄以意忖度之也”,应该是错失了文义的关键。《荀子》《韩非子》里虽然重视感官经验,但其中的物仍是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当中的物,与《墨辩》中“纯客观”的物相去甚远。 对光与影关系的客观考察,是《墨辩》中值得特别关注的部分。一组实验物理学中的光学命题,在 礼序和自然笼罩下的对万物的泛观中,格外地突兀。《经下》第十六至二十三条,梁启超说:“右八条皆论光学。”以第十八条为例: 《经》: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 《经说》:景〇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 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 孙诒让等人都认为这一条《经》和《经说》的内容讲的是小孔成像的原理。仅此一例,已可见《墨辩》考 察事物的客观态度。 这种独有的观察事物的客观眼光,是《墨辩》关注物的几何形状的根由。进而,几何学的要素有了 被从物当中抽离出来单独考察的可能。《经上》第五十八和五十九条对圆和方给出了几何学上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方,柱隅四讙也。” 一旦有了几何学意义的形的观念,对运动及与之相关的时、空的概念界定也就进入了观物的视野: 动,或徙也。 久,弥异时也。 宇,弥异所也。 这里提“宇”和“久”,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宇”和“宙”,即时间和空间。“或徙也”的“或”,是“域”的本 字。将运动理解为空间上的改变,今天看来并没什么新奇,但放在先秦时代却是令人惊讶的独到眼光。这里的“域徙”,谭戒甫以为应读作“或纵”:“动或纵者,物本静止,不得无故自动;或以力纵之则动矣。”并将这一条与下一条“止,以久也”联系起来,以为暗合于牛顿第一定律。这一解释恐有过度联系和发挥之嫌。《墨辩》中有明确界定力的条目:《经上》第二十一条“力,刑之所以奋也”,即是对力的定义性理解。这一理解虽然有相当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应该还是对经验常识的总结。不能与近代的力学等量齐观。 《墨辩》中独特的观物方式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数学所 以先兴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关于墨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不论这一猜测是否有根据,“清庙之守”似乎是可以有闲暇的。然而,不管某家盖出于某职官的联想式溯源对于理解先秦各家思想有什么实质的意义,“闲暇”都与“以自苦为极”的墨者无关。《庄子·天下篇》说:“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亲自操槀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虽然《墨辩》里的几何学要素,远未达到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周详系统,但毫无疑问是超越经验日常的抽象思考。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对于解释《墨辩》的观物方式而言,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说”并不适用。 二、礼序与物观 先秦典籍中出现的物,往往是人伦日用当中的。虽然粗看起来差别不大,但如细加辨析,还是能看 出不同思想传统间视线的差异。《论语》中的物,基本都是礼序中的: 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绤,必表而出之。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举凡服饰的颜色、质地,房屋的结构、位置,饮食的来源、状态,无不笼罩在礼序织就的价值网络之下。 与《论语》相较,《老子》中的物虽然也在日常经验中,但更多是实际功用意义上的,没有明显的礼序上的价值和等差: 三十辐共一,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礼序的价值和等差之外,物的客观功用显露出来,获得了更具客观意味的审视。 韩非虽“与李斯俱事荀卿”,但并未继承荀子的礼学思想。韩非主张“礼为情貌”“文为质饰”: 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韩非既将礼视为外在的修饰,其观物亦在礼序之外: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 在这样的物观之下,物的客观属性而非价值定位得到了凸显。 通过对先秦时期各家物观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是否重视礼序是能否以更客观的方式观物的根本 原因。在礼俗相对稳定的时代,人们首先是在礼的秩序所规定的价值差序中辨识并感知事物的。尊卑、善恶、美丑等价值虽然有其物的层面的客观基础,但总体而言,在人的一般感知结构中被置于优先地位。春秋末年,随着礼坏乐崩局面的深化,维护固有礼序中蕴涵的高贵和善美,是孔子以降的儒者们自觉的历史担当。当然,孔子的伟大主要不在于试图拯救礼序的外壳,而在于建构性地提炼和升华其内在的精神性和道理的根源性。正是这一努力,在周的礼制被历史的理势荡涤之后,保留下了礼乐文明的根脉。不同于孔子更具远虑的历史眼光,在礼序崩解的时代趋向中,墨子等选择了对旧的礼乐世界的破坏和新的秩序的构造。这一思想倾向可以理解为先秦时期的“理性主义”潮流。墨子、老子、韩非子等都属于这一潮流的支派。虽然对理想世界的构想各不相同,但在致力于旧的礼序的破坏这一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 三、非乐、节葬、 辩者的谱系 与《老子》径指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同,墨子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礼的价值。这与他的整体思想有关:墨子既强调“尚同”“一义”,就不能没有等级秩序;既主张“天志”“明鬼”,就不能没有祭礼典礼。墨子将礼当中不符合“节用”原则的修饰性要素放置到“乐”的范畴里,在保留礼的基本等序和仪式的同时,明确提出了“非乐”的主张: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 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与《荀子·乐论》当中的“乐”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墨子的“乐”的外延极大的扩充了:不仅包含音乐和舞 蹈,美味、厚居、繁文都涵括其中。 与“非乐”相比,“节葬”是更极端的主张。在三代的礼制中,丧葬的仪节都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不 仅是身份等差的体现,也是人伦关系中义务和权力的具体化。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可以视为儒家对丧礼的社会意义的一般理解。墨子则试图将丧葬仪式中的等差通统取消: 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 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 与儒家一样,墨子也强调自己的思想根源于古代的圣王,是尧、舜、禹相承之道。从功利主义视角出发, “节葬”对于节省社会财富、增加社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然而,正如孟子对墨者夷之所说的:既然“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那么,“薄葬”到什么程度呢? 能够像“上古不葬其亲者”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吗?既然一定要安葬,那就还是要有恰当的标准。就一般的道理而言,墨子倡导的“棺三寸”“衣三领”的无等差的“葬埋之法”,有义理不通之处。但在那样一个普遍的僭乱奢暴的时代,墨子的激烈态度背后是有其深厚的人民情怀和深刻的历史忧思的。在一个礼序失范的时代,不仅更具客观性的物观成为可能,摆脱掉身份依附的人的观照也同时出现了。 墨子看到了习俗的偶然性,指出厚葬久丧不过是“便其习”“义其俗”而已,既无道理的根源性,也无 价值的普遍性。不同的种群可以有截然相反的礼俗: 昔者越之东有輆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 处。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 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 希罗多德《历史》中有类似的讨论:波斯国王大流士问希腊人会不会吃掉父亲的尸体,又问吃双亲尸体 的印度人会不会火葬父亲,得到的回答都是“那不可想象”。这一类的思考似乎证明了礼俗的形成并没有根源性的依据,只是族群生存历史的偶然结果。其实这只是表面性的结论。虽然不同族群具体的仪节安排有极大的不同,但仍然有根本结构的相似,比如,对于父母的去世,总要有不同于日常生活形态的仪式安排以表达或寄托哀悼之情。而那些偶然形成的极端方式(或者说陋俗),往往也会在族群精神的历史展开中被渐渐革除。其前提当然是理性精神的肇端和开启。 在先秦“理性主义”潮流中,墨家走在了最前列:不仅产生了从礼序下脱离出来、消解了价值属性的 客观的物观,也产生出了脱离了身份依附的人的观念。墨子提出的“尚贤”“尚同”等主张,已经有了明显的突破宗法世袭制度的观念。对既有礼序的突破,为更客观的物的观照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这一点,在老子和韩非那里,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佐证。但仅此一端,尚不足以解释《墨辩》中几何意义或物理意义的物观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墨辩》不仅是墨家的经典文本,亦是辩学的思想文献。对于辩论,儒家和道家都持 保留的态度。《老子》的“大辩若讷”、庄子的“大辩不言”,都从根本上否定了言辩的价值。孔子虽然重言,如说“不学《诗》,无以言”,但也以言辞便给为病,因此“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并“恶乎佞者”。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终身陷于各种论辩当中,但被问及“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时,却说:“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辩论在孟子那里仍然总体上是负面的。只有墨子给言辩赋予了庄重的意义: “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穫而捃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 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正是这样一种对待言辩的郑重态度,使得哲学思考以某种自我证明的形态形诸文字和语言有了不可或 缺的必要性。 关于先秦时期名辩之学的兴起,《庄子·天下篇》中明确的记述: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 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这段记述影响甚广,基本被视为辩者之学源起的学术史定论。然而,这一学术史图景是有进一步辨析的 必要的。首先,将名辩之学的产生归诸惠施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可疑的;其次,辩者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学派归属、仅以争论全无社会人生指向的辩题为乐的群体,这里面显然有庄子对言辩之学的态度的影响。从“历物之意”的最后一个命题“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看,惠施显然是有其立言宗旨的。 思想史上辩论的出现,总是源出于思想主张的分歧。这一点可以从《孟子》《庄子》等典籍中记载的 辩论得到证实。先秦时期,儒、墨并称显学。对于儒、墨两家相与辩论的情况,《淮南子·俶真训》有这样的记述: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 儒者和墨者之间普遍存在的辩论,恐怕才是辩者之学产生的根源。惠施和公孙龙的思想倾向至少从侧 面提供了佐证。 惠施的“历物之意”既讲齐同万物,又主张“泛爱万物”,应该是有墨家兼爱的思想倾向的。值得 注意的是,“历物之意”的命题中,也有几何学上的平面概念:“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惠施思想的墨家渊源,孙诒让、胡适等都曾论及。胡适更以《庄子·天下篇》的“别墨”之称界定惠施的学派属性,并认为“别墨犹言新墨”。对于以“别墨”为“新墨”的错谬,谭戒甫已做了驳正:“别墨”是墨家分化后相互贬斥之语,各墨家分支都自认“真墨”,而斥对方为“别墨”。从思想渊源及思想倾向看,惠施属辩者群体中的墨者,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因与《墨辩》论题的交互指涉,公孙龙似乎也有墨家渊源。然而,审读《公孙龙子》全书,却看不到 墨家思想的印迹。《公孙龙子·迹府》称:“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则公孙龙的思想重心在于“正名”。《公孙龙子·名实论》曰: 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 所位焉,正也。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名实关系以及是否当位都是儒家一贯的关注所在。公孙龙子的思想渊源和倾向,应该整体上是归属于 儒家的。惠施主合同异,旨在齐同,背后隐含的是兼爱的主张;公孙龙守离坚白,强调差异,指向的是等差的维护。 先秦辩学的产生和兴起,出于儒、墨二家的思想分歧以及与之相关的辩论。随着辩论的深入,开始 有种种关于辩论的逻辑性反思的出现,并衍生出一些相对独立和专门的论题。辩者们探讨和研究这些相对独立的论题,反而将背后真正的思想关切掩盖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辩者们从根本上遗忘了各自的思想宗旨。辩者群体辩论的题目往往与日常生活的内容无关,所以,给人以好奇立异、诞妄不经的印象。《庄子·天下篇》的刻画,代表了当时人们对辩者的一般理解。 《墨辩》中独特的物的观念的产生,一方面出于以墨家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潮流对固有礼序的突 破,另一方面源自对言辩的庄重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名辩之学的兴起。当时代的巨变冲决固有的礼序,一部分思想者因珍视其中的美好和高贵而选择维系和辩护,另一部分则视其为阻碍选择更彻底的破坏。前者的努力,保留住文明的精神内核,将其延承到新的形态的塑造和展开当中。后者的廓清扫除,则为新秩序的建立解除了桎梏和束缚。儒、墨之争是中国固有精神在时代变局中强劲的伸张,由此开启的理性辩论的思想疆域使得中国文明的义理基础被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微信号|bdxbzsb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