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中文学刊》改刊十年纪念】郭诗咏|论施蛰存小说中的文学地景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小说集梅雨之夕的作者施蛰存属于什么派 › 【《现代中文学刊》改刊十年纪念】郭诗咏|论施蛰存小说中的文学地景 |
【《现代中文学刊》改刊十年纪念】郭诗咏|论施蛰存小说中的文学地景
|
萨义德的研究发现,欧洲小说中的空间有着非常近似的模式。举例来说,在英国莎士比亚和奥斯汀等著名作家身上,可以发现某种共同的关注:把为社会所需要和授权的故事空间安排在英国和欧洲,然后通过编排、设计动机和故事的发展,把遥远的或边缘的世界联系起来。这些地方的出现虽然是为了故事的需要,但它们却总处于附属的位置。随着这些精心维持的大框架的出现,于是产生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统治、控制、利益、强化、适应性等观念。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体系不是产生于作者的(半阴谋性的)预先设计,而是与英国文化认同联系一起。而那个认同想像自己处在地理所认知的世界里。” [4]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尝试将多部欧洲经典小说置于帝国主义的空间内重新阅读,从地理的角度切入,分析小说所呈现的空间模式及历史经验,探讨小说隐含着的各种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对位关系,为欧洲帝国主义小说谱系进行梳理。他提醒我们: 当我们仔细阅读小说时,我们得出一个比我到现时为止描述的毫无掩饰的“全球的”帝国的观点更有辨别力和更微妙的观念。……我们必须坚持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并且拒绝把单个作者的独特贡献压缩进一个普遍的主题思想,这时我们必须承认,把各个小说互相连接起来的结构,离开小说本身是不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是从每一部小说里得到关于“海外”的具体经验的。反过来说,只有每一部小说才能产生、说明和体现例如英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这就使评论者必须阅读并分析而不只是概括和判断这些作品。[5] 萨义德提出的阅读策略,一方面着重作品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另方面亦重视各个小说的互相联系,将小说文本、作者经验、读者阅读经验三者坐落于实际历史空间,避免了简单化的文本阅读或纯粹的历史铺陈。 二、文化地理学 文化地理学的开端可追溯至十六世纪的民族志,但到了1980年代它才开始发展。文化地理学视文化为一套信仰或价值,赋予生活方式意义,生产出物质和象征形式,并藉此而再生产。文化地理学从生活的多样性和多重性出发,关注世界、空间和地方如何为人所诠释和利用,以及这些地方如何因此而有益于当地文化的延续。换言之,它处理的是观念与物质、实践与地方、文化与空间之间如何产生关联的问题。[7] 文化地理学将人类的地方经验纳入研究范图,以之为地理学的核心关怀。它这种关心独有特殊的取向(idiographic approach),扭转了传统地理学讲求量化与系统的普遍均一取向(nomothetic approach)。[8] 在1970年代晚期,地理学里的人文主义学派(humanistic geography)提出关心个体及其经验,从生活经验的角度研究作为个体的实际人群和寻常俗民。人文主义学派援引现象学中意向性、存有等概念,重振地理学是一种诠释性艺术的观点,一种新的文化地理学于焉诞生。这个研究进路后来发展为对内在世界观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成为了英美地理学界主要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人群如何与地景产生关系、其感知过程,以及物质和美学的诠释,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汇合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后,这种“文化转向”更使当代地理学展现出空前的活力和新视野。[9] 与萨义德相似,不少文化地理学家特别关注各种文学形式中的空间和地景的意义。文学作品里有各种各样对于空间的描述和阐释,但在过去量化的观点中,这些都因其“主观性”而受贬抑。不过,若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看来,这些经验的“主观性”恰恰是它应该受到重视的原因。文学作品体现了人对地方的理解,为人群与空间的情感、情绪关系提供线索。进一步来说,文学不只描绘地方,它协助创造了它们,因为现代人对地方的认识,许多时并不来自亲身经验,而是来自媒体的再现。正如迈克•克朗指出: 文学(以及其他更晚进的媒体)在塑造人群的地理想像方面,扮演着核心要角。(……)显示不同的书写模式如何表达了空间及移动性的不同关系,以及文学里头的空间关系如何被赋予不同意义。不仅作品本身诉说着地方,连作品的架构也诉说着社会如何在空间上安排秩序。[10] 文学的主观性恰恰表达了地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地方书写,展现出时代和生活的变化,并包含了各种体验世界和组织世界的方式。研究这些书写,不仅可以理解一个地区的居民如何理解身处的空间,而且可以把握社会媒介赋予地方意义的过程。一幅来自统计学的地图无法呈现人类丰富的地方经验,文学作品却能告诉我们更多有关生活的具体细节。
从90年代起,30年代上海现代派与城市的关系是研究的热点。吴福辉及李欧梵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两位学者分别从区域文化(海派)及现代都市文化切入,从文化史的角度,在具体历史框架及脉络中重新探讨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派作品,透过重构(reconstruct)及重绘(re-mapping),取得丰盈厚重的历史感和立体感。[11] 此后十年,张英进、史书美、李今的研究更有多方面的突破,硕果垒垒。[12] 那么,有关这个课题,是否还有置喙的空间?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施蛰存都市小说中的空间问题。施蛰存小说风格与刘呐鸥、穆时英有明显差异,如果说刘、穆两位倾向于对外追寻,浮沉于上海繁华之中的话,那么施蛰存小说则展现出一种较为内倾的形态,着重发掘人类内在的隐秘心理。较之《上海的狐步舞》等作品,施蛰存对现代上海都市的直接描绘相对地少,故此,如要其小说的空间问题,或许需要一个更细致的方式。 笔者认为,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阅读施蛰存的作品,或许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文化地理学的启发性在于,它提示了我们必须重视小说的地理和空间,尽管它看来是多么的无关宏旨。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挤身国际大都会之列,其城市发展、都市景观、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均体现了其迈向现代化的急促步伐。而处身于城市中的作者及其艺术作品,皆不能避免地卷入这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由此造就了现代派出现和滋长。事实上,“现代”除体现于物质文明之进步过程,同时亦是一种存在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具体经验。故此,谈现代派文学,必不能绕过小说人物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这些具体经验的(文本)生成空间。 或者,我们不妨采取以下的研究进路:从空间与地理角度切入施蛰存的小说文本,分析小说内部空间的特征,探讨小说是如何产生、说明和体现了现代人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换句话说,即观察作家如何把现实中的上海城市文本,写入∕翻译为小说文本。这种阅读策略有利于逾越简单的反映论,让小说背后所联系着的巨大背景重新浮现,开启通往释读现代性经验及其意识形态的可能路径。 以下将透过《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两本短篇小说集的阅读和分析,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勾勒1932年以后施蛰存小说的文学地景。[13] 笔者认为,这些小说中的地理空间是与城市联系着的。通过描述并分析小说所展现的地理空间及生活经验,可达至把握30年代上海文学现代性的一个侧面。作为上海30年代现代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施蛰存如何书写文学地景、构筑其小说空间?其小说空间模式又体现了怎样的现代性经验,怎样的资本主义逻辑?这些问题,笔者希望在本文结束的时候,能够得到具体的解答。 首先,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施蛰存个人对于都市和现代的理解。 施蛰存并非上海本地人,他祖籍杭州,出生于杭州水亭址老屋,两岁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迁到离上海不远的松江。十七岁(1922年秋)的时候,与戴望舒同往上海读书,正式开始在都市生活。[14] 因其亲身经历,施蛰存异常敏感于地域差异及其对作家的影响。在一次访问中,他特别指出了“都会”和“农村”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影响创作的因素除了政治,还有就是都会与农村。生长于农村的作家到了上海,无法接受都市的生活,他虽然人在上海,所写的仍是农村题材。都会并不是指所有在都市的人都是都市人。为什么戴望舒喜欢法国几个象征主义诗人像亚米多包夫尔等,他们用象征手法,但是思想感性的基础是田园的,他们并不描写巴黎,他们都描写平静的教堂、牧牛等,但是他们用象征的手法。我们不能说象征诗人就是都市诗人,象征派也是要分散的,部份诗人尤其是后期才跟都市结合。[15] “都会并不是指所有在都市的人都是都市人”一句,暗示了施蛰存对于都市文学的定义是相当严谨的。在他眼中,题材和技巧应该分开来谈,使用象征手法的诗人,不一定是都市诗人。要判别一个作家是否属于都市,题材(描写对象)的考虑比技巧更重要,只有“接受都市的生活”、描写都市,才能被看作是都市作家。 施蛰存虽然来自乡村地方,但似乎很快便融入了都市的生活。1928年,他在上海认识了刘呐鸥,形成了一个以刘呐鸥为中心的小团体,当中包括了戴望舒、杜衡,冯雪峰也参加过一阵子。在1999年12月的一次访问中,施蛰存细致地形容当时的生活: 我们是租界里追求新、追求时髦的青年人。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与一般的上海市民不同,也和鲁迅、叶圣陶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明显西化。那时,我们晚上常去Blue Bird(日本人开的舞厅)跳舞,我不常跳,多半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摆测字摊”(上海方言,一人独坐一处),喝一杯柠檬茶,观赏他们的舞姿。穆时英的舞跳得最好。 我对跳舞的兴趣不大,多为助兴才去。和跳舞相比,我更爱吃日本咖啡、和“沙利文”的西式牛排。[16] 对施蛰存说,西化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代表了“新”和“时髦”,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种走在时代尖端、更为“现代”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施蛰存对于“现代”的具体经验是与其西化的生活空间,即上海租界,联系在一起的。值得一提的是,租界里的“现代”似乎亦有不同的变奏,鲁迅虽然同样住在租界,但他的现代性经验跟施蛰存等西化青年是不同的。而与同样过着西化生活的刘呐鸥和穆时英比较起来,施蛰存又明显倾向于较为静态的一面,少了一份竞逐声色的喧闹。
不过,若就此断定施蛰存对现代的感受是静态的,却是言之尚早。施蛰存的现代性经验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格调高雅而闲适的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情调,另方面是种种有关速度、力量、机械、工业的现代文明进程的感知。众所周知,施蛰存曾主编过一份大型的文艺刊物《现代》。《现代》并非同人刊物,系由现代书店经营和出版,但由于编者的趣味,现代主义的作品占了不少篇幅,以致后来有所谓“《现代》派”之说。[17] 1933年5月,一位读者来信谈及《现代》的诗歌风格的问题,于是施蛰存写下了这段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说话: 《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与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18] 这段话除了是替《现代》中的现代主义诗歌护航外,亦体现了施蛰存个人对于现代的理解。他认为,现代生活包含了上一代人所感受不到的独特经验,现代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使现代人的感情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代生活发生的空间,俱是都市。设备完善的港湾、采用现代机械的工场、提供娱乐的舞场、鼓励消费的百货大楼,与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是物质文明发达的都市。在他的认知中,现代生活与都市空间是紧密相连的,都市既是他生活的空间,亦是他体验“现代”的场所。施蛰存对现代的理解是以都市为中心的,这种对现代空间的想像,同时贯彻于他的小说世界。故此,研究他的现代小说,有关空间的讨论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施蛰存对现代性经验的把握,其实远比他所描述的、甚至他所意识到的更为复杂。下文将尝试把施蛰存各篇小说连接起来,分析小说所涉及的空间地理,释读文本里隐含的关于“现代”的具体经验。我们将会看到,在他的小说空间所启示的文学地景中,一种非常强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30年代的上海形成。 正如上文指出,施蛰存的小说风格与刘呐鸥和穆时英有着明显的差异。施蛰存不追逐都市风景线,也不热衷上海狐步舞,他着重的是人物的心理、私人生活的琐事,而不是光怪陆离的都市物象。《上元灯》(1929年)以后,施蛰存尝试以心理分析手法新编历史故事,结集成《将军底头》(1932年),同时开始投入对都市生活的描绘。1933年,他为自己的创作生活历程作了一次小总结: 《石秀》以后,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的,还有《将军的头》及《孔雀胆》(后改名《阿襤公主》。)这两篇以后,我的创作兴趣是一面承袭了《魔道》,而写各种几乎是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一面却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灯》里的那篇《妻之生辰》而完成了许多以简短的篇幅,写接触于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的结集是本年在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的第三短篇集《梅雨之夕》,后者的结集是即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19] 毫无疑问,施蛰存的小说十分重视个人内心的刻划。尽管《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行品》(1933年)的小说,写的都是私人琐事和个体心理,但与之重叠的却是一个有关地理和空间的体系。这个巨大的体系,把各个小说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清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版图。从《梅雨之夕》开始,都市空间以非常一致的方式出现在施蛰存的小说世界里,这个模式似乎并不出于他的精心策划,而是来自作者对都市空间的想像性认同。 以下将分四个方面分析施蛰存小说中的文学地景,及其所展现的现代性经验,以理解施蛰存如何在小说文本中再现城市空间。 1 空间的流动性和符码化 许多理论家所指出,城市和乡村的生活空间有很大的差异。乡村作为一个共同体,村民生于斯长于斯,村中几乎每个人都彼此认识,甚至熟知对方的来历和性格。在乡村里,谁是本地人、谁是外来者,非常容易辨识。与之相反,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人口是流动的,都市愈国际化人口流动得愈厉害。 在齐美尔(Georg Simmel)笔下,陌生人(de Fremde)既是流动的又是固定的: 在这里陌生人不是在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和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和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人,他虽然没有继续游移,但是没有完全克服来和去的脱离。[20] 陌生人实际上是远和近的统一,“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21] 当代理论家如帕克(R.E. Park)将齐美尔对陌生人的分析应用于移民现象和文化接触的研究;不过,也有论者认为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其境遇“就是已经无家可归、注定四处漂泊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22] 若细心留意,《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的小说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而施蛰存则恰恰准确把握了城市空间流动的特点。在小说集里,大部份作品都以城市为背景,人物大部份是住在城市里的小市民,小部份是从郊区到城市来探访的过客。小说里常常有主人公不断穿越城市的情节,他们或有意前往某个目的地,或毫无目的地漫游。至于穿越城市的方式,有时是步行,有时是利用电车、火车等交通工具。 在施蛰存笔下,城市空间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狮子座流星》中同坐一辆公车的乘客、《特吕姑娘》中的百货公司主顾、《在巴黎大戏院》中的电影观众、《春阳》中的银行店员等等,全都是一些在城市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陌生人。城市生活迫使人们必须习惯与陌生人共处,即使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仍要跟他们打交道,甚至并肩而坐。 施蛰存似乎对于这群既远又近的陌生人怀有莫大的兴趣,一直尝试书写这些陌生人背后的“故事”。不少施蛰存的小说,如《梅雨之夕》、《春阳》和《魔道》等,都有主人公因陌生人而勾起遐思、幻想的情节。这种构思一方面跟他发掘内心真实的取向相呼应,另方面亦是他书写上海城市生活经验的方式。
以《梅雨之夕》例,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下班回家的白领,在雨中碰见一位陌生少女,提出送她一程,进而产生种种遐想。他既感到少女似曾相识,疑是昔日情人,但又感觉非常陌生,完全无法看穿她的所思所想。在撑伞送少女回家的途中,两人在城市街头并肩而行,身体的距离与心灵的距离的巨大反差,为这篇小说带来了特有的张力。《梅雨之夕》的故事构思,正是来源自城市人对路上的陌生人既远又近的感觉。正因为身边人无法捉摸无法穿透,故事才能有声有色地说下去。不嫌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弥漫于城市空间中的陌生感,这种“把陌生人想像为熟悉的”的构思(反之亦然),或许是无法想像的。 不过,无论城市人口如何流动,施蛰存笔下的城市空间总是井然有序的。城市街道有确实的名字,主人公活动的地点是具名的大厦、公园或店铺,而且可以与真实的上海地理互相对应。换句话说,小说的想像空间是透过密集的命名来划分的。施蛰存小说正是以一种将空间符码化的方式,完成其内在想像空间的规划。 《梅雨之夕》的小说空间亦是依靠这种模式而建构起来的。这篇小说的情节本来十分简单,只用三言两语就可交待,不过作者却以大量的内心独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都市漫游者的形象。梅雨时节的傍晚,主人公离开了办公室,开始步行回家: 走到外面,虽然已是满街灯火,但天色却转清朗了。曳着伞,避着檐滴,缓步过去,从江西路南口走到四川路桥,竟走了差不多半点钟光景。邮政局的大钟已是六点二十五分了。未走上桥,天色早已重又冥晦下来,但我并没有介意,因为晓得是傍晚的时分了。刚走到桥头,急雨骤然从乌云中漏下来,潇潇的起着繁响。看下面北四川路上和苏州河两岸行人的纷纷乱窜乱避,只觉得连自己心里也有些着急。[23] 后来,小说交待主人公走到天潼路口,再到文监师路、北四川路。在这里,他归途被中断了:他在屋檐下碰见一位刚下电车的少女,少女没有伞,于是他决定送少女一程。透过罗列街道名称及市内重要建筑物,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以一种符码化的方法重构出一个为人熟知的城市。透过一个又一个的路标,读者很容易就能确定主人公所在的准确位置。这种规划空间的方式,只能出现于城市,为乡村里一望无际的稻田赋予准确的地标,毕竟是难以想像的事。 而在《四喜子的生意》里,我们甚至可以凭人力车夫四喜子的行脚,绘出一幅上海地图。与《梅雨之夕》一样,这篇小说亦是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写成,四喜子以倒叙的方式重组自己被关在牢里的经过。由与妻子吵架,踏出家门算起,四喜子竟在一天里走过了上海许多地方。他首先乘渡船过黄浦江,到了码头,抄叉袋角,走到池滨桥,取了人力车,从卡德路出发,走过泥城桥,西藏路,大马路,经日升楼、新新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再到浙江路。后来他在江西路口载了一个外国妇人到法租界去,于是折回西藏路,经过大世界娱乐场的门前,穿过八仙桥到达霞飞路。沿途的车行、百货公司、照相馆、珠宝铺等,皆历历在目。正由于小说文本空间能与现实中的城市空间相印证,熟知上海地理的读者,很容易就会随着四喜子所描述的街名和地标,被卷入小说的虚构空间。 正是通过命名和符号化,施蛰存在他的小说里构筑了一个区域划分极为清晰的城市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地图化”了的空间,读者可按图索骥,将想像的空间与真实的上海空间连接起来,而背后与这种写作模式及阅读策略连接的,正是现代上海的城市生活经验。因为现代城市对于空间的划分和理解,与这种符码化的模式是一致的。 2 以消费为中心的城市结构 在《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的小说空间中,消费行为是极为常见的。差不多每篇小说,都会出现买卖交易、娱乐消遣等经济活动或消费行为。看电影、上外国餐馆或咖啡厅、到百货公司选购消费品、跑马场或回力球场消遣,都是小说里常常出现的活动。这些消费场所是新奇的城市空间,形成了商品和欲望的想像地理。消费的气氛洋溢于整个小说空间,依靠各种各样的消费行为,一个充满着中产阶级生活趣味的繁荣城市被建构起来,删去这些有关消费的情节,整个城市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空洞。 我们可以轻易地在两本小说集中找到许多有关城市消费生活的描写。《蝴蝶夫人》里的李约翰教授的太太,正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消费主义者。李太太是一个很会出门花钱的女士,她每天都要出门,花钱吃冰淇淋,烫头发,赌回力球,喜欢看电影、打网球、逛百货公司、坐汽车、吃沙利文的糖果,结婚几个月就花掉了李教授薪俸,弄得丈夫要向学校会计处预支薪水。[24] 除了作为消费者外,小说里亦有一些积极配合城市消费主义的人物。《特吕姑娘》里的秦贞娥,是永新百货商店香妆品部的女店员,由于第一天上班即受到部长训话的“感召”,她决意要“尽了我的能力使公司的营业得到尽量的发展”,她深信“公司和我的关系是企图双方繁荣的合作”,于是无时无刻不保持着她的好兴致,竭诚为顾客服务,甚至在必要时运用她的妩媚的姿态,使男顾客购买最高价的货物。[25] 消费行为在城市的空间中是如此普遍,它并不限于高薪的中产阶级,在一些小市民身上,亦可见到城市消费文化的踪影。在《妻之生辰》中,丈夫为与妻子庆祝生辰,决定要送她一份礼物。妻子生辰当天,丈夫在下班回家途中,考虑着要买点什么给妻子: 买一个插着寿烛的朱古律蛋糕送她罢?太贱了,太不切实用了。那么,买一套精致的“蔻丹”送她罢,买几种“何比甘”化装品送她罢。想想看,她近来企慕着什么东西呢?呃,她不是想着要一些新式的衣料吗?……[26] 后来,丈夫忽然发现自己不曾带钱出来(他把所有的薪水都交给妻子),于是打算“从妻子那儿提出十元左右来完成这次的生辰贺礼”。然而妻子却告诉他,家里只剩下七八元了。没有钱,于是礼物就落空了。虽然妻子没有责怪他,依然微笑着为他弄晩餐,但当丈夫吃着妻子亲手做的细面,却深深感到愁闷和自责。这篇小说描写的虽然是小夫妻的生活琐事,但其小说空间却是与消费城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丈夫由始至终都不曾考虑过要自己亲手做一份礼物,而是希望通过即日到百货公司购买消费品来达到送礼的目的。只有在经济繁荣,商店林立的城市中,这种即时性的消费逻辑和习惯才是可能的。
更有甚者,外地人一旦进入城市,亦无可避免地兴起消费的念头。《春阳》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蝉阿姨是来自昆山的三十五岁寡妇,乘火车到上海的银行开保管箱。年轻的时候,她为了得到未婚夫的财产,抱着牌位成亲,故此对钱非常看重,不舍得随便花钱。走在南京路上,蝉阿姨初时看见大廉价仍定力十足,然而,和煦的春阳,城市空间的明亮和活跃感染了她: 什么东西让她得到这样重要的改变?这春日的太阳光,无疑的。它不仅改变了她的体质,简直还改变了她的思想。真的,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为什么到上海来不玩一玩呢?做人一世,没钱的人没办法,眼巴巴地要挨着到上海来玩一趟,现在,有的是钱,虽然还要做两个月家用,可是就使花完了,大不了再去提出一百块来。况且,算它住一夜的话,也用不了一二十块钱。人有的时候得看破些,天气这样好! 天气这样好,眼前一切都呈着明亮和活跃的气象。每一辆汽车刷过一道崭新的喷漆的光,每一扇玻璃橱上闪耀着各方面投射来的晶莹的光,远处摩天大厦的圆瓴形或方形的屋顶上辉煌着金碧的光,只有那先施公司对面的点心店,好像被阳光忘记了似的,呈现着一种抑鬱的烟煤的顏色。 何必如此刻苦呢?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蝉阿姨不想吃面了。[27] 于是蝉阿姨决定大破慳囊,到冠生园好好的吃一顿午饭。蝉阿姨心理的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受到春阳的影响,另方面是由于上海物质文明(汽车、玻璃橱、摩天大厦)的诱导。上述引文之前的一段,写蝉阿姨走在永安公司附近,孱弱的她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好像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许多呈着喜悦的容顏的年青人的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走”。[28] 上海商品市场的诱惑是如此强大,当中流动着的欲望和喜悦,使进入其空间内的人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投入消费的行列。 另一个较为特别的例子是《雄鸡》。这篇小说的场景是城外的乡村。兴发婆婆一天想杀家里的一只雄鸡来招呼将要来访的兄弟,却发现雄鸡不见了。她怒骂了媳妇、责怪了孙子、质问了邻人,却依然遍寻不获。故事的结尾,兴发婆婆终于发现了真相,原来是公公早上把雄鸡带进城里去送给四太太。既取得了铜元,兴发婆婆也就再不耿耿于怀了,还积极地盘算要不要“再捉一只婆鸡去配配对”。[29] 在这篇小说里,城市是一个隐藏不露但影响了整个故事发展的因素。城市空间的引入,使雄鸡的意义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雄鸡平日对于乡下人来说,是招呼亲友的一味好菜;然而一旦引进了城市的因素,鸡只就成为了生财的工具,具有经济上的交换价值。这倒过来说明了,施蛰存小说世界里的城市空间,是与消费紧紧连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施蛰存小说中的城市空间,是围绕消费而建立的。处身这个空间的人物,或连结于这个空间的外来者,皆受到都市消费模式的影响。这些消费行为,又往往与其他欲望交织在一起。而这种以消费为中心的城市空间模式,正记载着30年代上海商品消费文化的现代经验。 3 印刷的共同体[30] 《狮子座流星》有一段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卓佩珊夫人在公共车偷看邻座报纸的情节。卓夫人看完医生回家途中,在公共汽车上碰巧遇到报童在卖报纸。卓家有订报纸的习惯,但却常常买了不看,当废纸卖掉。如果可能的话,卓夫人觉得最好可以只看戏报和广告。出于这个原因,她决定不买报纸,但报童的叫嚷却教她很想看看今天报纸上那有关扫帚星的新闻。车开动了,她注意到有许多人在看报纸: 《时报》、《大晚报》、《新夜报》,还有英文的晚报。这些人是不是都预备看扫帚星的?这是不是像月蚀一样的东西?是一颗很大的像扫帚一样的星呢,还是许多星排成一柄扫帚的样儿?今天晚上,人家会不会敲锣放炮呢,像前年月蚀的时候那样?她这样怀疑着。[32] 那些出现在各份报纸上的新闻,使卓佩珊夫人把扫帚星的出现想像成一件社会性事件。她觉得车上每个人,甚至整个上海市的人都在参与这件“三十三年一转”的盛事。可是,由于她没有看见过女人在车上买报纸看,始终都没有勇气拿出铜元来。她唯有耐心地等待邻座的男子把报纸翻过来,让她可以偷看到那段新闻,不料,那男子突然下了车。在家附近,她又听到管门巡捕和王公馆里的丫环在谈论这件事。后来她终于看到晚报上的报导,却发现上面写的却是“狮子座流星”,令她感到很疑惑。 在这篇小说里,施蛰存处理“狮子座流星”事件的手法,很容易令人想起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想像的共同体”的概念。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出,民族国家透过印刷资本主义、小说、记忆、官方语言、人口普查、博物馆等象征资本,和国旗、国歌、国家型的纪念仪式及节庆活动,让所有国民,都在阅读、想像、记忆的同时性和即时性过程中,设定大家同属一个社群,透过想像与形构共同的生活和行为规范,形成国家与公民的观念,产生归属感,以达成巩固民族国家既有的体制。[33]
报纸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它令读者们产生同属一个社群的想像。首先,报纸通过版头上时历的一致,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连结,大家依循同质的时间概念稳定前进。另一方面,报纸作为一种书的形式与市场的关系紧密相连。报纸或可看作是“单日的畅销书”,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告作废。这种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同一地区的居民俱在同时消费,几乎分秒不差。这个独自进行的仪式在同一个社群内、在同一时历中,不断地每隔一天或半天的就重复一次。“我们还能构想出什么比这个更生动的世俗的,依历史来记时的(historically clocked),想像的共同体的形象呢?与此同时,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像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34] 报纸出现在施蛰存的小说虚构空间里是极具意义的。这意味着他的小说空间里包含了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小说空间里的人物,不断透过报纸和广告,认识、分享、讨论、交流着属于同一社群的事情(流星、大廉价、电影消息等等),形成一个共同占据的想像空间。由是我们可以明白,城市空间在小说文本空间的再现,并不仅限于小说中的城市描述,却往往深入到空间想像的层面。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施蛰存小说中因印刷品(小说、报纸、杂志等)而组织起来的想像的共同体,有时甚至是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小说里不时出现外国新闻、外国小说,故事中人更会在阅后加以评论。例如在《狮子座流星》中,就曾出现任职华夏银行的国际汇兑部主任的韩先生,很专心地阅读报纸上的国际财经新闻的情节。[35] 此外,《凶宅》亦相当值得注意。《凶宅》的问世,是由于施蛰存“想利用一段老旧的新闻写出一点的刺激的东西来”。[36] 这篇小说所据的真实新闻蓝本虽未可考,但它确实透过插入一篇又一篇的“新闻”,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写出了带有心理分析意味的侦探小说。 小说是由叙事者回忆一件发生于1919年的非常轰动的事件开始的,其后引出以大宅闹鬼为烟幕,谋杀妻子的故事: 凡是在一九一九年,……也许是二零年,我可记不准了,秋季,每天看上海报纸的人,一定曾被“戈登路之凶宅”这连接着登载了好几天的新闻所耸动过的。尤其是住在上海的人,也许甚至还趁星期日假期的下午,当作散步似的,亲自到那边去探险过。但是,他们看见了什么没有?没有,除了极少数外国人以外,凡是在这新闻刊布之后三天去探察的人,他们一点也不会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因为当华文报纸上乐此不疲地一再记载这新闻的时候,这屋子的四周已经围起篱笆来,屋主人已经挂出了“此屋出卖”的纸牌。[37] 通过援引报纸,施蛰存首先将虚构的故事变成彷彿是上海人曾经共同分享过的热门话题,随后才慢慢铺陈戈登路凶宅的奇闻及真相。参照柯南道尔侦探小说征引报纸、广告的典型作风,整篇《凶宅》主要由报纸新闻推进,至少有四种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新闻:上海华文报纸、《英文沪报》、《巴黎晚报》、美国警察厅的供状(后三种俱已“译”为中文),被组织到小说里来: 节数 报纸 日期 地点 内容 一 上海华文报纸 1919/1920秋季 上海 “乐此不疲地一再记载这新闻。” 一 英文沪报 1919/1920秋季 上海 “像小说一样有趣味的记载”,报导戈登路之凶宅,屋主妻子及两位租客的妻子先后自缢身亡,引出凶宅之说。 二 巴黎晚报 1928年11月19至28日 巴黎 赝造珠宝商(屋主)的日记。日记由哈尔滨检察官吏在档案中抄出,交予在东亚旅行的巴黎小报记者,译成法文寄往巴黎刊出。 三 巴黎晚报 1928年12月上旬 哈尔滨 第一位租客从《巴黎晚报》所刊日记中,发现妻子与屋主的私情。他携着报纸往哈尔滨勒布朗律师事务所,意图兴讼。 四 美国警察厅的供状 1930年5月 美国旧金山 谋杀妻子的丈夫(第二位租客)被捕后的供词,供出自己如何利用吊死鬼的传说,谋杀妻子后,再捏造冤鬼寻找替身的假象。 在小说中,凶宅闹鬼的真相随着不同的报纸、状词的披露被逐步揭开,形成了一个跨境的侦探故事。饶有意味的是,这些报纸是全球流通的,并呈现出某种“全球视野”及“跨境效应”:一份巴黎的小报,竟报导并转载在远东落网的赝造珠宝商的日记,而这篇日记又偏偏被第一位租客读到,然后带回中国作为兴讼的证据;而故事的谜底,却最终在美国揭晓。透过“征引”不同的大众媒介,小说的空间想像被扩大了──这个空间以上海为中心,延伸至世界各主要国际城市,以至形成跨文化与跨地域的连系。
虽然施蛰存在小说的虚构空间里所建构的,不过是“想像的‘想像的共同体’”,但我们不妨将这种模式与30年代上海现代城市经验联系起来并加以考虑。在30年代上海,报业已经非常发达,加上面向国际,当时上海的报纸,不只报导本地的新闻,同时会透过外电翻译来报导国际消息。与此同时,海外报刊亦在上海设有销售点。在施蛰存的小说空间里,报纸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30年代上海的现代性经验、族群想像,以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或者,我们可进一步用一种“颠倒”的方式,来表述这篇小说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在这篇小说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并不是再现的客体,而恰恰是小说生产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有关大众媒介的想像,及由此而来的想像的世界(imagined worlds)[38] ,这篇小说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都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大众媒介(这里主要是报纸)一方面创造了作者的空间想像,给予其小说生产的条件;而这些包含现代空间想像的小说,又反过来在大众媒介中进一步建构了自身及读者对于城市、甚至于全球的空间想像,回环往復,生生不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设想的背后,翻译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施蛰存小说中的跨文化跨地域媒介地形[39] ,亦是建基于中、英、法文的互译性,以及国际新闻的传译事业。施蛰存作为翻译家的身份 [40],似乎让他特别能注意到不同语言之间流通及互译性的问题。于是在《狮子座流星》中,才会出现卓佩珊夫人对于“狮子座流星”是否等于“扫帚星”的疑惑,而《凶宅》的跨国侦探故事,亦因着翻译的因素而可以一直说下去。换句话说,翻译是以上两篇小说所体现的文学地形的条件。正是由于翻译,小说中以上海为核心的空间想像才能建构起来,而小说的读者,才能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上海是与欧美大国同步和接轨的国际大都会,而小说所提供的世界想像亦由是诞生。 4 新的城乡结构 吴福辉曾指出,施蛰存身上具有“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性格”。[41] 他认为施蛰存早期的小说写作,“作品气息有赖于江南城镇的回忆”,而当心理分析小说进入较成熟的时期,便“一律是乡镇进入都会那种‘文化碰撞’的结构”。[42] 吴福辉具洞察力地点中了拆解施蛰存小说的重要原则,不过,需要追问的是,我们该怎样理解施蛰存小说中那普遍的“乡村与都市”的舞台背景?在“文化碰撞”的结构下,城乡关系又是否出现了新的形式? 城乡的二元对立,其实早在《上元灯》中已侧面地表现出来。《上元灯》“大部分的小说都是用怀旧的情绪来表达少男少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43] ,它一方面汲取了西方小说的章法,另方面又充满了东方文学的神韵和气质,兼具晚唐诗的意境(如《扇》被认为包含了《七夕》“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意境)。[44] 总体来说,《上元灯》在情调上与中国古典文学互相呼应,与文学传统的承传关系十分明显。在这种古典抒情传统的影响下,在《上元灯》、《周夫人》、《扇》等一系列小说中,城市边缘的小乡镇一律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氛围。相较于施蛰存日后书写的流动城市空间,早期作品中的乡村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宁静而美好,乡村中互相认识的居民构成关系密切的共同体。 相反地,《上元灯》中的城市却被呈现为罪恶的根源。在《渔人何长庆》中,菊贞的逃婚出走,是因为她不满足乡村的生活,向住大都市的繁华: 实在,菊贞对于长庆并没有什么恶感,但如果有一天她的父亲要是说出将她嫁给长庆的话,她也许竟会得反对的。她有着很大的希望,她曾经随着她父亲进城去,看见了城里的奢华;她曾有过从上海回来的女伴,听见了大都会里的新奇;……她常悠然想起许多美丽的运命来。啐,嫁给长庆吗?吃一世卖剩下来的死鱼儿吗?[45] 在此,都市文化被描写成一种诱惑,乡村的少女憧憬着都市的物质生活,揭示了现代都市文化对传统农村平静生活的强大冲击。在《渔人何长庆》的结局中,长庆从上海领回沦落风尘的菊贞,重新在乡村过着自食其力的平淡生活。由这个结局来看,《上元灯》时期的施蛰存,仍然视乡村为心灵的平静归宿。
民国上海街头一角 不过,编入同一集子的《闵行秋日纪事》却泄露了改变的契机。在《闵行秋日纪事》中,叙述者(我)应友人邀请,到闵行小住,在车上看见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女子,后来汽车遇到意外,只能徒步前往目的地。途中他与这美丽的女子攀谈,觉得这个拿着大包裹的单身女子处处透着诡异。后来在镇上他又遇见了她,暗暗跟踪,发现她好像在作非法的勾当。一天晚上他又跟踪她,却差点被子弹打中。后来才从朋友的仆人口中得知,她常常到上海去私带鸦片和吗啡,再派人用小船偷带到城市贩卖。 吴福辉曾指出,“《闵行秋日纪事》叙事的神秘色彩,扑朔迷离,也始终是他小说的一个特点”。[46] 尽管作者把叙述的线索放在历险者“我”对该名陌生女子不由自主的着迷,在历险的情节之上建立了另一复杂的心理层次,这篇小说读来仍很像一篇历险故事。与《渔人何长庆》相似,小说中的城市总是与罪恶(贩毒)相关,但这篇小说特别地方在于叙述者的身份。他是一个往乡郊渡假的城市人,闵行之旅赋予他展开无穷的浪漫狂想(fantasy)的机会,但却无法使他摆脱城市罪恶的干扰。《闵行秋日纪事》的重要性在于,它预示了施蛰存日后的乡村梦魇之旅,折射出城乡结构变化的征兆。 施蛰存对于离奇、神秘的事件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他《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的创作中。《魔道》、《旅舍》、《夜叉》,讲述的依然是城市人在乡郊遇到的传奇的神秘故事。不过,随着进入都市日久,施蛰存的小说风格早已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与昔日安详的、充满怀旧色彩的小说渐行渐远。在中期以后的创作中,乡村(或小乡镇)对施蛰存渐渐失去原有的意义。乡村不再是理想的寄託、心灵的归宿,却成为了城市梦魇的延续。主人公不但是留在城市的陌生人,他亦是乡村的陌生人。他虽然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可以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回到乡村,但乡村早已不是他熟悉的空间,乡村的乌托邦想像亦早已失落,陌生的感觉无处不在,而因城市压力而诱发的精神病,亦终在陌生而格格不入的乡村空间中爆发。 例如,《魔道》就是一个充斥着幻想的“妖怪”故事。与《闵行秋日纪事》一样,这篇小说的开端写主人公接受朋友的邀请到郊外作客。在乘火车的途中,主人公碰见了一个神秘的老妇人。在各种文学文本的互相影响下(西洋妖妇骑扫帚捕捉小孩、《聊斋志异》中的黄脸老妇、The Romance of Sorcery中的妖术),主人公开始认为坐在对面的老妇是个妖妇,感到十分恐惧,产生了种种可怕的联想。到了朋友家中,他仍不时看见老妇正在远远地窥伺着他。更为严重的是他出现幻觉,以为朋友的妻子也是那个妖妇的化身,于是他逃回城市,老妇的身影和幻觉却仍然挥之不去。
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狂想,但它同时是施蛰存小说出现新城乡结构的标记。小说中的乡村不再是宁谧之地,反而是一个比城市更使人不安的空间。骤眼看来,乡村和城市彷彿是两个不同的空间,但对于主人公来说,两者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并无二致,同样充满无穷无尽的陌生感和对熟悉事物的恐惧(uncanny)。城乡的二元对立被取消了,熟悉的事物无法带来安全感,代之而起的是永远无法摆脱的陌生和不安的感觉,无论在城市抑或乡村,陌生人的梦魇始终紧随身后。 《夜叉》和《旅舍》是上述故事的变奏。小说中那些想往乡村舒缓紧张情绪的都市人,往往在乡村里仍不断疑神疑鬼,为恐怖幻觉所困扰,精神更形紧张。在小说的世界里,乡村始终笼罩着来自城市的阴影,患上神经衰弱的城市人始终无法在宁静的乡村生活中得享片刻的慰藉,旅店里的一张床,一个平凡的女子,都使主人公徨恐万分,甚至精神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古典文学传统亦在这个新的城乡结构中产生变化。《夜叉》征引了古典志怪小说中的传统女鬼形象,并将之与恐怖的心理幻象编织在一起。《夜叉》是一个都市人在乡村怀疑遇到“鬼怪”的恐怖故事,主人公乘小船游览古庵,瞥见一个浑身白衣的女性。这个白衣女子本来只是个普通女子,但是在男主人公所阅读的传统志怪小说的互文作用下,她最后“化身”为夜叉: 这是一世纪以前的事情,是的,书上这样说。但文字的力量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读了这样的记载,我也有些恐怖了。我想像一个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在月影萧森的山坡上疾走,一忽儿就不见了。再停一会,我又在林隙中窥见一个满身缟素的女子,似进似退地在掩映着。夜叉,这就是我所猜想得出的夜叉。但是我曾经看见过夜叉吗?谁知道?当他变形的时候,你当面看见了也不会觉得的。譬如……譬如什么呢?哦,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刚才在小芦篷船中所看见的那个妖异的白衣女人,谁敢说她一定不是夜叉的化身呢?[47] 这里的“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指涉了《楚辞》的《山鬼》,而“满身缟素的女子”则使人联想起《聊斋志异》等传统志怪小说中常见的女鬼形象。对传统文本的征引,不但造成了传统古典小说和现代派小说两个不同语境的文本的汇合,更使小说中白衣女子的现代女性形象与古典文学的女性形象重叠起来。不过,汇合的结果并没有召唤出早期《上元灯》纤细柔和的气氛,亦没有造成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些古典的志怪文本,与《魔道》中的文学文本一样,最终服务于作者对现代城市空间无处不在的精神压力的书写,使其对人的精神状况的扭曲更显得无远弗届。 五、结语 黄继持曾指出,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作品跟西方文学“现代性”关系最密切的,是诗坛上的“象征派”和“《现代》派”,与小说的“新感觉派”。他认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以其主观世界之强调,接近西方现代小说的作风。但移植过来,却与中国现代化阶段脱节,只能暂时寄生于上海。”[48] 毫无疑问,作为以上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蛰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例子。 本文透过引入地理和空间视角,从文化地理学出发,阅读和分析《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两部短篇小说集中的文学地景,探讨施蛰存小说的空间是如何产生、说明和体现了现代人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总括来说,这些小说里对地理和空间的想像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其特点包括了空间的流动性与符码化、以消费为中心、印刷的想像共同体的存在,以及新的城乡关系。这个存在于小说内部的空间,虽然是虚构的,但所展现的空间模式和生活经验,却与上海30年代的现代生活经验互相重叠。 前文提到,施蛰存表示过并非所有在都市的人都是都市人。这令人想起了曾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沈从文。正如李欧梵指出,沈从文的小说世界是“怀旧式”(nostalgic)的,他“把湘西的乡土变成一种神话”。[49] 与“土绅士”沈从文比较起来,施蛰存选择了直接回应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作为一个现代派作家,他以一种有别于现实主义的方式,演绎他在上海所体验到的现代性经验。当茅盾通过深入的考察和数据分析,写成他的巨著《子夜》,暴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巨大影响;[50] 施蛰存则以一种可能是更为偶然的方式,侧面记录了30年代上海市民的个体生存经验。他的作品虽然专注于心理分析及私人琐事,但却在无意之中,将他所感受到的上海现代经验同步复制或翻译到他的小说空间之内。当注意的是,这种翻译再现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城市,它没有将整个上海全都搬演到小说世界中(至少没有同期左翼作家主力表现的革命运动),而是透过保留现代都市的内部逻辑,把隐藏于城市文本中现代性经验彰显出来。在这样的空间中弥漫着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最吊诡的是,30年代不少上海市民,正好是透过阅读现代派小说,想像自己属于一个世界主义的现代都市共同体。而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最终深刻地把握文学文本的实际性质,以及地理文本的想像特性。 [1] 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5页。原著请参见: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4. [2] 同上,第69-70页。 [3] 同上,第116页。 [4] 同上,第70页。 [5] 同上,第104-105页。 [6] 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译:《文化地理学》,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页。原著请参见:Mike Crang,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7]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第3-4页。 [8] 有关地理学中这两种不同研究观点的辩论,可参见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第7章, 第133-157页。 [9]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第11-15页。 [10] 同上,第58页。 [11]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 参见Yingjin Zhang,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L.A, Lond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3] 笔者认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可以1932年为分水岭。1932年,施蛰存开始为现代书店主编《现代》,并创作了很多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就是稍后结集的《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这些小说与前期的《上元灯》不同,不再眷恋于宁静安详的江南风光与古典情调,并将《将军底头》以来对于心理分析手法实验,运用到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之上。 [14] 不过,由于老家在松江,加上有一段时间在松江教书,施蛰存仍不时往还于城乡之间。参见《施蛰存年表》,《施蛰存(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应国靖编,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11-316页。 [15] 郑明娳、林燿德专访:《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与新感觉大师施蛰存对谈》。《联合文学》第6卷第9期。 [16] 据1999年12月张芙鸣对施蛰存的访谈。参见张芙鸣:《漫论施蛰存》。《面对都市丛林——〈香港文学〉文论选》(陶然主编,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12页。 [17] “《现代》派”,指《现代》杂志所发表的那种风格和形式的诗(及文学作品)。参见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8]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施蛰存对现代诗的看法,亦可参见《支加哥诗人卡尔•桑德堡》。《现代》,第3卷第1期。 [19]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年8月),第62页。 [20] 盖奥尔格•西美尔著、林荣远译:《关于陌生人的附录》。《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译本按德文原著Soziologie译出。 [21] 同上,第512页。 [22] 成伯清著:《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23] 施蛰存:《梅雨之夕》。收入《梅雨之夕》。据《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24] 施蛰存:《蝴蝶夫人》。收入《善女人行品》,《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页。 [25] 施蛰存:《特吕姑娘》。同上,第105-111页。 [26] 施蛰存:《妻之生辰》。同上,第54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27] 施蛰存:《春阳》。同上,第59页。 [28] 同上。 [29] 施蛰存:《雄鸡》。收入《善女人行品》。《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第77-87页。 [30] 本节的初稿曾以《印刷的共同体——重读施蛰存的〈狮子座流星〉及〈凶宅〉》为题,发表于《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0-216页。 [31] 卓佩珊夫人是这样设想的:“最好能够单定一张本埠增刊,翻翻戏报就够了。……不过,也难,大廉价的广告又都登在第一张。……看广告常常容易上当,多花费,今天早上要是不看见这医生的大广告,这一趟也就省掉了。呃,明天准定叫阿蓉回了。……再不然,就定一份便宜点的,横竖有大事情的时候好再定。”施蛰存:《狮子座流星》。收入《善女人行品》。《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第5页。省略号为原有。 [32] 同上。 [33] 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版,第140-142页。 [3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6页。安德森对小说、报纸与族群想像的关系之讨论,详见《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7-47页。原著请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35] 以下是韩先生阅报时喃喃自语的评论:“一先令便士六二五,正二月份,六八七五,哦,麦加利吃三月一先令九便士七五,花旗吃十二月五六二……汇丰……卖出?……英法要求停付美债。靠不住。美国一定拒绝,……而且……若使法郎英镑折美金算,难说……”施蛰存:《狮子座流星》。《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第9页。省略号为原有。 [36] 施蛰存:《〈梅雨之夕〉自跋》。《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07页。 [37] 施蛰存:《凶宅》。收入《梅雨之夕》。《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第352页。 [38] 阿帕杜莱(Appadurai)语。参见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96), P. 27-47. [39] 根据阿帕杜莱的说法,所谓“媒介地形”,既指“生产和传播信息的电子能力的分配(报刊、杂志、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亦“表示这些媒体所创造的世界形象”。而它们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们能够向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形象、叙事和人种图景”。阿帕杜莱著、陈燕谷译:《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2页。 [40] 施蛰存从事小说创作不过十年,但他的翻译事业却跨越半个世纪,直至1987年,仍有新译作出版。1949年以前,施蛰存翻译的主要是欧洲各国的小说,长篇短篇俱有,其中又以奥地利德语作家显尼志勒的小说为最多。 [41]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42] 同上,第79页。 [4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4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1-682页。 [45] 施蛰存:《渔人何长庆》。收入《上元灯》,《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第58页。 [46] 吴福辉:《施蛰存短篇小说集•前言》。《施蛰存短篇小说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7] 施蛰存:《夜叉》。收入《梅雨之夕》,《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29页。 [48] 黄继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及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文学》,香港:牛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49]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现代性的追求》,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99-200页。 [50] 有关茅盾笔下的上海空间,陈晓兰曾有仔细的分析。参见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你在人间游历 爱是最壮观的迁徙 像万只候鸟和蝶群 从第一眼抵达心底 后来你成为牧民 赶来云海繁星 脚旁驮岁月的白驹 将漫生春草嚼咀 当你站于隆冬爱河边 俯身朝下望去 有人破冰做你 一生倒影 你会凝视他 如同另个自己 直到你的热泪都化作潮汐 爱即永恒汛期 最终你所历风雪 开遍梅花鹿背脊 当你仍是虔诚滋养着 参天铁树的泥 有人做撼动你 一生马蹄 你会信奉他 如同整个奇迹
保马 微信号 : PourMarx
|
【本文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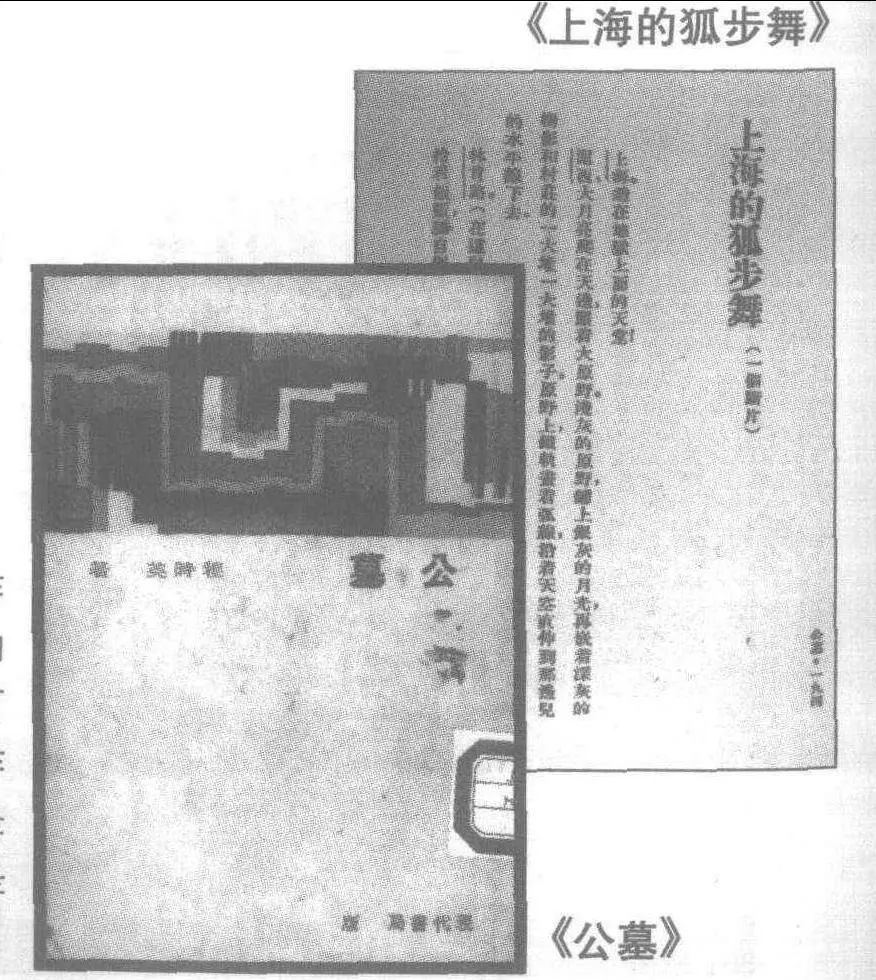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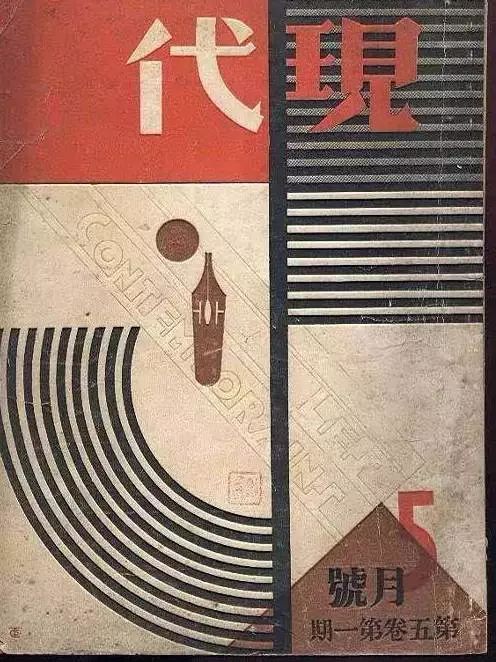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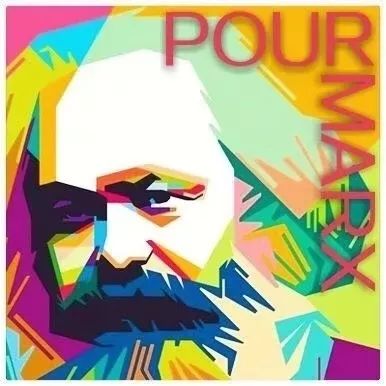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