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来:《大学》的文本地位与思想诠释(一)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如何理解三纲领八条目及其内在关系的内容 › 陈来:《大学》的文本地位与思想诠释(一) |
陈来:《大学》的文本地位与思想诠释(一)
|
陈来先生通过《大学》的作者和时代、《大学》的古本与改本、《大学》的思想与诠释这三个方面,对《大学》,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本文先从第一部分给大家讲起。 " 《大学》的作者和时代 1 《大学》的名义 名就是题名,义是这个名字的义含。《大学》本来是《礼记》的第42篇,其篇题原本就叫做《大学》,这篇到南宋以后被朱熹合编为“四书”中的一种,四书就是《论语》、《中庸》、《孟子》、《大学》。因此,《大学》成了独立的一部书,这样“大学”就成为了书名。 对于这个篇名的意思,古代就有一个说法,最早见于东汉的经学家郑玄。什么是“大学”,《大学》这个篇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 “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就是说《大学》主要是讲博学,当然这个博学虽然是这篇的主旨,但它最后的目标还是要引导到为政上,这是郑玄的解释。 这个解释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历史上当然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到了南宋,朱熹解释为什么叫《大学》呢?说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是相对于少年来讲的,也就是成人。后来,王船山也讲到“大人者,成人也”,15岁以上进大学,那是成人,15岁以前进小学,那是少年,不是成人。按这个意思来讲,《大学》不是仅仅讲博学,它是适合于成人的一个教育文献。可见,这与郑玄的说法有所不同。 其实关于《大学》的名义,古代有些文献是可以拿来参照的,与《大学》同在《礼记》中的《学记》篇多次提到“大学”这个概念。比如现在的《大学》篇一开始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是《学记》篇一上来讲“大学之礼”,《学记》里面也讲“大学之道”,说“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此外,《学记》里面还提出了“大学之教”,教就是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宗旨。除了“大学之教”还提出了“大学之法”,《学记》里面讲“大学始教……”。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学》这篇文章的名义应该与《礼记》里面所包含的这些“大学”的论述是一致的,一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大学”其实不是讲博学,而是古代教育的一个设置,古代在都城设立大学,西周时期叫做国学,是当时设立的一种最高规格的教育学校。所以,“大学”是讨论古代大学教育之法、教育之礼、教育之道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郑玄用博学来解释大学,是因为他忽略了古代关于“大学”的这些记载。
刚才我说《大学》是在《礼记》的第42篇,这是《小戴礼记》,《大戴礼记》也提到了“大学”,说“古人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八岁开始就到外面学习,学的是小术,“束发而就大学,学大术焉”,这个也讲得很明白,大学是跟小学相对的,与前面我们讲的朱熹和王船山所讲的大学是15岁以上成人的一种学校是一致的。小学和大学的区别,小学是学小艺的,大学是学大艺的,那什么是小艺呢?后来朱熹对此做了一个区分,小学主要是学习礼节、仪节,大学主要是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层次比较高,定位也比较深。 这是我们首先讲的第一个问题, 大学的名义,如果我们用朱熹的话来总结一下,“《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古者八岁皆入小学,十五皆入大学”,所以大学之道就是大学的教育之道。 2 《大学》作者 《大学》的作者在唐代以前没有人讨论过,没有人叙述过,也没有提到过。北宋的“二程”就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这话说得有一点含糊,孔氏当然是孔子,孔氏的遗书,一个理解就是孔子流传下来的,是孔子所写的。而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就是孔门之遗书,当然这个孔门对于古代来讲,不是讲整个儒家,主要还是讲先秦孔子到七十子这个时代,孔氏之遗书。到了南宋,朱熹继承了这个说法,朱熹早年就说得比较坚定, 他认为《大学》是“累圣相传,至于孔子,而笔之以书”,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二程”所讲的“孔氏之遗书”,朱熹直接把它解释为“至于孔子而笔之以书”,认为是孔子所写;“其门人弟子又相与传述而推明之”,他的门人弟子进行了传承、论述和发展。所以,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共同写成了《大学》这本书,他早年是这么肯定地讲。朱熹晚年时,对以前的说法做了点调整,他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他没有说这一部分是孔子写的。什么是经一章呢?就是我们上来看的“大学之道”那一段,我们也叫《大学》首章,这第一章朱子认为是经,后面是传。说经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孔子讲的话,曾子就把它传述下来。然后说 “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经一章后面还有传十章,这十章是谁写的呢?是“曾子之意”。经一章是孔子的意思,曾子只是把它传述下来,传十章是曾子的意思,“而门人记之”,门人把它记下来。所以,这样一来“孔氏之遗书”就落到孔子和曾子两个人身上,曾子做了大部分——“传十章”,这是朱熹对于作者的论断。
朱熹 那这个论断有没有什么根据呢?朱熹说“正经辞约礼备,言近指远,非圣人不能及也”,说这个经一章用辞很简约,但是道理很完备,好像说得很近,但包含的意思非常深远,“非圣人不能及也”,你看它那个语词和意思,只有圣人才能讲出来这句话。他说“至于传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与《中庸》、《孟子》者合,则之成于曾氏门人之手”,为什么说传十章是曾子写的呢?那传文里面引了曾子的话,他怎么不引别人的话,而只引了曾子的话?而且其中讲的内容又与《中庸》、《孟子》相合,因为《中庸》、《孟子》与曾子的思想也是相同的。当然,《中庸》、《孟子》可直接联系到子思,但是在朱熹看来,曾子与子思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说“则之成于曾氏门人之手”。 我们知道清朝有一个学者叫戴震,小的时候跟他家里私塾的塾师讨论过《大学》作者的问题,塾师告诉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当时戴震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朱文公是什么时候的人?朱文公怎么知道是孔子所言,是曾子记述的?曾子之意,曾子门人记述的?当时那个塾师无以应,答不上来。其实朱熹自己有一个解释,说我何以知道如此,他有一套自己的根据,但是这个根据能不能坐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私塾的老师水平也不太高,他并没有看到朱熹对这个结论来源的说明。 但是, 从二程到朱熹的这个讲法并不能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南宋有一位心学思想家叫做 杨简,杨简就不赞成,他认为《大学》非孔门之遗书,与“二程”、朱熹的立场是对立的。因为他是陆九渊的大弟子,因有“朱陆之争”,所以他反对朱熹的讲法,也反对朱熹所根据的“二程”的说法。他主要所针对的内容是“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后来把它称为三条纲领,后面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八条目。杨简针对这八条目讲“何其支也?”,怎么这么支离,说“孔子无此言”,“孟子亦无此言”,孔子没这么说,孟子也没这么说。那孔子怎么说的呢?他说“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汉代儒学根据《说苑》《孔子家语》的记载,说孔子讲过“心之精神是谓圣”,这句话我们在先秦的文献里还没看到。杨简说“孟子道性善”,孔子说心之精神是圣,性是善,心如果是圣的话,那心怎么能不正呢?他说 “何用其正其心,又何用诚其意,又何须格物?”所以他的结论是“《大学》非圣人之言,亦可验者篇端无‘子曰’”。进一步可以证明的一点是什么呢?这篇文献里没有“子曰”。比如《中庸》,一上来有好多“子曰”,但是《大学》里没有“子曰”,他说这怎么能说明这是圣人的遗言呢?所以《大学》非圣人之言,非孔门之遗书。这就是南宋的心学家提出的一种不同看法,当然他也没有确定《大学》的作者,他只是对“二程”和朱熹的讲法表示不赞成。
刘宗周 到了明代,明末一位大思想家 刘宗周是这样讲的,他引的话其实不是他自己独创的见解,是汉魏人常说的一句话 “子思惧圣道之不明,乃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就是说《大学》、《中庸》的作者是子思。《中庸》的作者我们知道是子思,汉朝人就是这样讲的。汉魏人说《大学》的作者也是子思,为什么作《大学》呢?“惧圣道之不明”,就是圣人之道没有彰显、彰明,要进一步发扬它。怎么发扬呢?作了两本书,一个是《大学》,一个是《中庸》,这两个的关系是一经一纬。这是刘宗周当时讲的。但是这个话并不是他的创造,因为汉魏时期已经有过这样的讲法。这种讲法就认为《大学》和《中庸》一样,它的作者是子思,应该说这个讲法比起“二程”的讲法更有渊源,因为汉魏时期已经有这样的讲法。当然,后来朱子说“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关于《大学》的作者,最后我们可以提到清初一位思想家的说法,作为一个补充,就是 陈确,陈确其实是刘宗周的学生。在刘宗周活着的时候,因为《大学》里讲“格物致知”,他曾经讲过这样一话,他说“前后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就是到了明末的时候,他当时能看到的专门讲“格物致知”的书有72家。我们知道所谓讲“格致”的其实都是讲《大学》的,不会离开《大学》另讲“格致”。可以说至少在刘宗周的时代,他看到的就是72种关于《大学》的著作。其实,今天如果收集关于《大学》著作的目录,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说“求其言之可以确然俟圣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见。”就是这72个人都讲“格物致知”的意思,但真正讲得好,可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我还没看到。他对宋代以来讲《大学》的各种文献也好、学术也好,他是有所不满的。陈确比他更进一步,不仅对宋代以来讲《大学》的这些学术有所不满,他干脆不承认《大学》是孔、曾所作,也不承认《大学》是圣人之言。他说 “《大学》首章非圣经也”,不是圣人做的经文, “其传十章非贤传也”,不是贤人作的传文。这就是彻底针对朱熹推断经传的作者分别提出反对。“《大学》首章非圣经也”,那就不是圣人所作,不是孔子所作,“其传十章非贤传也”,那就不是孔子门人这些贤人所作的。那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知道它不是呢?他从知行观的角度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学辨》,说 “《大学》言知不言行”,《大学》只讲了知,没有讲行,《中庸》还讲了笃行,《大学》只讲格物致知。他说“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这个道理有点偏,因为那时候禅宗还没出现,佛教还没进来,所以《大学》怎么是禅学呢?然后他说 “不知必不可为行,而不行必不可为知”,所以他的知行观其实比较接近于王阳明的知行观,他是从知行合一这个角度来讲,批评《大学》讲知不讲行,从而推断出《大学》不是圣人之言。 这是历史上关于《大学》作者的几种说法,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3 《大学》的时代 《大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三纲领、八条目,特别是八条目里面所讲的,从修身到平天下这个连续的论述,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就有类似的思想。《孟子》里面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与《大学》所论述的那个逻辑是一致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另外,类似的思想见于《礼记》里面的《乐记》,《乐记》里面引用了子夏的话,说“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这与《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一致的。因此,《大学》的基本思想应该说与《乐记》、《孟子》的时代相当,同处于一个大时代。前面讲了《礼记》里面的《学记》很多地方讲到大学之道、大学之礼、大学之法、大学之教,说明它和《大学》篇首所讲的大学之道的讲法也是相互呼应的,应该也是处在同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笼统的说,《大学》的时代应该是在战国时代,因为它的思想与战国时代的儒学很多讲法都是一致的。 如果说具体在战国的前期、中期还是晚期?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以前很多学者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梁启超认为《大学》这本书应该在孟荀之前,不仅在荀子之前,也在孟子之前,这就比较符合朱熹的推论,就是曾子和他的门人,七十子及其后学的这个时代。孟子稍微晚了一点,孟子是学于子思之门人,还不是七十子和他们的门人那个时代。但是,也有学者不是这样认为,比如胡适,他还是赞成梁启超的说法,但是劳干认为《大学》应该在《孟子》之后。后到什么地方他没说,可能应该在战国中期的后面。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在战国的晚期,甚至还有认为它是秦汉时代,最晚晚到汉武帝时期。 今天大多数学者都不再认为《大学》的成书时间是在秦汉或者汉武帝时期那么晚,而是认为《大学》应该是战国时期儒学的一个代表性作品。这个结论的得出当然是吸收了我们近40年来或者更长时间以来考古学关于古文献的发现带给我们对古书新的认识,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说了。 ◎本文原载于《大学解读》 (《大学》的文本地位与思想诠释)
|
【本文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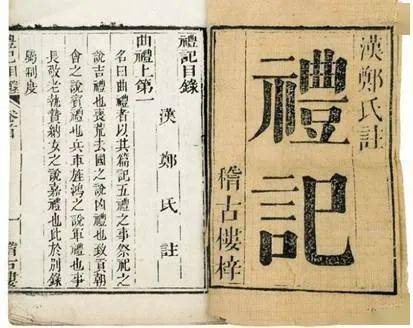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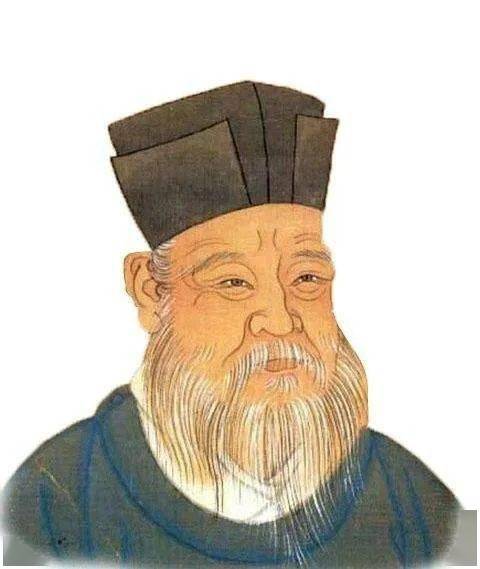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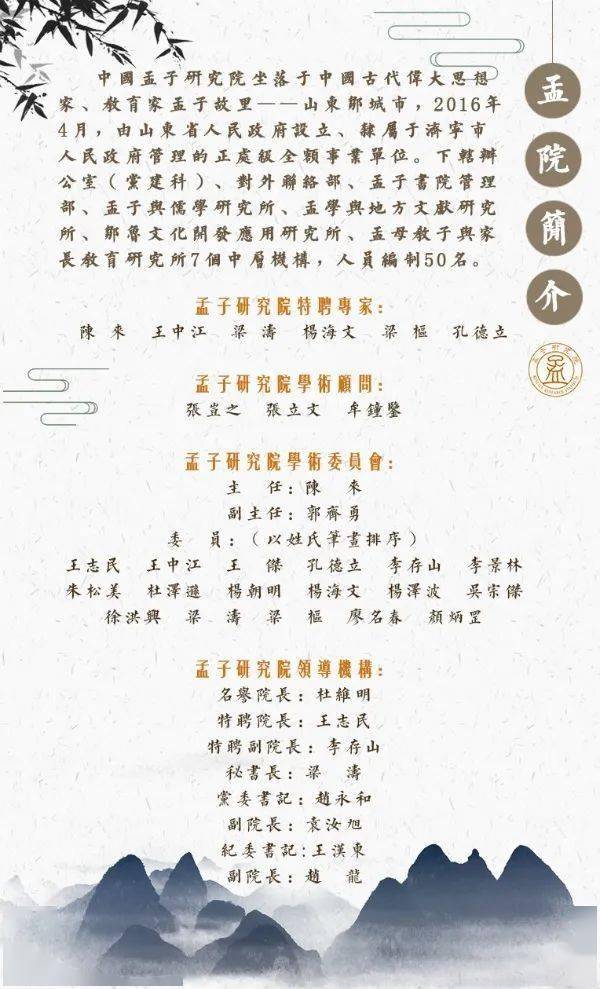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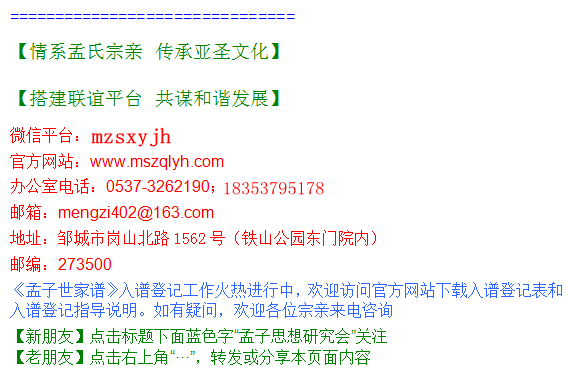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