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华:从牙医到作家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余华著名的作品是什么 › 余华:从牙医到作家 |
余华:从牙医到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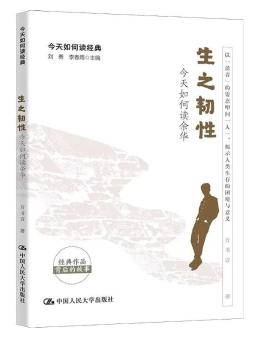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 《生之韧性——今天如何读余华》 万书言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一份工作——拔牙 高考失利以后,18岁的余华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到工厂工作,而是在他父亲的介绍下,到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牙医。余华的父亲觉得医生这个职业还不错,希望余华也能像他一样一辈子从医。在当代社会,牙医这个职业受人尊重,而且收入还不错,但是过去这个行当的地位却远远不如现在的医生。 余华自己也曾提到:“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拔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虽然是在国家的医院工作,但其实余华所工作的武原镇卫生院非常小,小到当地的百姓都不觉得这是一家医院,所以很多人都直接称其为“牙齿店”。此外,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当时武原镇卫生院里的牙医都未上过医学院,未经过专业训练。所以,在当时的余华看来,自己并不像一个专业的牙医,而更像是一名店员。 令人惊讶的是,余华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师父安排给病人拔牙。那一天,卫生院的院长安排余华跟随一位牙医学习拔牙。余华的师父姓沈,年近七十,原本已经在上海退休了,但因为舍不得放弃拔牙的工作,所以又在退休后回到武原镇卫生院,重新回到拔牙的岗位。余华第一次被院长带到沈师傅身旁时,沈师傅正在给人拔牙。因为无暇顾及其他,所以当院长向沈师傅介绍了余华之后,沈师傅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安排余华站在旁边观察他是如何拔牙的。在拔牙之前,沈师傅首先用棉球将碘酒涂到病人的上腭或者口底,接着注射麻醉药。 在等待麻醉药发挥药效期间,他便坐在椅子上抽烟。等到病人的舌头变大,他就开始准备用钳子拔牙。直到现在,余华对第一次看人拔牙的过程都印象深刻。没想到的是,在观察了两次拔牙的过程之后,沈师傅便让余华亲自给病人拔牙。这对于对牙医工作几乎一无所知的余华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虽然当时的余华非常紧张、手足无措,但为了不让病人起疑心,他只好装作非常镇定,学着沈师傅拔牙的步骤,给病人麻醉,询问病人舌头的变化,然后拿起钳子拔牙。 幸运的是,因为这个卫生院的病人主要是农民,而农民一般都是到牙不得不拔的时候才会去拔牙,所以余华在拔牙时很容易发现哪颗是需要拔的,拔牙的过程也就非常顺利。之后的日子,余华与沈师傅配合得天衣无缝,一般简单的拔牙都由余华处理,沈师傅则负责写病历和开处方;如果遇上比较复杂的情况,沈师傅就会亲自上手。 平时,沈师傅也对余华非常照顾。只要沈师傅从上海回来,就会给余华带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地塞给他,不让其他同事发现。在沈师傅的关怀与指导下,余华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从第一次进入卫生院工作到离开卫生院,余华所拔的牙齿有一万颗。 《我的第一份工作》(节选) 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次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当时我胆战心惊,心想自己还没怎么明白过来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在等待麻醉的时候,我实在是手足无措……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就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我第一次拔牙的经历让我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一排大小和形状都不同的钳子时,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一把。于是我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欠起屁股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他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了…… 就这样,这份工作余华一干就是5年。虽然这5年中余华在大家的照顾下成长得非常快,但他不甘心一辈子都在医院拔牙,不想过着每天8小时工作的生活,更不想过着天天看着别人嘴巴的日子。 空闲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站在医院的门口,望着车辆川流不息的街道,不断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难道我能一辈子待在医院吗?余华自己也曾在文章中提到:“我实在不喜欢牙医的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面对着别人的口腔,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 当时的余华非常羡慕在文化馆工作的人。因为余华所在的医院与文化馆很近,两个单位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百米,所以余华经常在医院的门口发现文化馆的人员在街边闲逛。有一次, 余华终于忍不住问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你们为什么总是在街上晃来晃去,难道不用工作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笑着告诉余华,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余华一听非常震惊,原来还有工作是这么轻松的。在余华看来,文化馆的工作就像是天堂一样,极其自由、悠闲,不像在医院拔牙那样枯燥乏味。余华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进入文化馆工作。 在当时,要想进入文化馆工作,要不就是会作曲,要不就是会写作、绘画。在这三项中,余华觉得作曲和绘画自己不太会,自己也就对写作比较感兴趣,所以余华决定开始创作,努力争取早日进入文化馆。 可见余华一开始从事写作的动机并不是想要创作,而是为了摆脱当时自己所处的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在知道余华要开始创作这件事后,与余华一同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的医生马上给余华泼冷水。他也曾和余华一样,非常热爱文学,尝试过写作。他劝余华不要再做白日梦:“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 年仅20岁的余华并没有因为朋友的反对而放弃创作,他回应那位医生朋友道:“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一开始,余华也不太清楚如何创作,所以他特意拿着一本《北京文学》反复观摩。 等到大致了解了之后,他就开始创作,并将自己的作品寄往各大杂志社。当时写作的条件非常艰苦,因为余华当时还在医院工作,所以他不得不在上午工作,晚上写作。夏天的时候非常热,为了不让自己的汗滴到稿子上,余华只好在手上绑上毛巾。 一开始,余华的稿件也经常被退稿,所退的稿件经过的城市比他自己去过的地方还多。每当他的退稿被扔进他家院子时,余华的父亲一听“吧嗒”的声音就知道是余华的退稿,便大喊一声:“退稿来了。” 有一天,余华在医院拔牙的时候,医院的电话响了,电话里的总机告诉余华是来自北京的长途。余华就一直待在电话旁等,直到快要下班的时候电话才终于接通。打电话给余华的正是《北京文学》的负责人周雁如,她在电话中通知余华他投给 《北京文学》的三份稿件都已入选,并诚挚地邀请余华到北京改稿。 在《与〈北京文学〉同行十七年》一文中,余华详细地叙述了当时接电话的场景: 电话接通后,周雁如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她早晨上班就挂了这个长途,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接通。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声音,说话并不快,可是让我感到她说得很急,她的声音清晰准确,她告诉我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她又告诉我在改稿期间每天还有出差补助,最后她告诉我《北京文学》的地址——西长安街七号,告诉我出了北京站后应该坐10路公交车。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就像是在嘱咐一样,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 接到《北京文学》的电话之后,余华非常兴奋,第二天就坐车赶往北京。之后,余华在北京待了将近半个月,除了改稿之外,还在北京的各处好好逛了逛。 例如,他专门去了一趟故宫和天安门。余华发现现实中的北京比他想象中的更大、更宏伟,他在 《古典乐与珍妃井,铃声》一文中写道:“天安门小时画过,画的时候总在其背面涂一幅红旗,大天安门一倍。而今见了天安门,觉得画大其一倍的红旗,非大我一百倍的人不可。”此次北京之旅不仅让余华感受到了北京的宏伟,更让他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独特魅力。去北京之前,余华不太瞧得起中国的古典艺术,而参观故宫的经历却使余华开始对自己盲目崇拜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反思。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向是瞧不起本国艺术的,而对外国现代派作品则如醉如痴,如醉如痴到了盲目。虽说先前也曾多次听过中国古典乐,可由于没有故宫给我造成的氛围,总使我无法领受其中的魅力。现在领略到了一点,也是值得高兴的。”可以说,北京之旅让余华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这促使他走出自己的小世界,弃医从文。 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文学》还专门给余华开了一份证明,证明他的稿件被《北京文学》录用。等到余华从北京回到家乡的时候,全海盐都听说了余华到北京改稿的事情。后来因为这件事,余华就被调到文化馆工作。虽然最终还是弃医从文,但医生生涯已成为余华的底色,不断地启发和影响他的创作。 例如,他早期创作的《第一宿舍》《“威尼斯”牙齿店》就与他的牙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宿舍》是余华的处女作,主要讲述了四位来自不同地域的实习生到医院实习的故事。这四位实习生有着不一样的个性,生活习惯不同,对医生这份职业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毕建国,非常敬业,每当他出现误诊的情况,他都会认真地将误诊的病例记录在本子上。令人惋惜的是,小说的最后,毕建国因身患重症而去世。 《“威尼斯”牙齿店》的主人公老金则是一名牙医,在农村开了一家牙齿店,他拔牙既漂亮又利索,获得当地老百姓的好评。老金虽然是一名牙医,却非常喜欢创作,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创作出普希金作品那样的小说。 由上述作品可知,没有当牙医的经历,余华是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的。此外,5年的牙医经历也启发了余华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作为一名牙医,应该非常清楚哪些牙需要拔、哪些牙可以补,不能张冠李戴,把原本可以补的牙拔掉,这是一个牙医最基本的常识。 创作也是如此,虽然呈现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不论是写实的作品还是超现实的作品,都应该基于现实生活,要把握分寸,这样才不会像把原本可以补的牙拔掉那样张冠李戴。在创作中,余华一直秉承着这样的理念。 例如,在小说《第七天》中,余华虚构了一个殡仪馆的候烧大厅,死者过世后家属需要在这个大厅的取号机上取号,然后等待死者被火化。此外,这个候烧大厅还分为普通区和贵宾区。贵宾区是面向富人的,他们的墓地都在一亩地以上,而且所使用的骨灰盒比黄金还贵。为了让贵宾享有尊贵的待遇,贵宾区里还专门提供沙发给贵宾使用。 虽然作者虚构了一个候烧大厅,但其中的取号机和贵宾区、普通区的设计都是源于现实生活,源于在银行办理业务的经验:在银行办理业务,要先取号;银行会根据存款的额度将客户分为普通客户和金卡客户,而且银行里也有普通区和贵宾区。  配图 | 沃尔特·西科特 接触川端康成 1980年,余华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在进修期间,余华偶然读到两篇小说,一篇是汪曾祺的《受戒》,另一篇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 当时,国内发表了很多“伤痕文学”作品,而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使余华了解到,原来表现伤痕的方式并非只有控诉这一种,换一种方式来展现受伤也许比“伤痕文学”更有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川端康成与余华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川端康成出生于1899年,他的父亲也和余华的父亲一样,是一名医生,但是在川端康成一岁多时不幸因患肺结核去世。在父亲去世一年后,川端康成的母亲也和父亲一样患病辞世。之后的几年里,川端康成的姐姐、祖母也相继去世,只剩下川端康成与几乎双目失明的祖父相依为命。 1914年,川端康成的祖父去世之后,川端康成成了孤儿,后被他的舅父黑田秀太郎一家收养。可以说,川端康成的童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余华的童年也是非常孤独的,虽然没有像川端康成那样有多位亲人去世,但因为余华的父母长期忙于医院的工作,常常要值夜班,所以余华大多数时间是和哥哥待在家里。 相同的童年经历,使得多愁善感的余华更能理解川端康成的作品,也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余华对于川端康成的喜爱可以说是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他不但到处收集川端康成的作品,几乎将当时中国发表的有关川端康成的作品全都读了一遍,而且把川端康成视为自己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 有一次,余华在日本宣传《兄弟》,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提到“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日本记者非常吃惊,因为他们觉得川端康成的写作风格与余华的完全不一 样:川端康成的作品较为优雅;而余华的作品大都充满了死亡与暴力,小说风格相对来说较为粗俗。 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余华为何会喜欢川端康成,优雅的川端康成是如何影响余华的创作的?余华看到记者吃惊的表情,便告诉他们说:“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产生影响的时候,就好比是阳光对树木产生了影响一样。但重要的是,当树木在接受阳光影响的时候,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川端康成就教出了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曾在颁奖致辞中称赞川端康成:“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 川端康成在余华的初期创作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一文中,余华曾坦陈:“我曾经迷恋于川端康成的描述,那些用纤维连接起来的细部,我说的就是他描述细部的方式……川端喜欢用目光和内心的波动去抚摸事物,他很少用手去抚摸,因此当他不断地展示细部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地隐藏着什么。被隐藏的总是更加令人着迷。”受川端康成的影响,余华在创作中也非常注重细部的描写。 例如,在小说《竹女》中,余华就对小镇的风土人情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那镇很小,百十米长的两条街,中间夹着一条从静水湖伸过来的小河流。桥倒是不少,有五座,都是石拱桥,桥面高出两旁的屋顶。那些屋子看上去都像是陷在地里。镇上有米庄、有鱼行、有当铺;还有豆腐店、酒店、药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凡是城里有的,这儿全有。酒店的生意最兴隆,柜台上挂着块牌匾,上面写:太白遗风。只要是男人,都愿在此喝上点,价钱也不贵,花上他八文、十文铜钱便喝得心满意足了。那药店叫康寿堂,生意要差些。街上常有个穿绸服的人荡来荡去,这人是地保,地保靠收税养着。地保收税从来不收那些开店设铺做大生意的,这些人全有来头…… 不论是对小镇石桥的描述,还是对镇内酒店、药店的情况的叙述,都非常地细致入微,仿佛小镇就在眼前一样,极具画面感。此外,川端康成的作品还启发了余华在创作中营造抒情的氛围,展现东方式温婉的忧伤。 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的结尾,船上的舢板剧烈地晃动着,舞女本想和主人公 “我”道个别,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就微微地点了点头。待船逐渐远离小岛之后,主人公“我”躺在船舱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而泪水簌簌地滴落在书包上。在川端康成的启发下,余华在小说中也多次展现充满温暖的悲伤。 例如,在《第一宿舍》的结尾,因为宿舍楼要进行拆除,所有的实习生都要搬离第一宿舍。在离开的前一夜,“我”一边静静地看着书,一边总觉得缺少一丝烟味。于是,“我”不自觉地就想起来问了一句:“毕建国,怎么你戒烟了?”说完这句话后才发现毕建国早已离开了我们,床铺也是空的。 原标题:《余华:从牙医到作家》 阅读原文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