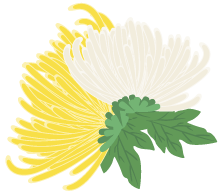| 谢默斯.希尼:凝视自己,并让黑暗发出回声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wy水桶杯 › 谢默斯.希尼:凝视自己,并让黑暗发出回声 |
谢默斯.希尼:凝视自己,并让黑暗发出回声
|
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舞蹈。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翻译解决的不只是语言问题,还有文化问题。只有译者真正对被译作品的国家的历史、文化、生活有深入了解,才能做到化“有形”为“无形”。翻译诗歌可能难度更大一些,诗歌自有其美感和韵律,如何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创造性译作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译作的优劣还会导致原作有不同的品质。 如文益君在看诗人的《山楂灯笼》这首诗时,找到了两种版本: 第一种: 但是有时候当你的呼吸羽毛般轻歙在寒霜中, 它会变成第欧根尼游荡的形状, 手上提着他的灯笼,寻找一个正人君子。 第二种: 但当你的呼吸在霜中凝成雾气, 它有时化形为提着灯笼的狄欧根尼斯 漫游,寻找那唯一真诚的人。 就这首诗的两种译本来说,我更喜欢第一种译法。当然,以上只是笔者浅薄的看法。巧合的是,谢默斯.希尼不仅仅是诗人,还是出众的翻译家,他曾将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译成现代英语,轰动一时。诗人也曾发表过一篇《翻译的影响》的文章,讨论了翻译之于诗歌的重要性。在他的诗集中文版序言中,诗人写道:我想对中国读者说,每当念及我们可以跨越语言、地理、文化的巨大距离,我就感到兴奋……那诗实际上是为作为读者的你写的,它召唤你向它靠拢。它放在那儿让你打开。它是一种造物,然而是内心的造物。所以,拥有中国读者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相信诗歌的公开性是有道理的,而我们感到作为帮助我们继续做敏感的人的诗的必要性,也是有道理的。
希尼的诗作纯朴自然,其诗歌描述的乡间风光(那些潮湿的绿色的角落、水流纵横的荒地、长满柔软灯芯草的低洼地,所有被水份润泽、被苔藓植被遮盖的土地)散发着北爱尔兰土地的芳香,这和诗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有关。在成名作《北方》发表之前,诗人已出版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通向黑暗之门》《在外过冬》等诗集,这些诗集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自觉意识,大都是吟唱诗人童年的美好岁月,描述的是家乡最常见、最普通的细微之物,像水桶、长犁、灌木丛、干草杈等等。诗人通过家乡的一草一木勾勒出一幅幅生动富有画面感的乡村景象,如: 小时候,没有人能阻止我去看水井 还有那带桶的老抽水机和绞绳 我爱那深落的黑暗,那陷在井中的天空,那 水草、真菌和潮湿苔藓的气味。 ——《自我的赫利孔山》节选 农具多次出现,干草杈的长柄飞过太空,杈尖挂满星光。 每当他想到宇宙飞船可到达最远处, 他就看到干草杈的长柄平稳地 飞过,沉着地穿过太空. 杈尖挂满星光无声无息一一 它最终学会随着简单的引导 超越既定目标,飞往另一世界 那儿尽善尽美——或是接近完美——这幻想 并不在于瞄准的目标,而在放飞它的手中。 ——《干草杈》节选 在1975年出版的诗集《北方》中,诗人写就了著名的“沼泽地组诗”。沼泽地是爱尔兰的基本地形,在《沼泽地》这首诗中,诗人用沼泽地借喻整个爱尔兰民族记忆的仓库,是爱尔兰人深埋在时间深处的无意识。 我们没有大草原 可以在晚上一片一片地切除大太阳 这里的任何地方眼睛都要向 侵蚀到眼前的地平线让步 被引进独眼巨人眼睛似的 山中小湖。我们无遮拦的国土 是一片沼泽,在太阳落下和升起之间 不断结着硬壳。 ——《沼泽地》节选 正是因为诗人对这些身边事物饱含深情,充满爱,所以他所构建的北爱尔兰田园世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气息。但希尼绝不仅仅是一位讴歌乡土的田园诗人,或者说不同于中国古代如陶渊明式的田园诗人,希尼在颂扬乡村的恬静,美丽自然的同时,也始终关注现实,关注民族的命运。更准确的说,希尼的诗歌主题其实一直围绕的都是爱尔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哪怕那些田园诗,诗人亦不是仅仅表述秀美的乡间风光。而是运用象征手法,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意象背后的现实。诗人始终不懈地“挖掘”着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挖掘》这首诗中,诗人将笔做枪(我的食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依偎着像一杆枪),泥炭则隐喻爱尔兰历史。 因此,在文益君看来,任何将诗人的诗歌一分为二,划为田园主题和政治主题都是片面的,狭隘的。此外,前辈叶芝从参与政治到离开政治,最后对政治彻底失望的经历也给了诗人启示,诗人关注政治事件,但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诗人深知要“管住自己的舌头”,文学与政治既要发生关系,也要留有距离。文学如果陷入政治纠缠,就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治工具。
有部轻喜剧电影《闰年》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镜头随着男女主人公的足迹为我们展现了旖旎的爱尔兰风光。但20世纪的这片土地上,却不断涌动着暴力、冲突与鲜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爱尔兰争取独立的力量不断掀起各种形式的斗争,形成北爱尔兰长期动乱的政治局面。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诗人的目光转向现实,在其诗行中思考着国家的分裂, 文化的冲突和宗教的矛盾引起的深层次命题。如: 我们厚大衣的口袋里装满了大麦—— 逃跑的时候我们没有厨房,没有要拆除的营帐—— 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得突然而迅速。 牧师与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一起躺在地沟里。 这群人几乎不是在行军,而像在徒手旅行 我们每天都在遭遇战中找到新的战术: 我们用长标枪切断敌人的缰绳洞穿骑手 把恐慌的牛群赶入敌阵。 我们穿过一定会让骑兵摔下马的树篱撤退。 直到,在维尼格尔高地上,那场致命的秘密会议。 数千人死在山腰,我们在炮轰中摇动着长柄镰刀。 山坡染成红色,血浸透了我们被冲垮的阵波。 他们埋葬我们时没有棺木没有寿衣 八月里我们的坟上长出了大麦。 ——《革命者的安魂曲》 装甲军车,出没于那些 沿途站岗的土兵, 他们涌来,退去 如同擦亮的挡风玻璃里的树影。 ——节选自《来自写作的前线》 晚上满月升过她的山墙 又经过她的窗子落回 躺进摆在桌子上的水中。 又一次在曾汲水喝的地方我看到 她杯子上一句《圣经》的训诫 记住施与者正在杯口处褪色。 ——节选自《饮水》
作为继叶芝后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希尼并没有被前辈的光环“阴影”所笼罩,而是在承袭叶芝诗歌中抽象朦胧的基色的基础之上,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特色。希尼认为叶芝为自己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提供了方向。 悉尼是一个“正常”的诗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没有人们想象中“李白”式的浪荡不羁,他不喜欢那些想通过“发疯”的方式写诗的年轻人。相反,他是一个具有强大自制力的诗人,是一个始终努力且真诚地追求自我完善的悉尼。这种自制力不仅体现在诗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其诗歌作品中。如在那些化用神话故事的诗歌中,诗人很少显露出主观的温情来,更多的是客观写就。 人们习惯上将20世纪的爱尔兰诗歌分为两个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在在上世纪40年代,爱尔兰诗坛的两位“大佬”——叶芝和乔伊斯先后离世。40年代以前,叶芝发起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这次运动重振了爱尔兰文化,并且创造性地吸收了当时欧洲的新思想新艺术。这为后来的诗人们铺就了道路,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诗人们的创作。因为叶芝和乔伊斯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后来者在叶芝的“象征主义”道路和乔伊斯的“现实主义道路”之间抉择时,产生了创作困惑。当然,以悉尼为代表的爱尔兰诗人们最终还是开辟了个人风格的诗歌道路。文艺复兴运动让他们追寻“爱尔兰品格”,追寻有着独立民族特色的诗歌写作风格。他们将泥炭般深沉的民族历史挖掘出来,并和现实相连接。诗人们的努力让当代爱尔兰诗歌有着鲜明的个性与品格。如果说以叶芝、乔伊斯为代表的诗人们让爱尔兰诗歌在整个世界诗坛有了一席之地,那么后叶芝时代的爱尔兰诗人们则做到了让爱尔兰诗歌坚韧地屹立于世界诗歌之林。 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我国的知名度也大大增加。但悉尼的中译版诗集并不多。已出版的诗集中也只是简略地选取了诗人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自200多页后是诗人的诗评集。这是因为悉尼是公认的天才的文学批评家,这些评论集宛如清晨荷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看诗人的评论集,可以看出诗人对诗歌的定义与理解,对当下世界诗歌以及 自己的诗作有着清晰的认知。如: 一方面,诗歌自然而神秘;而另一方面,它必须介入这个粗暴的公共世界。在这里,爆炸不分昼夜地真切地震颤着你的门窗,恐惧和乏味粉碎着生活,而无辜的人们被公开鞭打,在集中营中受到凌脖——各种各样的破坏性因素洋溢在空气里,或许还会使人疯狂放纵。 此刻,你会被卷入狂热的、宗教性直觉的古老漩涡;而彼时,你又会寻求人性的关爱和理性的平和。然而你“存在的理由”是否与纸上的文字无关?如帕特里克.卡拉纳夫所说,一个人在诗篇中喋喋不休并发现那就是他的生活。 你不得不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力,因为伪造情感是一种违背想象的罪恶。 与我们自己争辩的是诗歌,与他人争辩的是修辞。在直面当下的诸多事件之时,过多的意志较之处理的手段,往往会扭曲我写作进程中的节奏感。我总是倾听着诗句,有时,它们仿佛是从沼泽中显露出形体的,近乎完美,而且似乎很久以前便已躺在那里了,只是被一层神秘之纱所覆盖。技艺和判断的确很重要,但机遇和直觉同样有所贡献,我想这一过程类似于某种梦游般的奇遇,在男子的意志与智慧和女性丰富的情感与意象之间。 我猜想自已身上的女性因素和爱尔兰相关,而男性的血脉则来自英语文学的影响。我用英语来书写和言说,但我与一个英国人并不完全分享同样的视野和成见。我教授英语文学,在伦敦出版作品,但英语传统不是绝对的家园,另一种东西也同样养育了我。 这些声音向着两个方向展开:向后可追溯至爱尔兰所遭受的政治与文化的创伤,向外可以涉及外部世界的诸多困窘和经验。在学校里,我像学习英国文学一样学习着爱尔兰的盖尔文学。从那时起,我便确立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爱尔兰人,他所在的省份却坚持自己归属于英国。最近,我才发觉,我的出生之地恰巧暗示出了这种复杂的虔敬和矛盾。 当然,成为一个诗人的奥秘,无论是爱尔兰诗人还是其他类型,都存在于对词语活力的召唤之中。但我对定义的渴求,或许是追述性的,诉诸的却是我所出生之地的活生生的口语。如果你喜欢,我是在我的阅读逾越了我的根基时才开始诗人生涯的。我将个人的爱尔兰情感当作元音,而将由英语哺育的文学觉悟当作辅音。我的希望是,诗歌能够足以表述我的全部经验。
文益君之所以会在开头讨论翻译对原著的重要性,是因为读罢悉尼的诗歌,却很难与诗亲近起来。隐隐约约总感觉留有一段距离,没有那份熟稔和亲近感。一方面原因是诗人诗歌写作已臻化境,对本民族文化自觉的意识让诗人始终不懈探索,不甚了解爱尔兰历史、文化的外域读者读来便有如坠云里雾里之感;另一方面是,我国现有关于悉尼的诗歌译作实在算不得好,很多意象和词语之间的搭配显得突兀,不自然,由此必然造成读者对文本的陌生感。 我国著名诗人于坚对悉尼的赞誉颇高,于坚曾这样写道:“他不仅指引我们看到庸常生活的诗意,更通过这种诗意引领我们皈依神灵,热爱生活而不是逃避它。我喜欢他诗歌中的那种口气,他的语气缓慢,安静,有些诙谐,迟疑,他在适当的时候将诗领到深渊的入口上,他并不跳进去,旋转,又回来,更开阔的境界。他没有愤怒,愤怒出不了诗人。他诙谐地吹着口哨,神奇的语词将一切都领向温暖,他仿佛有一个巨大的襁褓,他的诗歌之婴明亮、安静。 他将神请到沼泽地边上,自己欣赏自己的复活。 这是一位真正有洞见的充满魅力的诗人,他不玩语言游戏,他来自爱尔兰。” 在某次采访中于坚也谈到了曾与悉尼的一次会面。于坚是我们大益文学院的签约作家,其诗歌中的先锋性与大益文学这方中国先锋文学重镇的气息完美契合。而诗人悉尼也在其诗歌中自创了方块诗的诗歌结构,创造性地化用神话于诗歌等。若是诗人尚在,想必也会和大益文学结下良缘。可惜,诗人已故。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会亘古流传,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黯淡。同样,诗人“ 洋溢着抒情之美,包容着深邃的伦理,批露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奇迹”的诗歌也会永远流传下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