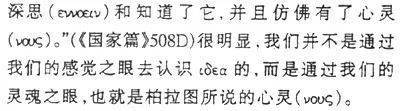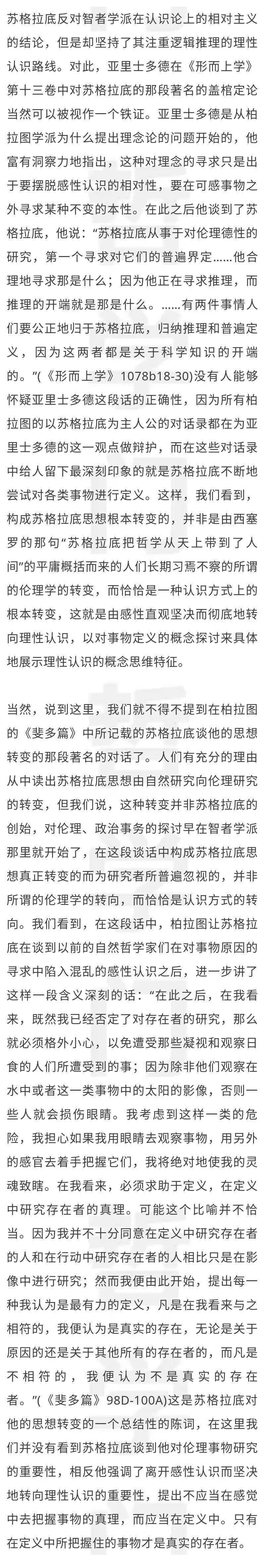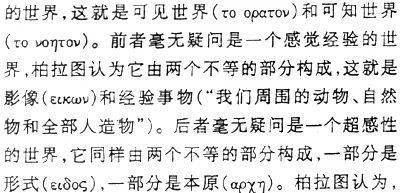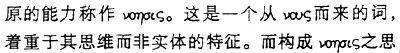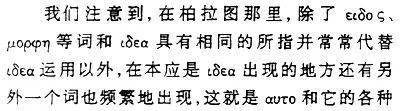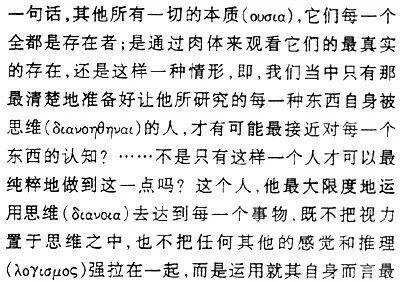| 论柏拉图的 idea 之为“理念”而非“相”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idea是名词 › 论柏拉图的 idea 之为“理念”而非“相” |
论柏拉图的 idea 之为“理念”而非“相”
|
“理念”,是有着充足的根据的。因为,从 的词源意义上来看,它显然不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相”免除了在理解上同我们的主观观念的这样一种联系。 但是,我以为上述词源学的考察并不是理解柏拉图理念论的关键之点,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就 作为“看”的对象而言,我们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难道仅仅是事物的形相、外观吗?当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时,我们立刻就意识到, 绝非上面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因为,贯穿柏拉图理念论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 乃是超感性的存在,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感觉之眼来观看它,而是在用我们的灵魂之眼。 关于这一点,狄奥根尼·拉尔修的一则记载是颇具有说服力的,这是发生在柏拉图和犬儒第欧根尼之间的一场对话。拉尔修这样写道:“当柏拉图就 进行讨论,并用到‘桌子性’和‘杯子性’的名称时,他(指第欧根尼)说道:‘柏拉图呵,我的确看见一张桌子和一个杯子;但是桌子性和杯子性却绝对没有看见。’而柏拉图回答说:‘有道理,因为你虽然具有用来看桌子和杯子的眼睛,但没有用来看桌子性和杯子性的心灵( )。’”(《古代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Vol.Ⅵ,53)爱挑剔的评论者当然会质疑这段文字的真实性,但是熟悉柏拉图著作的人会知道,即便这段文字所记载的事情未必是真实的,但是这段文字中的哲学内涵柏拉图却在别的地方以别的方式表达过。例如,柏拉图运用了眼睛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来类比灵魂和善的理念之间的关系。他说:“灵魂的眼睛也是这样。当它凝视那被真理和存在所照耀的东西,它便
这样一来,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里所说的灵魂之眼是什么呢?什么是柏拉图所说的心灵( )呢?显然,如果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柏拉图的 究竟是什么,就必须首先搞明白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如果现在就给出一个简洁的回答,那么回答就是,在柏拉图这里, 并非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神秘的直观能力,相反,它指的就是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且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性认识,这就是极具思辨性的概念思维。人们当然会质疑这个回答,会以在柏拉图那里理性认识尚没有出现为借口而力图把柏拉图对 的认识同某种神秘的直观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汪子嵩先生等主编的《希腊哲学史》中,便是以此为理由而力主把 译作“相”而非“理念”的。但是,实际情形真是这样吗? 二 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考察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的进展,就会发现,在认识论上,一个清晰可见的变化就是,由对以想像直观为特征的感性认识的倚重逐渐向着对以逻辑推理为特征的理性认识的重要作用强调的转变。这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前哲学时期,也就是在荷马和赫西俄德那里,神话思维还是一种支配性的思维形态,理性的、逻辑推理的认识当然还不可能有,相反,隐喻、象征、类比、想像构成了当时思维的主要特征,从而,作为后来希腊哲学认识论关键词的 (心灵)在荷马和赫西俄德那里只是指一种直观或者说直觉的能力。但是,正如弗里茨(Fritz)所指出的,即使这样,一种变化已开始出现了。无论是荷马还是赫西俄德,都把 的认识功能同普通的感觉认识区分了开来,把它特别地同事物的真相联系在了一起。[1] 哲学思维是和神话思维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从而,由前哲学时期进入到哲学时期,自然就意味着思维方式上的一种根本的革命,同时当然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上的根本革命。经验的、逻辑推理的思维开始出现了,这也就是泰勒斯被称作哲学家而非神学家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决不能无限地夸大这一转变,相反,我们要诚实地指出,对于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家而言,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一种生机论的或者说生成论的世界观,从而,他们虽然是在经验的基地上来把握世界的(关于这一点,所有米利都学派哲学家所做的那些天文学观察都是明证),并且在有限经验联系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推理(试想一想泰勒斯在几何学上所做的那些实际的测量以及阿那克西曼德对日食、月食的带有理论构造色彩的解释),但是他们对整个世界的描述在根本上还是依赖于一种建基于想像之上的直观。他们被这种想像性的直观所鼓舞,说出了许多仿佛神谕一般的权威性真理。 毕达哥拉斯、克塞诺芬尼以及赫拉克利特当然仍旧处于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思想氛围当中,甚至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的著作也充满了这种神谕的特征。但是,毕竟向着理性认识的变化在持续着。人们不管怎样强调毕达哥拉斯的数的感性特征和神秘性、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由于同“火”的内在关联而具有的那种生命的肉身性,但都必须承认,一种理性思维的特征已经逐渐渗透了进来,并企图在认识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例如,赫拉克利特一方面说,“看、听和学,所有这些都是我所乐意的”(残篇55),另一方面却说,“对人而言,眼睛和耳朵是坏的见证,如若他们拥有的是粗鄙的灵魂的话”(残篇107)。而对于什么样的灵魂才可称之为智慧,他这样说:“如果不听从我而是听从这逻各斯,就会一致同意说一切是一这就是智慧。”(残篇50)又说:“因此必须服从这共同的东西;尽管逻各斯是公共的,但是大多数人生活着仿佛他们有着自己的心智一般。”(残篇2)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除了有“话”、“言”这样的通常的意思外,它还具有了节奏、分寸的意思,并因此具有了理性的意味。[2]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决不能过高地估计在赫拉克利特思维中的那种理性,它在根本上仍旧是一种神谕式的智慧,一种在根本上不借助于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是借助于高贵而单纯的直观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尼德才具有了分界线的意义。 从巴门尼德开始,一种基于严格的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开始形成并且逐渐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研究者公认,尽管巴门尼德论存在的诗篇仍旧采取了神谕的形式,但是他对存在的讨论在主要的方面却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3]在这种逻辑的演绎中,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第一次出现了,并且发挥了其强大的论证力量,巴门尼德借此确立了存在概念的绝对的自我同一性和永恒性。同时,他还明确地把以逻辑推理为根本特征的理性认识和以经验表象为特征的感性认识对立了起来,强调了它们之间无限的区别。在著名的残篇7中他这样说: 因为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屈从于这一观点,非存在存在; 相反你要让心思(νοηυα)远离这条研究道路, 也不要让杂乱的经验迫使你沿着这条路 运用盲目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 而是运用理性(λοοζγ)(注:此处的 λοοζγ 无论是Guthrie还是Kirk与Raven,都翻译做“理性”,reason。)来判断由我说出的充满争执的否证。 在这里,巴门尼德针对他在前面对于存在所做的逻辑论证,毫不掩饰地要求人们不要运用自己的感觉经验来判断这一论证的是非,而是运用理性来判断。这样,理性认识第一次被确定为裁决认识是非的准绳。 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极大地发展了由巴门尼德所开始的这样一种逻辑推理的论证艺术。他对运动的反驳和对多的反驳毫无疑问是纯逻辑的,长期习惯于经验感性认识的人,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才可能理解这种对当时人来说可以说是全新的思维方式,因为它是完全和经验相反的。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我们看到,当提到他的这种论说方式时,芝诺明确地告诉苏格拉底,他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说明,判断一种观点是否荒唐的不是靠我们的感性经验,而是靠一种严格的逻辑论证。看起来似乎巴门尼德的观点由于同日常经验相反而显得可笑,但是经过这种严格的逻辑论证,日常经验却暴露出了它荒唐可笑的一面。 这种逻辑的论辩的技艺在智者学派那里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和完善。智者学派开始了对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真正系统的研究,这是公认的事实,而这毫无疑问也就是对理性思维的规律的研究。对此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因为,智者学派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普遍地持有一种感觉主义的认识论主张,并由此发展出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和道德观,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权威。这当然是实情,但是不应忘记的是,对这种感觉主义认识论的论证,智者学派采取的却是理性的逻辑论证的方式,而不是神话隐喻或者智慧格言的形式,后者是巴门尼德以前的思想家以及前哲学时期的智慧人士所经常运用的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对此,有心的人可以注意一下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关于德性是否可教这一主题的论证。在那里,当普罗泰戈拉应苏格拉底之请准备对德性是否可教加以论证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苏格拉底,我很高兴照办。不过你们喜欢怎样的讲法呢?要我像老一辈人对年轻人讲寓言或者神话那样对你们来讲,还是拿问题一步步进行论证呢?”[4]在此之后,他分别运用了传统的神话寓言的方式和新兴的逻辑论证的方式表达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这样,我们看到,至少逻辑推理的论证方式在智者学派那里已经成为一种自觉了。高尔吉亚那篇著名的《论自然或非存在》的论文就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里,高尔吉亚确实是依据一种感觉主义的认识论来动摇巴门尼德所确立的永恒、绝对、惟一的存在的,但是,所有的论证却全部都是巴门尼德式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上的。这样,智者学派在确立以逻辑推理为根本特征的理性思维的权威性以取代旧的神话思维和感性直观思维的权威性上,确实可以说是厥功甚伟的。
这当然就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仅就《斐多篇》而言,苏格拉底在认识论上的这一见解当然也可以视作是柏拉图本人的观点。而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就是,柏拉图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路线上,在他的思想中更加明确了理性认识在本质上就是概念思维,从而把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而来的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必然发展进一步提升到了概念思维的水平上。这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柏拉图而言,思维不再仅仅借助于感性经验的意象,在这个水平上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概括,相反,却是通过概念的运动超越感性经验来建构理论的体系。关于思维如何由感性经验认识向着理性概念思维飞跃,柏拉图在《国家篇》中也是像《普罗泰戈拉篇》中的普罗泰戈拉论证德性是否可教的方式一样,通过比喻和论证双重方式来进行的。 就比喻而言,当然就是《国家篇》第七卷一开始的那个著名的“洞喻”。柏拉图通过一个人如何摆脱了黑暗洞穴中由昏暗火光所映射出来的不真实的幻影而步出洞外直面阳光照耀下的真实世界的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一个人的认识如何从沉溺于混乱的感性经验意象飞跃到直接进行概念思维的水平这一重大转折。 而就论证而言,在《国家篇》第六卷的最后,柏拉图以清晰而明确的说理对感性经验认识和理性概念认识进行了根本的区分。他以一条线段的划分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
前者是各门科学的认识对象,而后者则是辩证法的认识对象。柏拉图认为形式虽然构成了可知世界很大的一个部分,但是由于它的存在仍然依赖于最高的本原,并且对它的认识有时候还需要借助于感性经验的意象,因此对它的知识并不是完善的,真正完善的是对本原的认识,他把这种认识本
维特性的不是别的,就是纯粹概念的运动。柏拉图这样说:“至于可知世界的另一部分,你要知道,我指的是,理性本身凭借论辩的能力所触及的东西,它不把假设当做本原,而只是作为假设,就像起步的台阶一样,为的是达到无需假设的东西,臻于万物的本原,在触及它后,又返回来去把握那些分有它的东西,这样一直下降到结论,它不利用任何可感知物,而是利用形式本身,通过形式到达形式,最终以形式结束。”(《国家篇》518B、C)显然,这最后一句话是重要的。我们可以问,是什么样的思维活动不需要借助经验感性的意象,而仅仅从非感性的形式出发,“通过形式到达形式,最终以形式结束”呢?毫无疑问,这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概念思辨活动,而哲学思维正是以这样一种思维活动使它和一般的科学研究活动区别开来的。 这样,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就是,那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发展而来的人类认识的最高官能,也就是心灵 ,在柏拉图这里就被明确为是一种富有高度思辨性的纯粹概念思维。我们当然可以公正地指出,这种概念思维在柏拉图那里发展得还并不成熟,不仅对于这种概念思维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他还不是十分的清楚,而且在很多时候还常常把它同神话思维的意象混杂在一起,但是,就我们上面的分析来看, 毕竟已经超越了感性的直观,被提升到概念思维的高度上来了。因此,它并不是如人们所想像的,只是一种高级的、甚至神秘的直观能力。在这里,重读一下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柏拉图理念论的一些评论是有意义的,他在谈到人们对柏拉图的理念的常见的两种误解时这样说:“……把理念定义为理智的直观,以为它们必然或者直接呈现在幸运的天才里,或者直接呈现在一种陶醉或灵感的境界里,——这样就把理念当做幻想的产物。但这却不是柏拉图的意思,也不合乎真理。理念不是直接在意识中,而是在认识中。理念只有当它们被当做概括性的认识之简单性的结果的情形下,才是直观,才是直接的,或换句话说,直接性的直观只表示理念的简单性那一环节。因此人们并不是具有理念,反之理念只是通过认识的过程才在我们的心灵中产生出来。热忱[按即陶醉、灵感]只是理念最初的粗糙的产物,但是认识才把它们推进到明白的合于理性的发展的形态。”[5]这样看来,对于柏拉图来说, 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心灵直观的能力,而是思辨认识过程本身。而这样的一种思辨活动,显然是纯理性的。假如我们深刻地把握住了 在柏拉图哲学中的这一特性,那么,通过 的纯粹的概念思维运动所把握住的东西,怎么可能仅仅是“相”呢? 这样一来,现在的问题就转化为:如果由灵魂之眼 ——一种纯粹的概念思维运动——所把握住的东西,完全不同于通过我们的感觉之眼所看到的事物的混沌的形相和外观,而是一种理性存在,那么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柏拉图的那个显赫的概念 究竟是指什么呢? 三
性、数、格形式。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是一个特殊的代词类型,它当然具有代词的功能,但是它既非关系代词,也非指示代词,更不是人称代词,它所指代的不是这一类的任何一种,而是对事物之自身的指代,并由此具有了表示“同一”的形容词功能。 在古希腊语中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功能当然可以被哲学地来理解,这就是,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同一就是自身,自身就是同一,惟作为自身而存在的东西才是一个保持同一的东西,而反过来,惟保持同一的东西才是一个作为自身而存在的东西。柏拉图在本应是 出现的地方大量地运用了 这个词。例如,在《斐多篇》74A中,柏拉图这样说:“我们断言在某处存在着某种相等,我说的不是木头和木头的相等,也不是石头和石头的相等,也不是诸如此类的别的相等,而是所有这些之外的另一个东西,相等自身。”在75C中他又把 从“相等”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的概念上,他这样说:“因为我们目前的理论不只是涉及相等,也涉及美自身,善自身,正义自身和神圣自身。”这样,很清楚, 不是别的,就是事物之自身。那么作为事物之自身的 具有什么特质呢?它是否像康德的“物之在其自身”(Dinge an sich selbst)一样乃是一个不可认知之物呢?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发现,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曾经做过明确的探讨。他让苏格拉底这样来询问爱盘根究底的西米阿斯:“我们认为存在着正义自身还是不存在呢?”当西米阿斯做了肯定的回答后,他又让苏格拉底接着询问道:“那么美自身和善自身呢?”当西米阿斯再次做了肯定的答复后,苏格拉底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在什么时候曾经用肉眼看见这一类东西中的任何一个呢?……或者你曾运用别的某种肉体感觉到它们吗?我说的是所有这一切,例如体积,健康,力量,以及
纯粹的思维着手去探究存在者中每一种就其自身而言最纯粹的事物,最大限度地离弃了眼睛和耳朵,总而言之,整个肉体,因为肉体,只要和它在一起,就扰乱并且不让灵魂去获取真理和智慧,西米阿斯呵,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切中了存在者,难道不正是这个人吗?”(《斐多篇》65D、E)这样,我们就彻底明白了,在柏拉图看来, 作为事物之自身,并不是像康德的自在之物那样是绝对不可认识的,它只不过是绝对地不为我们的感觉所认识而已,从而它不是感性认识的对象,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且在根本上乃是一种纯粹的仅仅基于概念推理的理性思维的认识对象。从而,毫无疑问,作为事物之自身的 绝对不可能是“相”、“形式”或者“外观”,像这样的一些和感性经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词绝对没有揭示出 的本质。与此相反, 在本质上是一种超感性的存在,作为事物之自身,它不是别的,就是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实际上柏拉图在上面一段话中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说:“我说的是所有这一切,例如体积,健康,力量,以及一句话,其他所有一切的本质 这个“存在”的阴性名词之被运用,就是指事物的最真实的存在,而这不是别的,就是事物之本质,当然也就是事物之本身。对此,即使是从拉丁语发展而来的“本质”一词essense,也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因为,essense的词根es正是希腊语系动词“是”的词根,从而它在构词上也正是“存在”的名词化。通过如此一番周折的考究,我们终于明白了,柏拉图的 从客观存在的方面来看,并非是事物的感性形相,而是事物的本质,它构成了事物最真实的存在,而这也就是事物的本体。而作为事物之最真实的存在、本质,它不是感觉经验的认识对象,而是理性思维的认识对象,从思维方面来说,它就是思维之概念。人们当然知道“概念”(concept)和“观念”(idea)的差别,前者是一种客观思维,后者则是一种主观意象,前者的展开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后者的展开却是任意的。这样, 在柏拉图那里就同时具有了本体论和逻辑学的内涵。也就是说,柏拉图对 的探讨不仅是对存在本身的探讨,同时也是对思维本身客观逻辑的探讨,他通过 不仅是在架构一种世界体系,而且也是在架构一种概念体系。思维和存在,正如巴门尼德所揭示的那样,在柏拉图这里也是同一的。 但是,当我们这样揭示出柏拉图的 的根本内涵之后,我们立刻便认识到, 还具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内涵,这就是, 对于柏拉图来说,不仅意味着一种理性存在,而且还同时意味着一种理想存在。关于这一点,人们只要看看《斐多篇》中柏拉图对他心目中的真实世界的描述就明白了。柏拉图认为那是在地球的大气之上的世界,那里的一切都比地球上存在的一切更加完美,实际上,它们就是地球上所存在的一切的完美形式。“那儿的整个大地就是这些五颜六色,而比起我们这儿的颜色来,更鲜明更纯净,大地是美不胜收的一片紫色,一片金黄色,一片白色,白的比白垩白雪更白,还有一片一片大地是其他各种颜色,比起我们这儿所见的颜色 |
【本文地址】